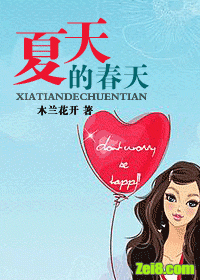武则天的佛缘-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际上是帝王与宗教的联系人,他们能从宫中传递出皇族宗教生活的完整图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又是皇族成员宗教信仰的代言人。
这时,皇宫内道场的僧尼智运、真莹等人,奉命发起了武则天被称为天后之后的一场佛教功德事业,这便是在洛阳龙门雕造万佛窟。万佛窟内共雕造佛像一万五千余尊,各壁主尊分别为弥勒佛、观音菩萨及阿育王(优填王)。各壁题记分别祝愿天皇、天后、皇子、诸王子等“万劫千生,无亏供养”、“桑田碧海,永固归依”、“愿救法界苍生无始罪障,今生疾厄皆得消灭”、“愿无始恶,业罪消灭,法界四生,永断恶僧”、“从今生至成佛以来普作菩提,眷属誓相度脱”。万佛洞的造像布局与题记内容表明,这是继龙门惠简洞弥勒佛造像和奉先寺大卢舍那佛造像之后,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的又一项佛教功德事业,其间亦充分体现了天后武则天崇佛的真正目的。
如果把天后武则天这个时候的崇佛及利用佛教仅仅看作是追福、建寺、造窟、写经、度僧、施舍等,则还不够充分。天后武则天崇佛和利用佛教是一种无意识的意念,或者是潜意识的身心活动,因为她对佛法的理解比一般信徒更为深刻,佛教已融化到了她的血液之中,一切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她的崇佛,不需专门刻意去追求,不需再吃斋念佛,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因缘造就的。
这一点,天后武则天自己也非常清楚。在对待佛教问题上,她再不需要张扬,再不需要诵经念佛,再不需要焚香祈祷了。她觉得佛教就在自己心中,一切都是随缘而动的,其中不需要做作,都是佛意所使然。从她当上皇后到高宗皇帝去世,在她的催促下,高宗皇帝频繁改元,大致共用了十三个年号,这和高祖皇帝、太宗皇帝在位期间只用一个年号完全不同。在武则天看来,改换年号是摒弃传统,是在不断创造新的标记,这也就是随缘。
永徽是高宗皇帝登基时用的年号,和武则天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但在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自己被从感业寺接回宫中,她即施展巧慧争宠,到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冬十月,王皇后、萧淑妃被废为庶人,自己荣登皇后宝座,次年废皇太子李忠为梁王,立自己生的儿子李弘为太子,显庆年号即由此而来。显者,示也;庆者,可贺也。这也不正应了“身宠君尊,当世显扬”的古语吗?这就是随缘。麟德年号的颁行,主要是由于太子李弘地位的完全确立。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太子李弘已经12岁了,在她的要求下,高宗皇帝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就在这时,河东绛州(今山西绛州)有麟现于介山,长安含元殿前亦有麟的脚印出现,故使高宗皇帝改元麟德,为“母以子贵,子以母显”张扬。这也不是随缘吗?在武则天与高宗皇帝的频繁改元中,始终闪现的是武则天的身影,而她本人也能够在这频繁改元中得到心理上的巨大满足,或者说有一种莫大的成就感。在她看来,这种满足和成就感,是她本人应该享受和领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缘造就。有因必有缘,自己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什么方式播下的因,就必然要有结果,频繁的改元就是对这种结果的显现和张扬。所以,这一切都是随缘而动。
可以发现,天后武则天对佛家的因缘关系的认识,颇有独特之处。这便是她用因缘关系来证明自己一切作为的合理性。其实,她根本无须来证明,她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为这种证明与其说是给天下人看的,倒不如说是调节和平衡自己内心的需要。天后武则天就是在这种需要不需要中继续她的因缘。
这些年来,她虽然参与朝政,但都是通过高宗皇帝和朝廷才能合法化的行使权力。并不能以皇后或天后的名义与高宗皇帝或大臣分权,更不能在名义上控制外廷。原先拥戴她为皇后的那班人马,死的死了,退的退了,已经没有多少实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又要广布自己的因缘了。这就是必须重新物色一批新的亲信力量。高宗皇帝按照旧例集中大量学者汇编前朝史料和整理儒家经典,给了她启发,自己为什么不能照此组织为自己服务的学者班子呢?于是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起,武后便随缘而动,组织了听命于自己的学者班子。参加这个班子的人都是写文章的高手,大都担任记载实录言行的左右史或著作郎。武后以修撰为名,将他们召入宫禁之中,并特许他们由皇宫北门出入。当时皇宫分南北两个部分,南边为朝廷办事的地方,北边为后宫内苑,一般人是不允许出入北门的。武后特许这些人可以从北门出入,故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北门学士。武后让这些人编撰了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制定了臣民行为规范的《百僚新诫》,恢复整理出了儒家礼仪说教的《乐书》,还编写了科技方面的《兆人本业》,以及整理注疏了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等,这些书在当时朝野影响非常大,有些书甚至被确定为科举的必读书。武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让这些北门学士进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只是表面上的,实质上这些北门学士是武后的写作班子,开始时他们替武后起草奏章,研讨政策,批复文牍,后来就逐渐起到了中书门下宰相的作用。随着武后的权力逐渐扩张,这些人大都得到了重用,有几个还正式荣升为宰相。他们在以后武则天执掌政权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种培植心腹亲信,为自己政治活动建立基础的行为,在天后武则天看来,也是随对于崇信佛家因缘说教的天后武则天来说,太子李弘的病逝,使她显得非常无奈。
太子李弘在父皇母后的呵护下已经成年了,他曾十分胜任地在监国期间管理各项政务,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赞许和拥戴,被公认为放心的接班人。高宗皇帝患病期间,曾多次说待太子磨练得差不多时,就将皇位禅让给他。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暮春四月,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随天皇天后在洛阳合壁宫休养时,突然死在了宫中天后武则天的居所绮云殿。对此,诸史纷纭,多认为太子李弘是天后武则天鸩杀的,理由是天后武则天把太子李弘当作自己临朝称帝的直接障碍,且又知道高宗皇帝要将皇位禅让给太子,故先行一步,将太子鸩杀。为了给这一结论寻找根据,诸史还多认为太子李弘与天后武则天的关系一直较紧张等。
其实,这是一桩历史谜案。
太子李弘与母后的关系的确有些紧张,因为在腐儒顽愚的儒家经师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李弘,对崇信佛教的母后过于残酷的做法多有不满,但生性懦弱内向的性格,使他把这些不满完全隐藏在内心,从不表露出来。天后武则天对自己在感业寺生下的这个儿子,一直比较满意,她也能或多或少地觉察到长大后的太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不满,但她并不在意,她企盼太子能真正长成一个有资格接班的人,她对太子还是充满了希望的。因为这是一个母亲的本能,自己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太子能顺利登基吗?这一想法与天后武则天想做人间弥勒并不矛盾。想成为弥勒佛的化身,拯救天下众生,只是她长期崇信佛教而悟出的人生目的与生命的意义,她由才人而为尼姑,由尼姑而为昭仪,由昭仪而为皇后,由皇后而为天后,这一切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她领悟到的人生目的与生命意义。但是,弥勒佛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是她长期宫廷生活和参与朝政争斗的精神动力。而且越是有所建树,有所作为,她就越觉得自己就是弥勒佛的化身,就是人间的弥勒佛了。但在现实中,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大的企望。被称为天后之后,她觉得现实中的自己已经登上了生命发展的最高峰,已经做到了有史以来一个皇后所能做到和享有的一切了。所以,理想中的弥勒佛和现实中的天后,尽管还有很大差距,但武则天已经觉得二者已相差无几了,她必须顺从帝王传位与继位的规则,起码在这个时候,她还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她对太子李弘,这个自己在感业寺生下的长子,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记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时,她与高宗皇帝驾幸洛阳,留太子李弘在京师长安监国处理朝政。一天,李弘到后宫散步,发现了幽禁在后宫的他的两个异母姐姐,即萧淑妃生的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这两个公主都已经是30多岁的老姑娘了,还没有出嫁。太子李弘对此有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耳濡目染了母亲如何残酷的对待废皇后王氏和萧淑妃的,他不满母亲的这种残无人道的做法。为此,他满怀同情地奏请高宗皇帝,允许二位公主姐姐出嫁,免受不公平的待遇。当武后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儿子的书呆子气。幽禁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武后认为是报应,是她们为生母萧淑妃在消孽,是武后与萧淑妃恩怨所结的必然。太子李弘他就不明白这一点,同情也罢,怜悯也罢,这并不是他所能管的事,他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监国处理政事上,根本不可以或不用操心母辈们后宫里的事。武后没有和儿子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觉得这孩子善良有余而狠毒不够,必须再经过磨练才能挑起肩负社稷的重任。两位公主的命运当然也是因缘所定,武后随即就将她们二人嫁给了两位无名的禁军卫士。
在那个十恶不赦的贺兰敏之搅乱了太子李弘纳妃的事之后,武后又为儿子找到了新的妃子,这个儿媳便是高门士族出身的禁军大将裴居道的女儿。高宗皇帝和武后本人对这个大家闺秀的儿媳妇非常满意,觉得在配婚生子传宗接代方面再不用为儿子担忧了。但太子与裴妃成婚一年半过去了,裴妃却未能怀孕生子,武后非常着急,命太医全面检查了太子的身体,太医检查的结果使武后更为不安了,他们说太子身体有沉疴旧疾,不但生育有问题,就连生命也难说能维持多久。
太子李弘终于死了。但绝不是天后武则天鸩杀的。按史籍资料分析,太子李弘似乎是患了肺痨疾病,遇风寒后又急性发作而永诀人世的。当时,太医们还费了很大的功夫去抢救治疗,但终究无效。太子李弘过早地去世,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都没有预料到,尤其是这位嫡长子没有留下一颗龙种,岂不是要断子绝孙吗?作为母亲,天后武则天悲痛难胜,写下了《一切道经序》,来悼念自己这位早逝的长子,高宗皇帝更采取了一个不平常的举动,他下诏向朝廷宣布,谥李弘为孝敬皇帝,仿佛太子真的当过皇帝似的。
如果说太子李弘病逝是因缘所致,天后武则天是根本不赞同的,但她又是很无奈的,只能默默地面对这个现实,把悲痛埋藏在自己的心底,只能“心缠积悼,痛结心慈”,默默地诵经念佛来超度自己的儿子。
史载,太子李弘病逝后,高宗皇帝在如此沉重地打击下,身体更是每况愈下。说实话,高宗皇帝已经是心力憔悴难负重任了。他原来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李弘身上,想让他磨练一番后,将皇帝位禅让给他,谁知他一病而逝,使自己的希望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萌发了一种奇怪的想法,即自己先行退位,使天后武则天摄政,待新太子议立并培养一番后,再还政于太子,使其正式登基即位。这个想法中是否掺和了天后武则天的意见,很难说得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高宗皇帝的这一奇怪的想法中,起码体现了对天后武则天的绝对信任,以及对她为政能力的充分肯定。
高宗皇帝破天荒地提出让天后武则天摄政,并将此事正式交付宰相们讨论。这时在相位上的有张文瓘、戴至德、李敬玄、刘仁轨等多人,他们对高宗皇帝要使天后武则天摄政一事都噤若寒蝉,不敢置喙,唯有中书令郝处俊固谏以为不可,他慷慨陈词地对高宗皇帝说:“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李唐王朝的天下是高祖太宗皇帝打下的天下,并不是你高宗一个人的天下,你若使天后摄政,就是把天下交给了别人。
宰相之外,中书侍郎李义琰也进言呼吁,力劝高宗皇帝“处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