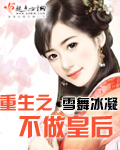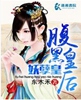宣穆皇后-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时候的曹操,颇不是什么名人,也只有个陈宫将其救下,然而都快将将脱险,到了曹操旧识的吕伯奢一家,曹操早成了惊弓之鸟,疑窦暗生,杀了恩人一家。
到了后世的演艺戏文将这一段演得精彩,但事实上当时比起董卓乱政,各地黄巾军不除来说,也不算什么大新闻。
年头上,死里逃生的曹操受人资助组建了一千五的兵,加入了讨董关东军。
联军盟主便是他儿时的玩伴——袁绍。
二月,关东军与董卓军僵持,董卓下令迁都长安,受到士庶反对,便下令焚洛阳。
千年古都,付之一炬。
对于全天下的人来说,洛阳古都早就成了汉王朝的一个象征了,洛阳的失落,与其说是一城的生死存亡,倒不如说是汉室将倾之兆。
对全天下士子来说,更意味着王道的覆灭。
于此同时的温县,接道这个消息后,驿道酒肆的行人,走卒担夫皆惶惶不可终日,士人齐聚则解冠朝洛阳方向而拜,抱头痛哭。
张父汪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县碰头照例顿足长叹一番,末了,带着满腹的沉郁回家。
夫人山氏见了颇为奇怪,赶着迎他上前,等入了内室,一边给他换上家常便衣,一边问道,“大人您今日可是怎么了?”
张汪心里正一口气压得喘不过,“国都……国都被毁了。”
山氏是知道这消息的。
张汪又顿了顿,“黄子琰,杨文先二人因反对迁都,皆为罢官。”
山氏一听,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么说这两个陌生的人名,各位或许是听着纳闷的。
黄杨二人皆是当时的太尉,司徒。汉代三公,直接占其二。可见董卓的嚣张之态,连罢三公有其二。
要是这么说还陌生的话,黄子琰既是黄琬,在牢里被关了二十年还能继续爬出来做太尉,可见其家族背景有多硬多不好惹。
杨文先就是杨彪,这人或许也还不熟,但说到那个说“鸡肋”的杨修大家却是熟了的。这位即是杨修之父,杨修被曹操杀了,见了他却还要“谢之”(谢:道歉),到了曹丕称帝还要以其为太尉,可见一斑。
但这会儿,任凭这些朝廷上的名士们如何反对,朝外的末系士族们如何痛哭,这群汉帝国的“秀才”们遇上的却是这个董卓这个“兵蛮子”,管你是民还是官,颇流氓的直接抢了城里能运走的所有财宝,运得走的运,运不走的砸。肯动迁的走,不肯动迁的直接一把火杀城,看你还走不走。
当然此刻也固有一批汉臣遗老,宁死守节,活活烧死城中,子孙者虽恸哭抢地,为了族系延续也只得含着血泪上路,竟是连尊者的尸骨都无法收埋。
说到悲壮之处,张汪虽八尺男儿也不由泪落,“洛阳二百里内无复孑遗,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世道真是没救了吗?”
对于这时代的读书人来说,儒家正统已被标榜百年有余,早是根深蒂固的了。
读书人,首要的就是气节,忠君报国是这时代的第一位,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这个时代人最正统的思想了。
别说张汪会为此低落,就算是作为妇孺的山氏终日在家中,听说国都沦陷的事,也是惶惶不安着。
但丈夫这样的心情,作为妻子,且是个贤妻,山氏也不得不安抚其说:“大人如此,忧忡忡于天下,然世道颓败,却非我等民庶一己之过;世道泰然,亦非我等民庶一己之功。”
张汪自然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但作为个受了二十多年教育的……封建好青年,要一时接受儒道之世的败落,却也是有了心结。
一旁的摇车里,春华因是个婴儿,倒也没人管束与她,更不会有人认为她会有记事,一岁大的孩子,实在让大人来避开说话的这种考量都没有。
所以她颇听了父母的说话。
张汪是个封建好青年,但女儿春华却已被换了魂了,这一个“春华”却是压根没半点的王道儒道这样的概念。
对她来说,不过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风水轮流转,皇帝轮流做。
思想上却是没半点的负担。
倒是在摇车里被人推着,将将要睡的时候想起,似乎世道不好的时候,经济会崩溃来着?
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来着?
前一世的时候,多少人被高涨的物价逼着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的?
坏了!
小女春华(二)
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来着?
前一世的时候,多少人被高涨的物价逼着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的?
坏了!
果然是坏大了!
董卓,董太师他抖着威风,废坏通行已久的汉五铢钱,改铸小钱流通。
本就是灾年,战乱,北方荒了许多的农田耕种,粮食产量减少,物价直涨。现在又改货币,经济的崩溃不说是直线,却也早受不住巨压了。
物价飞涨,货币不通,许多地方更吃不上饭,多了流民就多了混乱,有了混乱暴动,农田的产量又该下降,没东西吃又要产生流民,直接成了个恶循环。
哪怕春华自己政治经济学学得并不好,但也记得一战二战那会儿德国的经济大概。
这是在逼人流亡无家,逼□离子散。
在外面是都快不知饿死多少庶民,对张家来说,作为温县大族,虽不知饿死,日子却也过得紧巴巴的。
张氏夫妇也渐渐愁容苦面,唉声叹气,王道败落于民众的关系或许不大,谁做皇帝小民们并不放心上,但没饭吃了,才是叫人反朝廷不停搞起义的根源。
这时候,张汪也不再天天没事扮小资扮愤青,精忠报国也好帝王天下事也好,都抵不上全家三十来张嘴每天两顿饭重要。
终日唉声载道,好在初生的小女儿是越长越可爱了,也算是种安慰。
但事实上,大人吃不饱,就连这小女儿也受了连累,婴儿本该长得白胖才是好看,自家的女儿却也在这世道上常是吃不饱的,小小年纪也面色黄得和大人一样。
做父母的心里就更似剜肉了。
黍早是吃不上了,吃得也只能是糙粟就野菜这样的活着。
家中早有三个月未食过荤腥肉食了。
夫妻俩商量一番,只得招来全家并奴仆三十余人,内院裁人的事却是要夫人先打头。
山氏颇望了丈夫一眼,才说道:“当今之世众位都是见了的,咱们张家也不是个钟鸣鼎食的大族,愈发无法维持一族之生计。众位也是家里的老人了,便都说了实话,家里是难撑了的。你们不若自谋出路,这里是小县,到了大城中也有更多的生计可寻。张家也不妨阻了各位,今日若有想走的,便可将人契一同带走,另多结一月工钱。”
众人面面相觑,最后却是无一人走的,纷纷道,“小人等受主家恩惠,忠心耿耿,又岂会在此刻相离?”
虽然被众人奉承着表了番忠心,张氏夫妇却一点都不受这些好话,心里急得狠。
众奴婢心思也好猜。
乱世年头,出去了不是遇上兵灾就是流匪,去大城镇哪里是好去的?这一路途中就该饿死不知多少的人。
就算到了大城镇里,连自己所在的小县东家们都急着减人,大城内未必会有需要买奴婢的人家。
同样是个饿死,混在张家,至少是个老奴,主人家虽说养不起那么多人,饿肚子总比饿死的好。
没人肯走。
张氏夫妇更是急得都快满嘴生泡。
又在家主张汪亲自主持了第二次动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仍是换了一众“忠仆”的保证。
仍是没人愿意走。
最终张汪实在没办法,只得叫来账房显示家中早无余钱,锅中无余米。
效果却不显,仅走了一个原是张汪的妾,因仍青春美貌,便出去找寻旁家为妾。
张汪更是气闷,该给赶跑的未给赶走,却走了个他平日最宠的小老婆。
一时也心中无法排解,回房给妻子说了不少的好话,言道如“患难见真情”一类的酸话赞美糟糠为其“贤妻”。
山氏听着好笑,早些年也真是和这些妾们醋过一两回,然而此刻却真没心思计较这个,全想着的是如何减了下人。
这才是正经。
好话说尽了,客气着做却丝毫不见成效的,先礼后兵,山氏凑近丈夫说了主意,又怕他到底是书生意气,又从不接管过家里生计,不当家不知米贵。
谁知她丈夫听了却立刻是点头允了,“夫人果然是好计。”
山氏松了一口气,也真怕张汪来一句仁义大道的,倒是反衬得她像是个小人了。
过几日,家里渐渐流传出东家田产遭了秧,预备拿下人们的卖身契去换钱交上这年的税。
一听说要发卖人,众人便开始恍惚起来。
买人,不是说换个主子,张家是本地的士族大家,对下人也算温和,换个主子,又是从头开始,到了新的地方,原有主子的奴才又该一通的排挤。
况且在张家只要主子们还有口吃的,这些多年的下人们总还可以从中漏下点吃食。到了别家,那可真是被发作了苦工还没地方说的。
要是早走,哪怕是多领一个月的工钱也是好的。
出了这个谣言后,下一次都不用张汪自己亲自去动口说了,连日来总有下人到山氏夫人那里那卖身契。
到了几日后,原本三十多人的张家,现在一户仅止十一人。
张氏夫妇和小女儿春华,张汪的婶母宁氏,夫人山氏的乳母婆子姚妈,陪嫁丫鬟玉桂,张家原系的世代忠仆张贵与其妻子三人,张贵的老妻王氏是原本张汪的乳母,其子张兴是张汪随侍的小厮跑腿。
这些都是必留下来的人,就连原本张汪的三个妾在此事中却是全改嫁了的。
另有一对父子,儿子窦安是个跛脚汉,父亲窦老汉却已病得不成人形。
前几年年景还好的时候,张汪在其为官之时,一次外出,轿子行到市集的时候,见到一个跛脚汉给人驮货,几次被摔倒或是被人绊倒都毫无怨言的爬起,又重背了货在渡津口卸货。
辛苦不说,最后却被工头用借口连工钱都没领到。
隔天的时候再次经过,这跛脚汉却仍是背着货一步步艰难行走。
张汪便觉得奇怪,待听得他家中还有一对父母,更是叫人拿钱财接济他。
跛脚汉窦安却也不推辞就收下了。
纯粹是好奇,大少爷出身的张汪却是感了兴趣问他,“前度见你,那工头并不与你工钱,为何还为其做事?”
窦安答说,“纵然他戏弄于我,我却至少有得一处给我活干,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不发我工钱,但心情好的时候能得到他给工钱我就能养家。别处,看到我这个样子是不收我做工的。”
张汪遂觉得他是个老实肯干的人,又觉得他至孝之心可嘉,留在身边,自己也没给过差使,但平日却是府上谁都可以仗势欺辱的。明面上没差使,府上的脏活累活却都全是要他做的。
这样的一个人,在张汪带全家逃难的时候,自己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做了一辆简陋的推车,自己尚且一瘸一跛地推着双亲逃命。
其母在路途上熬不住死了,他大哭一场在晚上歇脚的时候,在野外给老母挖了地埋了,日子过得穷,破衣服都舍不得陪葬,乱世年头甚至都不敢上牌。
隔日红着眼推着生病的老父又逃命。
这场病后来一直不好,到今日主人家不得不裁人,老父还是病着,根由还是那场逃难。
张汪也是怜悯其遭遇,见了窦安却难开口让他走。
倒是窦安自己颇明白形势,先说了出来,“大人您当日收留小人,才有了小人父子今日。也不敢因此仗着您的体恤就要求什么,只是父亲病得厉害,当不得再挪动了,粮食工钱不乞主人恩舍,只请您好心让我父子在张家院外搭一处蓬。”
张汪更无法拒绝他,默认他在张家外搭蓬。
夫人山氏觉得奇怪,待从张汪口中得知事情来由后,也不免动了恻隐之心。
隔日让身边姚婆子拿了粮食接济。
怎料昔日在张家富裕的时候窦安并不辞张济的接济,这一刻却是拒绝了好意。
回道:“今日小人父子不过是徒然借主人家檐下一隅避风遮雨,若得了主人家的接济,小人绵薄之力终不及府上其余人,不敢当主人家的粟米,今日尚得一隅为吾父治疾,他人获怨,却连此一隅而不得。”
姚婆子原本去接济时确实是起了轻蔑心思的,但听了这番话后,却回去据实以报。
“夫人,”姚婆子道,“这人是个知道本分的人。”
山氏想想,“也是乱世中能生存的人了。”
这话说得不但周围婆子丫鬟惊讶起来,就连一旁被布带绑着腰学步的小儿春华也惊讶了。
窦安是个跛子,怎么会说他才是这乱世中能存活的人?
“得人恩惠,却是会看眼色,”山氏给女儿拨了下头上两边已经竖起羊角辫,也不知女儿会不会懂,说下去,“当日在府上富裕的时候受了接济,于府上却是不需计较的;但今日的一碗饭又怎和昔日可以相比。今日府上尚且常要减膳缩食,这一饭之恩可就大了。”
“他自度缺憾之体,能为府上做的不如其他下人,若贸然得了和众人一样的工钱饭食,是必要得怨的。到时获了怨被赶出,那他就连现在给老父遮雨的那片瓦都没了。”
山氏说完,也笑了起来,怎么和个小儿说起这个。
笑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