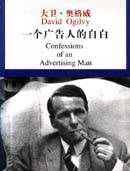这咬人的爱 [出书版完结]-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尽管他的忠诚,一钱不值。
当初文旭生想要孩子,我因工作所累,一直推辞。
结果他另辟蹊径。
如今,他也算求仁得仁,恋家的小娇妻,不久降世的孩子,离开我,他得到所有他想得到的。
我叹口气——
“何时举行婚礼?”我循例问道,“我查查我的时间表,不一定有空参加。”
“没有婚礼——”唐美妍脸上神色一黯,“旭生说,他已经举行过一次,没必要再铺张。而且他认为筹备婚礼太劳累繁琐,我身体吃不消。”
“哦!也对,举行婚礼是件极劳心劳力的事情。你现在身体较贵,确实不适合操劳。”我连忙劝慰她,“但是婚礼当天的敬酒,便可以让你脱一层皮。”
“可是——我从少女时代便开始憧憬穿着雪白的婚纱,与心爱的人一起步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那是女人一生最美的时刻。”唐美妍忍不住轻轻抱怨。
“那确实是一个女人最鼎盛的时刻,因为此后,他就委顿了,青春将消耗在繁琐而冗长的婚姻中。”我忍不住打击她。
“绍宜姐。你不觉得,婚礼是一个男人给女人的最大赞美?”唐美妍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不觉得。因为那个男人赞美过我以后,又转身赞美别人。”我故意同她开玩笑,她神经大条,并不觉得我在讽刺她。
“旭生可没准备赞美我。他一直觉得为我付出良多,甚至赔进了婚姻。所以,他不愿意妥协。他认为婚礼根本是虚礼。”
“他没有错啊。当年我与他也有过盛大的婚礼,但结果如何呢?所以婚姻与婚礼完全是两回事。”我尴尬地笑起来。“离婚后,单是处理那些结婚照片,便已经令人费神。”
“可是——有总比没有好。”她仍然不甘心,大地此生都要带着遗憾了。
是呀,每个女人都渴望身披嫁衣的那一刻,那是一个女人最踌躇满志的一刻。
明亮、温暖。充满喜悦,之后便将转入月亮的背光面。
从此以后,她就得学会接受现实。
我忽然想起十年前,文旭升生同我求婚的一幕。
那是我的生日聚会上,在一干同学的哄闹中,他忽然单膝跪下,拿出一枚小小的钻石戒指,涨红了脸求我嫁给他。
那时候,他那么年轻,工作刚刚起步,存款颇为有限,但他的眼神那么真诚,那么动人。
他说,请让我照顾你一生一世。
我在同学们的哄笑中,含羞点头,无名指上,风都能吹走的小钻石,重得仿佛承载了我一生的幸福。
那时候,我绝对没有想到,会有一天,我亲耳听见他与另一个女人的婚讯。
而且,心情如此平静。
真正让我心情不平静的是晋州的前妻卫欣。
她原本只同晋州保持了清浅如水的关系,只偶尔互相短信问候。
但自从她知道我的存在后,却一反常态。
然而,这反常也并不过火。
她只是每日必发一两条短信给晋州,言辞温婉有礼,无非是普通的关心与问候。
我也不便声张。
又是,她会突然现身“浮生”坐下来,静静坐在一角喝杯茶。
上门是客,晋州也做不到绝情地赶他走。
甚至少不了,还要上前寒暄几句。
其实她并没有上前打扰我们,相反还特别安静。
她已经尽量坐得远写,但又不会远倒我们看不见她。
她也并不主动上前同我们打招呼,反而越加静默,只用一双有缘的眼,脉脉地注视着晋州。
她仿佛只要她这样看着他,便能重新点燃他对她的感情。
有天我加班较晚,回到“浮生”已经快打烊了。
往日这时,只得晋州一个人静坐一角,安逸地看一卷闲书。
而此时,阁楼咯气氛诡异,有种刻意的安静,仿佛一万个人同时屏住呼吸。
晋州对面坐着一个女人。
他们之间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僵坐着,好似两个人融侨无比,但又各自固守一角,全身心在对抗对方的力量。
两人都没说话,甚至没有动,似乎时光凝固住这种抗衡的姿态,甚至眼神。
晋州微微后仰,一双眼静静注视着卫欣,目光笃定平和,却又那样矛盾。那眼中,有悲悯与不忍,也有包容和怜惜,还有一点点残忍和抗拒。仿佛他是俯瞰众生的佛,下一刻便要用舍身渡劫,挽救苍生的欲孽之苦。
而卫欣,则半佝偻着背,微微前倾,一双淡眉轻轻频拢,那双眼,那么暗,黯得近乎空洞。然其后,又有一把火,熊熊地,以决绝 的姿态从地狱深处燃烧而上。
那火势越来越大,几乎要蔓延到对面晋州的身上,我仿佛可以闻到他身上,蛋白质烧焦的气味。
我轻轻吸口气,竟然被这诡异的气氛所震慑,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木梯在我的脚下,不争气地发出轻微响动。
那咯吱声,细不可闻,却仿佛一枚顽石,投掷进了静水深潭之中,搅乱一池平衡,乱影分动,层层荡开。
那水波扫到晋州,他略侧过头看过来。
见是我,他目光一闪,明显长舒口气,却瞬时更加黯淡,像一锅水,沸腾到极致后,突然降为平静。双眸深处的烟火也渐渐灭了,茶霏之花开到尽头,寥落一地颓然残英。
她站起来,挽起沙发背上的大衣,低头走开。
走至楼梯口的时候,她抬头望了我一眼。
一双眼里,尽是死寂。
我看得心惊,指尖都不由掐进掌心。
然而只一眼,她已擦身而过,清浅足音一路向下,黑色衣角猎猎飞起,像一只寒鸦,挥动一身清寂,孤身地遁成一道暗影。
“她想同我复婚。”晋州仰头看向我。
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坐到他身后。
“你不问我怎么答她?”他握着我的手。
他手掌凉薄瘦长,指节明晰,但体温却是烫的,源源将是温暖注入我手心。
“我知道答案。”我回望向他,“我信你。”
晋州忽然叹口气道:“只是难为她了。我没想到,她至今还存着这份心。”
我想说两句玩笑话,但一想到那双清寂空洞的眼睛,便什么话也说不出。
我只是默默握紧晋州的手,将脸埋进他颈窝。
得借助他暖热的气息来令我平复刚才的惊动。
这天后,卫欣便仿佛真正消失了,像一滴水终于汇入大海,再也泛不起波澜。
然而,我心中始终像藏了一头怪兽,总觉得在某个时刻,蛰伏的它,会突然奋起反扑。
冬至那天,一早便开始下起细如碎末的雨。
清冷的雨,携着寒气,自早上淅淅沥沥到晚上,空气越发寒冷,呵气成霜。
我同晋州窝在我家书房中,将暖气开足。
我穿一件极薄的羊绒衫,赤足踩在地摊上。
我整个家中,最奢华的便是这条羊毛地毯,一踩上去,深深的羊毛便盖住脚背。
这是上个月,我同晋州逛街时发现的。
米灰色细羊毛,触手柔软温暖,令人想将整个身体都匍匐上去。
我当时忍不住脱了鞋,赤脚踩上去,整只脚顿时陷入了厚长的羊毛之中,我的心都软了。
但这张地毯价格不菲,我只能望而兴叹。
没想到过了两日,晋州便捧了它来敲我的房门。
而且一买便是两条,分别铺在书房与卧室。
这大概是我一声中收到的,最奢侈,最贴心的礼物了,暖暖踩在上面,整个冬天都在它面前融合了。
早上晋州来的时候,我还在睡觉。
打开门,他满身清寒站在门口,怀中是一大束粉紫色郁金香,花瓣上不知是雨还是露,晶莹得似一颗颗珠子,几乎已经冻结成冰粒。
但他唇角有好暖的笑容,春风一般扑向我,让冰冷都化为软水。
我不禁看得有些发呆,这好看的男人居然属于我了?
而我什么也没做。
“还没醒?”他含笑在我面前晃晃手。
“谁让你来这么早?”我尴尬地接话,因未睡醒,声音还朦胧微哑。
“今天冬至,太冻了,给自己放一天假,来你这里取暖。可容我进屋说话?”他故意哈口气,白霜便氤氲而开。
我这才醒悟过来,忙将他让进屋。
看他一脸坏笑地从头到脚盯着我看,我才恍然——
自己刚自床上仓促爬起来衣衫不整,发乱如鸟巢,满脸床单印,赶紧羞愧地扑进浴室沐浴洗漱。
幸亏他早在我家长驱直入,我也不当他是客人,自顾自敷了面膜救急,又沐浴洗发,最后伤了点极薄的淡妆,才肯从浴室出来。
一出浴室,满屋浓香,原来紧张正用文火为我煲着鲍鱼鸡丝粥。
他站在厨房里,往一只水晶瓶里插郁金香,拳头大的花朵,一看便是上品。
“几天前才松了我好大一束腊梅,今天又送郁金香,你准备在我家办画展吗?”我笑盈盈地走过去,将脸贴在他背上。
他的羊毛衫已经穿的很旧,正是最祝福的时候,脸贴上去,只觉得软。
“天寒地冻,有花养着,便觉春天不远了。”他的声音透过后背,嗡嗡传出来,震得我的耳朵微微有些痒。
因是冬至,晋州特意煲了一大锅当归生姜羊肉汤来驱寒。
晚上喝过奶白羊肉汤,饮了大枣姜茶去膻味,我们便窝进书房。
窗外冷雨不断,让人疑心这些雨下道一半会凝成冰帘。
我最爱在冷雨凄风的晚上,将暖气开得足足,营造出另一个世界。
晚上饮过羊肉汤,我便觉得浑身说不出的暖热舒适,仿佛血液里都流动着热气。
我端杯红酒,窝在他身前,与他同看一本《加菲猫全集》。
这套大开本的《加菲猫全集》,是我最宝贵的收藏,轻易不肯拿出来与人分享。
此刻我们也似加菲一般懒洋洋,音乐细碎地响着,偶尔传来窗外大风呼啸而过的喧嚣声,更显得一室静谧春暖。
因暖气开得足,瓷瓶里的素心腊梅被纷纷催开了,满室都是清幽的香味。
有晋州在,连腊梅的冷香也变得静暖。
正好一支曲子较为活泼,晋州便跳起来,拉我与他一同跳舞。
我赤脚踩在地摊上,厚软的羊毛,挠得我脚心微微发痒,晋州的脸近在眉睫,我抬眼看他。
唇边笑意还未凝住,他已经趋上前吻住我。
我唇上一暖,身子也跟着软了。
我爱煞他的唇舌间的柔软,他呼吸间清净的兰香味令人沉溺,享受单纯的肉体欢愉。
待我稍稍恢复几许清明,我们已经交卧在那软厚的地毯上。
我重重咬一下他的唇,轻笑道:“原来你送的地毯,别有目的。”
他眼睛明亮如星,情欲令他的声音暗哑低沉,越发令我心跳加快,“物有所值。卧室还有一块,可以再来一次。”
我忍不住大笑,“果然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他翻身压住我,低头吻我的颈侧。
晋州一向温文儒雅,非到这关键时刻,不流露他的野狐气质。
我紧紧搂住他的腰,攀紧他——
我真是幸运,在重创之后,以一个弃妇的身份,遇到如此良伴。
连垂垂老去的肉身与灵魂都得到双重慰藉。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晋州的手机不管不顾地响了起来。
在旖旎的静谧氛围中,那铃声突兀单调,令我的心无端跳起来。
果然——
晋州接起电话,我因一直贴着他,也听到电话里传来卫欣饮泣的声音,“晋州,是不是非要用这种方式,才能留住你?当年,你可以为了她离开我。现在,我也要让你为了我,离开她。我宁肯死,也要你记住我一辈子!”
接着,卫欣不断在电话里哀哀痛哭,言语混乱,似乎神志都有些不清了。
我和晋州相对一望,立即跳起来抓过衣服,胡乱套上,便狂奔出门。
我负责开车,晋州一边指路,一边在电话里柔声安慰卫欣,想尽量平稳她的情绪。
然而,无论他说什么,卫欣都已经听不进去了,她颠三倒四地说着话,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我脑中一片混乱,我只想着——
如果她死了,我和晋州也完了。
我一路将油门踩到底,脑子一片混沌。
十分钟后,晋州和我便赶到了。
无论怎么敲门,也没人回应,连电话也挂断了。
我的心不断下沉,仿佛那深渊永没尽头。
幸亏卫欣家住的苏式旧楼,阳台与阳台之间,有窄窄的一条台阶连着。
我们求邻居开门,让我们从阳台爬过去。
“你别跟来,危险。”晋州头也不回便阳台跨出。
然而,我内心如火在焚烧,只觉一股力量推着我非要跟进去,我也奋力爬过阳台,顺着巴掌宽的台阶,跟在他身后,向前移动。
七楼风大得厉害,我挂在阳台边沿,整个人仿佛随时都要被风吹走,
我却丝毫也不觉得怕。
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卫欣死。
晋州发现我 跟上来,不断回头嘱我小心,但是声音被风一吹,几乎听不清,黑暗中,我只看见他一双眼睛急得要滴出血来。
他先行爬上阳台,立即回身伸手拉住我,我跟着他翻上阳台。
顾不上说话,他脱下外套,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