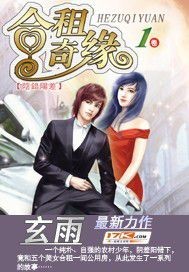两生缘-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首先,这里不是他熟悉的世界,从房内的摆设到男人身上的衣著均非他所见过的,即可窥知一二。
其次,他似乎投胎到了一具魂魄刚离体的肉体之上。肉体的原主──据这男人方才的说法──是因为遇到意外而受重伤,但显然除了程望秋自己以外,并无其他人知晓原主已魂归西天之事,俱只当他是受伤卧床休养。
最後,眼前的男人明显认识身体的原主,且至少有一定程度的交情。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男人能够不经通报便闯入房内。
程望秋心中暗叹,这情况看来不是轻易就能了结脱身的,有这麽多的眉角和难行之处,无怪乎鬼差们会认为这「两生」是张下下签,也无怪乎那位小姑娘要嚎啕大哭了──不仅得接续前人之命,一个弄不好极可能惹上无穷无尽的麻烦,还可能变成替前人收拾烂摊子的角色。
这下该如何是好?
现在才後悔换签什麽的已经太晚也没有意义了,程望秋只略作思考,电光石火的一瞬便对下一步棋该如何出招有了定夺。事事瞻前顾後、犹豫不决并非他的风格,与其将来的一举一动皆处处掣肘,不如从一开始就彻底坦白,主动进攻。
他试图动了动手脚,发现除了疼痛之外,活动上并没有有太大的困难,於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自己撑坐起来,又动手去拔那盖在他脸上的罩子。罩子用一个复杂的方法固定在他脸上,他摇了半天拿不下来,最後乾脆用蛮力硬扯。
从头到尾那个男人并不阻拦他也不出手帮忙,只是安安静静站在一旁,用饶富深意的目光研究著他的动作。
拔下罩子後他的呼吸总算顺畅了点。他清了清喉咙正想开口,男人却突然像是发现了什麽有趣的事情似地笑了起来。
不知为何,程望秋直觉地感到男人并非因为开心而笑,那好听的笑声里似乎还掺杂了某些异样的情绪。
「有什麽可笑的?」程望秋的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般的嘶哑,连他听了都很想命令自己闭嘴。
「你不是程子夏。你是谁?」男人笑盈盈地望著他道,语气里是不容置疑的肯定。
他的笑意没有到达眼底。
程望秋心一跳,面不改色地回道:「……在下程望秋,登楼远望的望,落叶知秋的秋。敢问公子如何称呼?」「程子夏去了哪里?」男人选择性地忽略了程望秋的问题。
「……在下无所知悉。」「你从哪里来的?」「自冥府投胎而来。」「所以你只是个跟程子夏毫无关系的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确实如此。」虽然听起来有点伤人,但实情就是这样。
男人点点头,一下子便敛起笑容。
两人沉默地对视片刻,男人迳自从旁抓过一张椅子在程望秋身边坐下,双手撑在膝上十指交叠,抿著唇像是在思考些什麽。
程望秋也不急,由得对方慢慢思考。这种时候多说什麽都是无益的,况且他才不会蠢到去问对方是怎麽发现自己并非原主的,那得多尴尬。
半晌,男人才像是下定什麽决心般,开口道:「我很欣赏你选择坦白相告的勇气。你看起来是个聪明人,我不想浪费时间绕圈子,所以有话就直说了。我说话可能会有点难听,但没有什麽恶意,还请你见谅。」程望秋点点头表示理解。
事实上,男人的态度已经比他预想中还要和平得多,至少是颇为冷静地在解决问题,而不是拿起扫把将他视为妖怪般扫地出门。这让他一开始对男人的印象稍微有些改观,毕竟以二十岁出头的年纪要做到如此沉稳,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既然你跟程子夏没有半点关系,那麽说实在话,我并不不打算和你有过多的牵扯。
」男人望著他道:「问题是,你现在占用著子夏的身体,我不得不管。我对你是人是鬼还是妖怪都不感兴趣,我也不在乎你来到这里的理由,但我不希望你拿子夏的身体去做些违法或惊世骇俗的事情。」程望秋听著心头直冒小火,偏又不好发作。说什麽「占用」程子夏的身体,他明明就是投胎来的,一切都按照冥府的规矩,虽然有偷偷换过签,但好歹也算是个合法的途径,这个人凭什麽说得他好像是窃取他人之物的小贼?
算了。程望秋深吸两口气,他都年纪一大把了,老人家不跟没见识的年轻小夥子计较,自降格调。
男人才不理会程望秋明显不爽的神色,继续道:「我和程子夏虽然是炮友,但也是朋友,所以即便他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也要确保他的身体不会被拿来胡搞瞎搞,这是朋友最起码的道义。」男人顿了顿,道:「从你之前的行为看得出来,你很明显地对这个世界并不熟悉,这样太危险了。我会用三个月的时间教会你在这个世界生存的基本知识和能力,三个月过後我们一拍两散,我也不会再管你的事,这样我对子夏至少就算是有尽一份心力了。」程望秋没听懂「炮友」是什麽,但他听懂了「朋友」两个字,於是心下稍安,便笑道:「这个提议甚好,初来乍到此地,对这里不甚熟悉,还有劳公子帮忙。」男人只是淡淡地道:「不用急著谢我,我并不是为了你才出手帮忙的。」程望秋也不在意他的态度,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能够得到帮助比什麽都重要,相形之下态度什麽的不过是浮云罢了。
虽然他有一点点──只有一点点──介意这个人在弄清楚他身分前後态度上极大的落差就是。那让他稍感失落。
「对了,我不管你是哪个时代投胎来的人,但我劝你最好改掉那种文诌诌的讲话方式。」见程望秋一脸的茫然,男人耐著性子开导他:「我们这里人说话不用之乎者也的,你那样子讲话很像是哪个过时的八点档古装剧的演员,出去会害子夏被人误认为是神经病的。」过时?什麽东西过时?八点档又是什麽?程望秋一头雾水又不好意思追问,但他半猜半理解可能是在要求自己说话要更俚俗一点,於是模棱两可地点头称是。
「知道就好。你躺著休息吧,我去帮你找护士来检查一下身体。」「呃,且慢!」程望秋急忙伸手拉住他的衣角,露出友好的笑容。「公……你、你还没告诉我贵姓大名?要怎麽称呼你?」「……我叫萧毓。锺灵毓秀的毓。」程望秋的笑容一下子僵在嘴边。
---程望秋:我和萧毓是炮友唷!(笑)萧毓:。。。。。。咳,他说的是碰友。
两生缘 (3)
***套用个程望秋几天前才刚习得的词汇,他近日来深受「代沟」与「文化隔阂」的困扰。
依照萧毓不负责任的翻译,所谓「代沟」是指因为年龄、身分地位等等因素而沟通不良,而像他们两人之间经常发生的鸡同鸭讲的状况,就叫做「文化隔阂」。但是程望秋完全分不清楚这两者之间有什麽区别,反正他觉得他和萧毓之间既有代沟又有文化隔阂,而这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和麻烦。
例如对於「程子夏」这个身分认同困难的问题。
其实说穿了,就是他对自己投胎的这具身体颇有意见。
程望秋想,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这辈子第一次踏进医院的厕所,就方寸大乱地把自己锁在里面闭门不出一个小时,最後被以为他发生什麽意外、破门而入的萧毓半拖半拉地带出厕所。
「正常人在厕所做蛋糕也不会花到一个小时,你在里面干嘛?厕所里的东西该怎麽用我不是都教过你了吗?」萧毓双手环胸,居高临下一脸不爽地瞪著他,脸上写满「你可以不要给我找麻烦吗」的表情。
为了那扇他不小心破坏掉的厕所门,他被迫听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医生长达半小时关於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长篇大论,还得付出四位数的赔偿金,那个肉痛啊。
「我的脸……」程望秋明显受到过大的打击,神情颓丧目光呆滞地喃喃自语。
「你说什麽?」「……我说,」程望秋突然转过头一脸悲愤地望著他,表情如丧考妣双目含泪,完全没有了先前成熟稳重的风范。「这是什麽脸啊!我无颜见江东父老了!」「子夏的脸哪里不好?你别忘了,这是程子夏的身体又不是你的。」萧毓不耐烦地掏掏耳朵,完全不懂他在纠结什麽。
「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年轻人懂什麽……」程望秋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边原地转圈圈边抱怨道:「我的胡子呢?我那把有『朝中第一美髯』封号的胡子呢?天啊,没有胡子我要怎麽见人?圣主在上,我精心保养了多年的美髯就这麽弃我而去了吗?」萧毓压根没听懂他在碎碎念什麽。
「而且!」程望秋一拐一拐站到萧毓面前,抓著自己那头挑染成金棕相间的头发问道:「我的头发为何是这种奇怪的颜色?这是某种异常的疾病吗?为何你的发色是如此正常的黑色?」「那是挑染,不是疾病。而且这颜色哪里奇怪啊?明明就好看得很。」萧毓撇撇嘴,可不敢告诉这位古板守旧的「老人家」,以前程子夏曾经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七彩霓虹灯,现在这个颜色还算保守得多了,不过估计说出来程望秋会更崩溃。
程望秋无言,他实在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人何以有如此奇特的审美观。不爱蓄须、不爱蓄发,把受之於父母的头发修剪得如此之短,又喜好在发丝之上大作文章,染成各种怪异的颜色,成何体统?且不论男性女性皆衣著轻便,大方地裸露胸膛、手臂和双腿,这种在他原本的世界是何等惊世骇俗的事情,这里的人却都习以为常安之若素。
虽然说入境随俗,但过大的「文化隔阂」著实叫他这位老人家的心脏有些吃不消。
程望秋回想一小时前在厕所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样貌时,几乎连自杀回冥府重新投胎的冲动都有了。一张漂亮的鹅蛋脸、两弯浓密新月眉,过分苍白但毫无瑕疵的脸蛋上水灵灵的一对猫儿眼,额前碎发修剪成一个斜斜的弧度,半长不短、金棕相间的发丝凌乱地披散在脸颊和肩上,整个人看起来说有多无辜就有多无辜。虽然略显女气了些,不过不得不承认程子夏确实生得一副好样貌,比他从前见过的京城名妓、最富盛名的青楼「一晌贪欢」里的花魁何素春还精致得多。
但好看归好看,问题他程望秋前世是个武将,是名威天下的宁远大将军啊!堂堂八尺壮汉一下子变成了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小白兔,这差距大得让程望秋一时半会难以接受。
遥想当年,他宁远大将军威震四海,身骑战马披坚执锐,何等的英姿焕发!那不怒自威的气势,只要一个眼神就能吓得对方双腿发软,而现在呢?程望秋试著眯起眼对镜子里的自己露出个凌厉凶狠的眼神,但怎麽看都像是在抛媚眼儿,半点威严都没有。
萧毓无法理解程望秋快要崩溃的心情,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云淡风轻地道:「别抱怨了,子夏可是大家公认的美男子,你已经算是很幸运了,别不知足。」「……」又例如萧毓对於情爱和床第之事开放得不可思议的态度。
出院後,程望秋住进了萧毓的房子,萧毓还好心地清出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给他当作客房。
某天深夜,早早便就寝的程望秋被客厅的开门声和交谈声吵醒。他睡眼惺忪地揉了揉眼睛,哈欠连连打开房门查看,就看见萧毓搂著一名眉清目秀、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年轻男子,两人在玄关处耳厮鬓磨打的正火热,言词放荡露骨得连他听了都耳根子发烫。
萧毓和那名年轻男子肢体纠缠著进了房间,程望秋隔得远远的都还闻得到他们身上的酒味。过没多久,一声高过一声销魂的呻吟,间或夹杂著暧昧模糊的喘息透过隔音效果不甚佳的墙壁传来,羞得他面红耳赤。
男人的呻吟不似女人般娇软,略微低沉沙哑的嗓音却轻易地便撩拨起人心,像猫咪的爪子轻轻挠啊挠的,挠得程望秋整晚都没睡好,翻来覆去直到快凌晨才入睡。
隔日果然睡迟了。他盥洗妥当时,萧毓早已经起床多时,正在餐桌旁吃著早餐配报纸,家里到处都没看到昨晚那位五彩缤纷的年轻男子。
「你在找什麽?」萧毓皱起眉头看著程望秋四处张望的动作。
「昨晚那名……呃,男子呢?」「喔,你看到啦?他一大早就回去了。」萧毓的口吻轻松得像是在谈论今天的天气一样。
程望秋觑著他的脸色,捡著字眼小心翼翼地问道:「呃……你、那个……有龙阳之好吗?」「蛤?」萧毓先是一愣,想了一会儿才想起龙阳之好是什麽意思,接著便很大方地点点头:「是啊,我喜欢男人。」他这麽坦率承认的态度让程望秋很是讶异,忍不住脱口而出道:「这种事情是可以这麽光明正大地承认的吗?你都不会因此感到羞赧吗?」「为什麽要感到羞耻?我又不犯法,而且多的是跟我一样的人。」萧毓耸耸肩。
「可是那不是……不正常的吗?」程望秋想起某些很不好的回忆。
「哪里不正常,人各有所好而已,谁规定男人就只能喜欢女人?」萧毓喝了口咖啡,慢条斯理地道:「有句话怎麽说的?『有些人喜欢啃鲍鱼,而我偏偏喜欢咬肉棒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