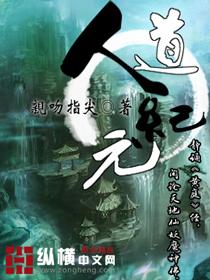橡皮人-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跟我握了握手,推起旁边支着的一辆自行车,带我走向广场四周密密麻麻、黑黝黝、迷宫般的小巷子。进了小巷子,他飞身上车,我紧抱着包坐上后座。自行车左拐右拐,蹬得飞快。这城市在东汉末年便是有名的军事重镇,历史上几次著名战役就是在这一带打的。一千五六百年过去了,这儿衰微颓败了。城里看不到任何的价值的古迹,也很少新式大厦,到处是百余年来为应付迅速膨胀的人口匆心建造的低矮丑陋的平房。特别是的十年来人们自己用碎砖、木板、油毡为新婚夫妇搭起的违章建筑,独食了街道,绿地,使道路弯弯曲曲。城市显得杂乱无章,天亮起来,街上出现一些衣衫不整、土头土脑的行人。老邱把车停下,问旬不是有点冷,我哆嗦着承认。
“喝碗馄饨吧,热乎热乎。”
“还远呢?”我随他走地路进一个卖小吃的棚子问。“不远了。”他叫了四碗馄饨,从一个肮脏的铁皮匣中拿出两双粗糙的木筷,比比齐,递给我一双。“凑和吃点,这儿的东西什么都变味了,就馄饨还行。”
棚子里大锅升腾起弥漫的蒸汽,围裙污垢油腻我服务员端来滚烫的鸡丝馄饨,凉风一吹,碗上凝了一层油脂。我往馄饨里放了少辣椒糊,把油汪汪、红乎乎的两碗馄饨都囫囵吞了下去。
“人和杨金丽挺熟?老邱递给我一支烟。
“可以,”我说,“一般吧。”
“我和她不错,徐光涛张燕生我也都认识。汽车真有吧?”
“他们说有那就是有,不过我也没见着,估计应该有。”我把烟点上。
老邱呆着脸抽了几口烟,对我说:“过会儿你见着老蒋说话留点神。别说什么‘估计应该有’,就说有,车就在那儿等着呢,你见着车了,车就是你经手买的,什么事都妥了专等钱了!得把话砸实了,否则你模棱两可,这土财主就缩了。”
“他要细问呢?”
“侃呗,谄呗,胡说八道会不会?”
“倒是会一点。”
“这就结了。不会这个你出来干么?不会这个什么事能干成?就这么回事,为什么都是假的,掏出银子来是真的。”
老邱阴着脸,我低头哼哼一笑。
我记得后来我一见老蒋就认了他个“大哥”。巧舌如簧,又打又拉,在一间肮脏下流的小酒馆里用劣质自酒把他灌得烂醉,拽着他脖领子拖去银行提款。我想起他那会儿也许把我当成了福特本人,而他自己则是我同父异母,名副其实的“大哥”——大款哥。
那天晚上天很黑,马路上灯火阑珊。商店都关门了板,街上早早就没了人,只有风阵阵吹过空荡荡的马路,就象吹过寂静的旷野。我昏头涨脑跟着黑煞神似的老邱钻地了迷宫般纵横交错的小巷子,擦着低矮乌热的屋檐走。隔很远才有一根木电杆,吊着盏昏黄的路灯。路宇下多有大堆的垃圾,垃圾堆后在的黑暗暗处忽明忽灭地闪着向颗红红的烟头,走近可以看出几个少年沉默的轮廓。很多路灯都不亮,我们基本上是凭借依稀的星光走黑道。时间不算得晚。绝大多数人家却都熄灯上床,只有看到夜色下紧紧挨挨,层层叠叠地无数小屋,你才会想到近在咫尺的周围迸息静卧着成千上万的人。
在一个不亮的灯灯杆旁,老邱停下来,让我扶着车,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垃圾堆。我极力往黑糊糊的垃圾堆后看,看出那儿站着个人。老邱过去嘀嘀咕咕不知同那人说什么,一会儿,搂着那个出来,走到跟前我才看出是个女孩儿。我们继续往前走,道越发窄了。地上还净是土坷垃碎砖头,走得入磕磕绊绊。终于豁然开朗,我们走出鬼域般的旧城区。一条相当宽阔、路灯齐全的大马路横亘眼前,路边有几幢一模一样的简易楼,马路对面似乎是新建工地,盖了很多半截楼房,工地后面是昏暗的大片田地,这儿已经是郊区了。老邱指给我看马路尽头一座稍明亮些的建筑,说那就是火车站,我已完全转了向,甚至不能相信那就是我来时的那个车站,老邱说就是它。
老邱家在那几幢简易楼里的一幢,一间屋,一张床,我们三个就挤在那张床上。黑暗中,我听到老邱说:“那车,别给老蒋!”
一个身着西装,丰腴庄重,灿若银盘的脸上有着双黑色大眼睛的女人出现在餐厅门口,矜持伫立,款款扫视大厅。当她看到我,我做了个鬼脸。张燕生见状回头一看,立刻竖起胳矛喊那个女人。又对我调侃:“有戏呀,一下就认出来了。”
“那么大个砣放在那儿,狗熊也看得见。”
李白玲笑吟吟,一步三摇地走过来,徐光涛和张燕生笑容可掬地用欣赏的目光迎候她,仿佛在看时装表演。
“你怎么才来?”张燕生殷勤地拉开为她留着的椅子,给她介绍我和老蒋。李白玲看了我一眼,问张燕生:“给你联系的房间住上了吗?”
“住上了。”“条件怎么样?”
“还可以,就是客房服务员不漂亮。”
“这我可无能为力。”
餐厅女招待推着银闪闪的餐车来上酒菜,她显然认识李白玲,冲李白玲一笑,李白玲也亲热一笑,支使她拿些冰块来,女招待连连点头答应。女招待开了酒瓶塞,在每人的玻璃杯里斟了酒,退下去,我们吃喝起来。张燕生,徐光涛相当活跃地竟相向李白玲敬酒调笑,李白玲左右逢源,酬酢自如。我知道李白玲在此进个神通人大的人物,我们此行一切食宿都是张燕生通过她安排的。这女方浑身魅力,特别是那双黑眼睛,视界极宽。不管她仰脸嬉笑,还是低首啜酒,我总感到一缕视线不轻不重地落在我身上,沉静有如一个人在幕后不动声色地打量我。
“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她忽而转向我问。
“嗯。”
“看上去他挺老实的。”她对张燕生、徐光涛说,“跟你们不一样。”
“老实屁!”张燕生说,“数他坏,整个一个阶级敌人,全是装的。”
“是吗?”李白玲感兴趣地望着我。
“还是有应该相信你的第一印象,这是有目共睹的。”
“你非常象我认识的一个人。”李白玲明显带有好感地对我说。
“也许我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再好好看看。”我嬉皮笑脸。”
“不,她是个女孩儿。”
张燕生和徐光涛不怀好意地吃笑,我也笑,不再说话继续喝酒。
“为什么中国男人雌化现象这么普遍,嗯,为什么?”
我孟浪饮酒,脑浆都沸腾了,听到李白玲对的张燕生的感慨,愤然插话:“因为中国女人先于男人普遍雄化。
李白玲微笑地看着我。
我强自镇定地坐着。“你也非常象我认识的一个人。”
“是吗?”她盅了口酒,笑着说:你大概要报复我了。”
“不是中国人。”
“噢,”李白玲沉着地说,“我倒是有八分之一的外国血统。
我祖上有不在北京做官,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来,烧杀奸淫。”
我终于坚持不住了,酒性上来了,心脏象小喷泉似的突突跳跃,站起来喃喃说:“我说的是个黑人,一个胖胖的非洲姐妹。”
我走出餐厅。
电梯骤然下降时,酒物已经涌出,我竭力将全部内容含在嘴里。进了房间,我立刻冲进卫生间大吐特吐,唉哟哟地呻吟,大声喘气,象是刚被人痛打一顿。吐了又吐,最后终于吐干净,我干噎着把马桶冲了,用淋浴喷头冲净地上的残渍,漱了口出来,愣心地坐在沙发上,一闭眼就感到天旋地转,象被儿童一鞭接一鞭抽打的陀螺。电话铃响了,我拿起来挂上。片刻,李白玲推门进来。
“滚你妈的滚你妈的!”
“你怎么啦?喝晕了?”
“滚你妈的,少在这儿装大尾巴狼。”我趔趄扑过去,粗暴地往门外推她,“我不在上面吃饭,下来干么?”
李白玲掰开我抓住她胳膊的手,有力不失分寸地把我推回沙发。
“你醉了,喝这么点酒就醉了,吐得满屋子是味。”
她走到桌旁沏了杯酽茶,塞到我手里,让我喝,又拧了条凉毛巾给我擦脸。
“好点了吗?”
“好点了,谢谢。”我头脑清醒了,对她说:“你回去吧,说我没事,一会儿我就上去。”
“我还是陪着你吧。你跟我说话,一散一下注意力,就不会头晕了。”
“这是正常的——喝醉,不醉我反而不舒服。要的就是这感觉。”
“你这是变态。”
“不不,我跟别人不太一样,你了解我你就会知道——你不能用世俗的眼光看。”
“啊!”李白玲笑过来。“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怎么,又是一个!还有方便?”
“我,你没看出来?我对人我的胡言乱语不是一点都没吃惊。”“你一说我倒看出来了,你的确有点硕大无朋,特别是眼和——脸。”
李白玲先是一笑后是一板:“留着你的刻薄话形容形容自己吧。你既然能指人了那就是恢复正常了。咱们是不是若无其事地上去,不能叫那些俗人看咱们笑话对吗?”
“对的。”
在走廊里,李白玲挽住我,我感激地冲她一笑。回到餐厅杯盘狼藉的桌旁。燕生问我:“和以桶亲嘴去了?”
“没有。”
“那和李白玲亲嘴去了?”
“是!”我大笑望着李白玲,李白玲也笑。
“真没事?”徐光涛问。
“没事。”李白玲替我回答,他看见一漂亮姑娘,就满酒店尾随人家,我找到他时,他正和人家纠缠不休,非说人家心事。”
“光涛,如果你能把车给我留一礼拜,我给你五千块钱。”
我们这顿马拉松似的饭终于吃完了,老蒋付饭钱时都快哭了。步出餐厅时,我和徐光涛走在后面。
“不是我要,是我的一个朋友要,可他非得一个星期后才能诳出钱,不瞒你,就是那边的联系人老邱。”
徐光涛手里玩着烟,增晌不语好一会儿才说:“一个星期怕是留不住。他们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要车的人很多,抢得打破头。”
“所以想让你用老蒋的钱先垫上,他的钱不是已经入了你的帐户?”
徐光涛笑起来,暖昧地沉默。
“实说吧,老邱答应给我一万,我分你五千,绝对没打埋伏。老蒋答应给你多少钱?瞧他那枢鼻缩眼样儿,打他的钱比你胗子打蛔虫都难。”
“我相信你,咱们有的说吗?”徐光涛说,“不说别的,看哥儿们面我答应你。不过一周内你们一定要把车款汇来,免得坐蜡。”
“那是一定,我跟你一起去边境,没钱你把汇进帐户。谢谢光涛,我早知道你仗义。”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谢谢?听这意思是要害我。”
“去你的王八蛋,不答应弄出你尿来。”
“这话听着亲切多了。”
“老李。”我快步撵上正亲密地张燕生交头接耳谈笑的李白玲,从中间把他们分开,问李白玲附近哪有邮局。
“跟我一起走吧,我正好也要回单位办点事。”她说,“我带你去。”
”你就别去了。”我说燕生,“怪碍事的。”
“我不是去。”燕生笑着说,“我回去睡觉去,我和老蒋哥儿们。”他把老蒋拉过来,搭着他的肩象狐狸阿媳妇搂着灰兔小朋友。
“别把头睡扁了,”李白玲冲他背影喊,“那就不帅了。”
酒店门口,计程车一辆接一辆驶来,开走。我和李白玲钻进一辆车,计程车驶出酒店庭院,开上马路,李白玲告诉司机要去我地方。
“先到我单位去,回来再送你去邮局。”
“随你大小便。”我往后一仰,“你在什么单位?”
李白玲说了家著名大公司的名称,补充告诉我,她是那家合资企业驻当地办事处的副经理。
“怪不得你路子野,大家都求你。”
“就那回事,都是利用。以后,”她看看我说,“你有什么事我也可以帮你办。”
“你真是个热心肠。”
那倒也不是。只不过我这个愿意交朋友,省得一个人孤单单挺无聊。”
她笑吟吟地年喜新厌旧我,我也笑吟吟地看着她。好说:
“好孩子。”
汽车停在一幢新建的盒式大厦门口,李白玲边下车边问我:
“和我一起上去吗?去我办公室看看。”
“不啦,我说,“司机该不放心了,我在车里等。
“那好,我马上下来。”
李白玲消逝在大厦的自动门内,我敬司机一动烟,和他聊起来。司机听说我是第一次出门的北方农村人,优越感立刻暴露无遗,很自豪地历数该城市和种种发达和文明,我竭力装得象个不傻瓜。李白玲回来时,正好听到司机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肉的香糯、鼠肉的高蛋白的肉拓的焦脆。
“我去你们北米,菜做得真难吃。”司机把车开上马路,还在不停地唠叨,“肉烧得稀烂,又拼命放酱油,咸死人吃不惯。”
“你不知道呢,我们北方的猪是吃屎长大的。”
“哇!”
“连我也不爱吃。可是,你吃你我们北方的唧鸟猴吗?”
“那是什么?”
“也是一种高蛋白的动物,金丝猴的亲戚。”
李白玲拧我一把,笑着说:“你瞧不惯我们这儿的人,也用不着这么愚弄人家。”
我捏了捏李白玲的手:“我喜欢你们这儿的人才说,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