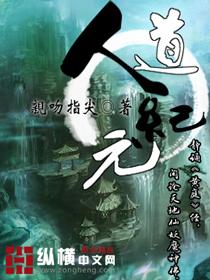橡皮人-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早晨,张燕生回来了。一进门还挺乐呵,看来昨晚过得挺惬意,问我睡和怎么样。
“挺香。”我瓮声瓮气地回答,“就是半夜你的两个朋友来找过你。”
“谁?阿芸和阿豆?”
“不,胖胖和瘦瘦。”“什么胖胖瘦瘦,”张燕生摸不着头脑地说,“我不认识。”
“他们认识你——警察。”
“别开玩笑。”
“玩哪门子玩笑,昨晚警察来抄了。”
“真的?”燕生登时紧张了,“他们来找我?”
“没有,跟你说着玩呢。找你干吗,你又不是他们局长。”
“说真的说真的,警察真来过了?”
“真来过了,杨金丽把他们领来的,大概她被他们堵被窝了,就胡说走错了门,来找咱们的。没事,警察搜了一遍,咱们也没什么走私物品,了不起把咱们当成皮条客了。”
“你别大意,当成皮条客也够咱们喝一壶的。”
“那我倒不怕,没有的事,安也安不上。”
“警察还问什么啦?”
“没问什么,就问你哪儿去了,我说你办事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他们扣了我证件,把杨金丽带走了,还说随时再来。”
“随时再来?”燕生刚坐下又“蹭”地站起来,“这地方不能呆了。”
我和燕生乘的计程车驶出车流,靠边停在一个规模宏伟的红色陵园门,马路对面就是李白玲上班那幢钢筋水泥和玻璃组成的盒式大厦。我进陵园找了张长椅坐下,燕生去给李白玲打电话。一会儿工夫,李白玲匆匆而来。我把昨晚的事对李白玲讲了一遍。李白玲听完哦吟片刻,问我:“他们扣了你的证件,你能溜吗?”
“那证件是作废的,要不要都无所谓,我有些担心的是那个电话号码本。”这时我蓦地想起,昨天我曾把暗记下来的李白玲的电话号码写在上了面。
“上面有谁的电话?”
“噢,那都是过去一些熟人的电话。”
“有我的吗?”李白玲看燕生。
“我没把你的电话告诉过他。”燕生说。
“没有。”我也说。
“那就没有什么。”李白玲松了口气,“我给你们换了个住处,溜了完了。”
“可是,”我想了想,还是得告诉他们,“我给老邱的地址也是这个酒钻。”
“他是谁?”
“他来干什么?”燕生问我,“老邱来干么?那个二混子。”
“……他也是来买车的。”
“你没告诉过我。”燕生怀疑地看我。
“现在告你不晚。”
“马上打长途通知他来得及吗?”李白玲说,“告诉他换地方。”
“恐怕来不及。”我说,“前天不是我们一起打的电报?他现在已经在路上了。要我说其实没什么,燕生另找个地方住去。我还回去等,没事。十处是不是治安处?”我问李白玲。
“不知道,不过我可以打电话找个公安局的朋友问一下。”
“你问一下,要是治安处就没事,不就是风纪上的小事吗。”
“好吧。”
我们三个来到陵园门口的公用电话处,李白玲给她的警察朋友打电话,打完电话她脸色大变。
…十处是经济保卫处。”
我和燕生正在酒店房间里收拾东西,门上传来猛烈的叩敲声。燕生迅速钻进卫生间,我把皮包塞进床下。坐到沙发上喊:“进来。”
门开了,老邱昂首阔步走进来。
我松了口气,喊燕生出来,弯腰拖出皮包继续往里塞衣服。燕生心有余悸他走出来,认出老邱,咧嘴一笑:“是你,吓我一跳。”
“出了什么事?”老邱看我们惶惶的神情,诧异地问。
“警察刚来抄过,而且随时还会再来。”
“这儿警察那么凶?”
“凶,凶得跟郎平似的。”我扣好皮包,走过去老邱说:
“你白来了,那事吹了,徐光涛的车没了。”
“怎么回事?”老邱立刻急了,“那你他妈的给我拍什么电报?”
“这情况我也是刚知道。”我有气无力地掏出烟请老邱,老邱抽出一根叼上,我给他点着火。
“彩电呢?”他喷着烟问,“你联系没有?”
“联系了,可我们已经叫警察注意上了,那事该怎么办?
你用公家的汽车款倒电视,不正找人家逮吗?”
“谁捅的漏子?你们办事怎么这么不牢靠。”
“我猜是老蒋,他发现上当就报了官。”
“连这么个笨蛋你们都瞒哄不住,干什么吃的!”
哼。”我看了眼燕生,“这事一时也说不清楚。”
“是不是老蒋报的官还没定呢。”燕生说。
“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老邱往沙发上一坐,“我不管,你他妈给我想办法去搞车,搞彩电。”
“我他妈没办法!”我挥着手说,“警察张着网呢,你让我乍着毛往里钻?”
“合着你打着晃涮爷们玩呐!”
“我还不知道谁涮了。”“你们别在这儿吵。”燕生拎着收拾好的皮包过来说,“先撤,有什么话回头说,别让警察一块捂了。带着钱吗?带着钱什么话都好说。”
“好吧。”我对都邱说,“你先跟燕生走,待会儿咱们再商量。
我再跟徐光涛联系一下,探探究竟,看老蒋到底是个什么鸟。只要他没报官,事情还有缓。”
“反正,你看着办吧。”老邱把烟头嗖地扔到地毯上,凶脸地看了我一眼。
我自个儿以房间里从了会儿,最后检查了遍房间,看没丢下什么东西。就带上门出来。正想不惹人注意地通过服务台忽听服务员叫我:“喂。”
我停下看她,服务员一脸笑容,旁边坐着的另一个服务员姑娘也在冲我乐。她们问我:”昨天警察找你啦?”
“是啊。”我立刻装出了副清白无辜受了冤枉了的样儿,“我正好端端地象个乖孩子一样睡着觉,人就突然闯进来,搜身又讯问。是你们给开的门吧?”
“警察叫开门,我们敢不开吗?”服务员笑说。
“也是,这年头,好人也难免受冤枉。”
“我得了吧。”坐着的那个姑娘笑着说,“谁叫你和那个坏女人一块混的,沾包了吧。”
“我哪知道她是坏女人。从小我就认识她,中学起她就是我们班的团支书,在这儿碰上了,你说能不打个招呼?谁想她变成了坏人。”
“都会说,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你瞧我长得象坏人吗?多么忠厚善良的脸,对谁都是那么诚恳、谦逊。”
“越说自己好的人越不好。”两个姑娘笑的咯咯的。
一个姑娘好心忠告我:“你不是坏人,可你要小心坏人。
特别在我们这样的酒店里,什么没有?就拿住在你斜对面房间的那个港客老头说吧,别瞧他道貌岸然,听民岸然,听民警说,他坏透了,专往国走私,在香港也是社会渣滓。”
“你是说老和杨金丽在一起的那个老头?”
“就是那个坏老头。那么老了,还骗人家女孩子,真不要脸。民警说,要重重罚他,把他的护照都扣了。”
“光罚还不够,”我沉思地说,“应该拖出去毙了老家伙。
好啦,我下去吃点东西。”
我离开服务台,乘电梯下楼,降下两层,停了电梯出来,没安全楼梯又走上去。小心翼翼地避开服务台两个姑娘的视界,蹑手蹑脚走到那个老港客的房间,没敲门就拧把手进去了。老坏蛋正穿了件睡衣坐在沙发上喝茶,看到我进来一愣:
“你找谁?”
“找你。”我往他旁边的沙发上一坐。
老家伙放下茶杯,打量着我:“唔,是你,杨小姐的朋友,又想换港币吗?”
“不,想跟你谈点事。昨天,你和杨小姐的事连累了我。”
“是呀,”老家伙愤愤不平地说起来,“内地的警察太不讲道理了。杨小姐在我这里坐了一坐。就在罚我的钱,坐一坐也要罚钱,真是闻所未闻。怎么,也要罚你吗?这可没有我的关系。”
“要不是你,警察也找不上我。”
“这我可不能负责。你是要叫我替你付罚金吗?不行。”老家伙急了,用广东话连嚷带叫,“没有这个道理。”
“我不是那个意思大地我的意思是因为你们的事连累了我,我们也算有了缘份,好不好做点买卖?我听说你是个很有办法的人,能搞到价格合理的电视机。”
“什么意思?”老家伙眼睛骨碌碌转了几圈,“你要买电视机?”
“是的,不多,一小批。”
“市场上有哇,要多少你尽管去买好啦,打我干吗?”
“你看,老先生。”我慢条斯理地说,“我开始提到杨小姐,意思就是我们之间用不着搞什么遮遮掩掩的把戏,你的情况杨小姐跟我讲了许多,我呢,想你也能意会到。大家开城布公。都是买卖人,谁也不想占谁的便宜,按规矩办,现钱现货,大家得利,你说呢?我也不是来敲诈你,也不是给警察当探子给你设圈套,只是正经八百想跟你谈桩生意。怎么样,谈不谈呢?”
老家伙又端起茶杯吸吸溜喝茶。喝了一阵,放下茶杯,打烟。我敬了他一支,给他点上火。
“那么,”老家伙开了口,“你想要多少台?”
“先问一下,你是什么价?”
老家伙说了个数,我一听说不行。
“都是这个价啦。”
“咱们别来这套行不行?都是明白人,大家痛快点。你价格合适,我多要你一些。”
老家伙又报了价,降了一些,我仍觉得高。
老家伙端起茶杯:“我这已经是最低价了,再落我要蚀本了。你说个价?”
我说了个数,老家伙一听直摆手,“不谈了,我们不要谈了。哪有这个价,有这个价我买你的。”
我把价提到一个整数,老家伙扔是摇手。
“怎么着?”
“不谈了!”老家伙斩打截铁,“你找别人买去吧。”
“嘿,老东西。”我站起来,“不谈了?我让你进得来出不去你信不信?”
老家伙面无惧色,嘿嘿怪笑:“我们这是做买卖吗?我又是不小孩子,你也不要虚张声势。”
“妈的老流氓!我虚张声势?我也不是不了解你,不就是六○年饿跑的乡下佬吗,番薯屎还没拉干净,装什么大哼。我一个电话就能叫公安抓了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香港是干吗的,香港警方知道你被抓了,会高兴得拍贺电。一句话,你想不想要你的护照了?”
如果说我前面的确是在虚张声势,老家伙听着毫不为其所动,这最后一句却击中了要害。尽管老家伙仍面无表情,但我肯定,他搞不清我是什么来头了,起码他要猜猜。一般说,上了年纪的人,权衡某件事的利弊时,是会慎重斟酌每种哪怕是很微小的可能,他们没有精力冒险。果然,老东西虽说嘴没软,话里已经透出转圜的意思。
“你不要唬人,我是不吃唬的。我对国内的情形有一些了解,我相信你不是普通人,但要搞我,也没那么容易,我也是认识一些人的。再说,做买卖也没有强买强卖的。”
“那好,”我不再恫吓老头,接着他最后那句话说,“咱们再互相让点步,你尺寸上可以小一点,我价钱上给你凑个整。”
我和老家伙又诗价还价一番,最后达成妥协。由于每台价格比我原来设想的最低价格还要低一些,老家伙提出交货只能在那地更靠南的沿海城市,我也一口答应了。我们约定了具体的交货地眯,时间定为后天起的连续三天内。
“听着,”老家伙伸了只干瘦的手指说,“如果我不能及时拿回我的护照,我便不能履约。”
“放心,老先生,我保证你最迟后天拿到护照。当然,你也不别心疼那几个罚金,就当为‘四化’做贡献吧。”
我心里有底,警察只要罚了款,会很快发还护照的。
我穿过酒店大厅时迎面看到姓马的胖警察和小个子警察从自动门进来,连忙隐在几个胖胖高大、香气扑鼻的外国妇女身后,低头装作浏览柜台里的烟酒化妆品。两个警察行色匆匆没看到我,从我身后熙攘的人群中穿过,消逝在电梯间。
我拔脚出了酒店,叫过来一辆计程车,让司机开到陵园。中处,我坐在疾驶的轿车后座想,我这是玩玄呢。警察兄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象秃鹫一样敏感,哪儿死尸腐肉,隔着十万八千里也会凭直觉扑下来。
计程车到了陵园附近一个街角,我付了钱下来,步行走进陵园大门。天下起小雨,陵园内的松柏草坪一片浓缘,玉兰树在雨中静静开放着硕大雪白的花朵,树荫下的长椅都打湿了,渺无人迹。我找了一圈,没发现张燕生们,身上已经潮了,便沿着漫长宽阔的台阶走向山坡上的纪念雕像。这里组用巨大粗糙的花岗是凿砍的剑拔弩张的人物群像。半个世纪前,这个城市曾发生过一次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许多外国革命者的血和中国共产党员、工农群众的血流在了一起。中学时,就我从课本中了解了这次著名的起义。即使此时此地,我在为理想献身的烈士英魂面前不由肃然起敬。望着那些无声地呐喊着搏战着的巨人们,我一阵阵发呆,竟忘了来此何干,直到一个人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我才猛醒过来。倏转身,李白玲笑嘻嘻站在我面前。
“你没带警察来吧?”
“……”
“你怎么啦?”
“燕生他们呢?”
“他们先走了,留我在这等你。大家看你那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