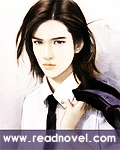岁月是朵两生花完结+番外-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点头道:“啊,好。”
此后两相无话,程嘉木一直蹙眉沉思,如入无人之境,周越越几次把毛背心拿出来,又默默收了回去。他丝毫没有要回自己座位的意思,我和周越越不好说话,只能通过眼神交流。
周越越用眼神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用眼神回答他:“没事儿没事儿,等他人走了我再跟你解释。”
颜朗从兜里摸啊摸啊摸出一副扑克牌来,吸了吸鼻子道:“我们来玩会儿扑克牌吧。”
周越越艰难地推开颜朗的扑克牌,斜眼觑了觑程嘉木,佯装正直道:“玩牌多低级趣味啊,我们来聊聊人生啊人性啊什么的吧。”
颜朗头也没抬:“这年头都聊生人呢,谁聊人生啊。倒是可以聊聊人性,先聊聊人,再聊聊性。”
周越越指着颜朗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看着颜朗只觉得头皮发麻,忍耐半天道:“谁教你的。”
颜朗无辜道:“爸爸。”
我说:“你不是一直喊干爹么?爸爸也是可以随便叫的?”
颜朗不耐烦道:“称呼而已嘛。”
程嘉木瞟了他一眼,淡淡道:“这性格倒挺像Stephen的。”
程嘉木半路在一个小站下了车,临下车前和我换了手机号。
周越越说:“宋宋,你们刚刚是在说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吧?你都弄明白了?”
我茫然看着火车顶摇头:“哪弄明白了啊?听得半懂不懂的,搞不好是他认错人了也说不准。”
周越越吃惊地指着我:“那你还装得你就是那个蛋挞似的,说什么过得很好,还会和,和那叫啥的结婚来着?”
窗外一棵不知名的枯树上挂了只残破的风筝,我目送那棵老树越退越远,短暂地组织了遍语言之后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他就不会来打扰我的生活了,就算我是那个蛋挞,也没人会来打扰我的生活了。我们娘俩好不容易才平顺下来,经不起什么升华了。”
周越越从颜朗手里接过扑克牌,看了我半晌:“有时候我真搞不懂你。”
颜朗嗤了声:“你搞不懂的人多了去了。”又转过头来问我:“妈妈,玩儿什么?跑得快还是干瞪眼?”
我想了想:“就跑得快吧。”
我很理解周越越为什么不能搞懂我,一来她本人不是个失忆人士,不能感同身受,二来她这个人没什么逻辑,不适合搞研究。我从前也像其他罹患失忆症的病友一样,对恢复记忆有一种狂热的执着,不搞懂自己到底是谁就不能安心。但对失去的记忆本身又有一种畏惧和惶惑,人们对于未知总是惶惑。从前是执着大于惶惑,如今却是惶惑大于执着。并且随着秦漠的到来越来越惶惑。现在我压根儿就不想想起从前了。生活好不容易这么顺,老天爷最近这么厚待我,再怎么也等我先尝够甜头。就算要想起过去也不应该是现在,况且我根本就想不起,这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我想,我只是随缘……罢了。
火车到达终点站。安顿好后,我给秦漠打电话报平安,他不知在干什么,声音压得很低,问我乡下的温度、临时住处有没有烤火设施之类。我和他说起路上见闻,提到先锋小说家程嘉木和我们一个车厢,周越越一直策划让人给他毛背心上签名,结果人都下车了她也没成功。
秦漠说:“程嘉木?”
我说:“对啊,长得跟藤木直人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我都吓了一跳。你认识?”
秦漠低声道:“不认识。”又道:“你衣服多穿点儿,看后天我有没有空过来一趟。”
以下为出版书手打部分。
第十九章 这个恐怖的雨夜
时间已经把妲己弄成知己,把知己弄成知彼,你不再了解这个人的一切,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考到了驾驶执照。
我们一行九人前来支教的这个村子名叫鲁花村。
周越越一度怀疑此地是人民大会堂专用油― 鲁花花生油的故乡,但很快就被她自我否定,因鲁花村实在太穷,完全看不出具有滋生大型民营企业集团的土壤,再说此地也不产花生。
我妈从前做镇长的时候,每年春节都要到治下特别贫困的乡村慰问,给贫困户送米送油,以确保镇上的电视台在连小偷都休假的新春佳节里还有新闻可播。我因时常尾随,对远离城市喧嚣的贫困深有体察,在这方面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第二天看到鲁花村村小的孩子们时便没有多么大惊失色。但周越越自小长在都市,没有见识,一走进这所摇摇欲坠的村小,看到这些摇摇欲坠的祖国花朵,立刻便说不出话来,连颜朗都比她镇定许多。
尘土飞扬的操场上,祖国的花朵们个个骨瘦如柴,穿着磨损严重、款式古老且明显不合尺寸的脏衣服,三五成群地怯生生望着我们,脚上清一色套一双军绿色的解放牌胶鞋。这样的打扮让我想起四五岁时候的颜朗,那时他的衣服鞋子大多是街坊周济,尺寸不合是常态,但总是干净整洁。外婆对颜朗在卫生习惯上的要求一直很高,高得连我都于心不忍,且丝毫不随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变动摇。颜朗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孩子们脚上的胶鞋,观察良久,对我说:“妈妈,这么冷的天气他们穿这个鞋冷不冷?”
我说:“嗯,但你看他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新鞋子,每一双鞋子都很干净,你也要向他们学习,珍惜自己的东西。”
周越越没说话,大大叹了口气。
听接待我们的老师提起,这些鞋子来源枝运动会前夕,校长去相隔八十里地的镇上赶集,买了一张体育彩票,中了五百块钱,想起运动会上大多数孩子没运动鞋穿,回来就拎了两麻袋。平时孩子们都很宝贝新鞋子,只有在重要场合才穿出来。显然,他们认为今天是一个像开运动会一样重要的大场合。
听完接待老师讲述的这段传闻,大家纷纷感叹,一方面觉得校长运气好,上天有好生之德,另一方面猜测校长还没有娶老婆,显然他要是娶了老婆,大抵不敢随便把私有财产拿出来充公,老婆不让他把公有财产拿出来充私已经很难得。
我们适应了会儿环境,看接待老师将散落在操场各处的小学生们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我们这些支教的新老师的到来,并勒令他们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以示欢迎。阵阵掌声中,我身后一个服装设计系的时髦姑娘后知后觉地说:“你们看,他们脚上穿的那个鞋子,就是那个解放牌胶鞋啊,其实挺好看。分析流行趋势,眼下正流行回力鞋配铅笔裤,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流行解放牌胶鞋配铅笔裤,看那个形状,再看那个线条,多Cool 。”
我和周越越构思了下解放牌胶鞋配铅笔裤的立体形象,觉得那已不只是Cool ,简直是Cold ,双双打了个哆嗦后达成共识,觉得流行这东西真是难以理解,比甲型HINI 流感还要不可琢磨。虽然对于穷人来说,流不流行不重要,流不流感才重要,但对于潮人来说,流不流感其实不重要,流不流行才重要。双方的区别是… … 怕死和不怕死的区别。
站在操场的正中央,可以看到四周巍峨的高山。山上覆盖的林木在如此寒冷的冬天依然郁郁葱葱,树冠参差纠缠,紧紧挨在一起,远看构成一道谱系不清的私家菜——清炒西蓝花,可想当积雪落下,那就是蒜茸西蓝花。
短暂而朴实的欢迎仪式结束之后,通过接待老少半个小时词不达意的冗长介绍,我们去粗取精,了解到鲁花村小分六个年级,加起来一共一百二十来人,其中四十多个学生因家离学校太远至少要翻越一座大山 ,不得不住校。
接待老师介绍完毕后,我们酌情分配,各就各位,很快进入教学状态,颜朗也跟着三年级的学生们旁听去了。
上午四堂课,我打算挨着给三四五六年级讲诗歌,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讲到“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讲完收工。结果才上完第一堂,就遇到周越越过来和我换科目。据说她勉为其难上了一堂历史,讲到司马迁时非说他有个儿子叫司马光,当场和有一个认为司马迁没有后嗣的五年级小学生发生激烈的冲突;令偶然经过他们教室上厕所的支教队队长大跌眼镜,果断的安排她过来和我换科。
周越越问我:“你没有准备讲稿吗?”
我鄙视地看着她:“给一帮小学生讲讲诗歌还需要讲稿?”
她欲言又止了半天,说:“哦,那确实不需要。”又说,“诗歌,诗歌,我还是不错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诗歌。”
和周越越换科后,我的教学任务陡然减少大半,就是说当语文算数外语老师都还在讲台上唾沫横飞时,我们叫历史政治地理的已经能够功成身退四处溜达了。我将手机打开,从教师里走出,耳边是周越越声情并茂的朗诵“……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两情若是久长时,惊起一滩鸥鹭”……
我走出二三十米远,已经不能再远,再远就超出了这个玲珑别致鲁花村小的势力范畴。我靠在校门口搓着手拨通秦漠手机,拨通时竟然没有考虑到目前手机状态是长途加漫游。这一刻,终于能能解为什么全中国除了交通运输部门以外,最支持远距离恋爱的就是中国移动。
四百多公里以外,秦漠接起电话,没有立刻出声,耳边传来均匀呼吸,就像他的气息穿透话筒.直接抚摸在我接听电话的半张脸上。纯学术地说,这其实属于意淫的一种,由此产生种种联想,一不小心没控制好度,不能自拔地立刻脸红了。我红着脸尴尬地咳了一声:“你在干什么?”
电话那头道:“画设计图,怎么这个时候打给我,不上课吗?”声音沉沉的带点儿鼻音,真是一副磁性的好嗓子。
阳我立刻从他的鼻音中辨出不正常来,呆了一下问他:“你感冒了?”
他嗯了一声,补充道:“你传染给我的。”
我一边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一边觉得内疚,正要嘱咐他吃两片力克舒,突然想起来:“我前天晚上虽然踢被子了,但昨天早上刚有点感冒的征兆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我一个没感冒的人,怎么可能把感冒传染给你?”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不痛不痒地淡淡道:“你可不只踢被子了还踢我了。”
我愣了半晌,没说话。
前天晚上我和他情不自禁,差点发生婚前不正当行为,幸好被大姨妈即使制止,之后气氛一直很好,吃过饭后他落地生根,赶都赶不走,我经过剧烈思想斗争,觉得大姨妈在,没什么好怕的,略有迟疑疑地让了半张床给他。
躺在床上熄了灯,他抱着我说:“你别紧张,刚才是我太激动,这样对你不尊重,我道歉,婚前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我自动忽略了婚前两个字问他:“但是你不会睡不着吗?”
他说:“为什么我要睡不着?”
我说:“你看我就躺在你旁边,你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的。”
他说:“……”几秒钟后更紧地抱住我,让我的头紧贴在他胸的.声音为难道,“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要是我说睡得着,显得你太没有魅力,回答睡不着,又显得我不够沉稳。”
我被他逗乐,笑出声来,也忘了紧张。
借着窗外的某种非自然光线,他轻抚我的眉毛,声音柔得好比阳春时节一股和煦春风,他说:“宋宋,你在我怀里,我觉得很安心,可以睡个好觉。”
回忆就此打住,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红着脸假装很愤怒,对电话那边的秦漠嚷:“是你非要住我这边的,我都跟你说了我睡相有点不太好。”
他在那边低低地笑:“把被子踢下去好几次不说还差点把我也给踢下去,原来这个只是叫睡相有点不太好,不知道很不太好的睡相又该是个什么样。”
我哑口无言,想说点什么来反驳,在脑海里检索半天,什么也没检索出来。
他也不像是非等着我说一个答案,不等我开口,已经声音压得沉沉的继续道:“其实,除了踢我那几下子外,其他的小动作都挺可爱的。明明睡得人事不省了还非得拽着我的睡衣,我下床去喝水,一根指头一根指头掰开你还不肯,非要再拽上来。
我沉默了,脸热得厉害。
电话里起码有两分钟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眼看着人民币在沉默中从手机账户里义无反顾地流出去,不禁让人想起一个四字成语……沉默是金。一个学生从我眼前飞驰而过奔往厕所,中途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目送那个学生进人男厕所,秦漠已经点到即止地转移话题:“课上得怎么样?”
我拍了拍脸,镇定下来:“这些孩子都挺聪明,我教他们念诗,都念得很好,比城里的孩子一点不差,只是念书的条件差太多,不过这里的校长和老师人都很好,对学生也好,真正的为人师表。”
他又一一问了颜朗,顺便问了周越越,临挂电话前,我思忖着问他:“你明天是不是要过来?”
他笑道:“怎么?想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