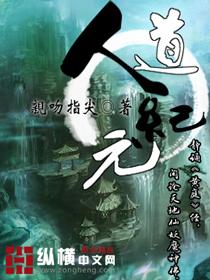黄安口女人-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引子
黄安口是一个地名,在辽东怀仁境内。
在富尔江的江套子里,有一座很高的山,三面环水,一面接地。靠水的那一面是几百米高的峭壁,很是险峻。正面有一条通道弯曲陡峭通向山崖,那山崖当地人称它老垃子。
崖上是一个很大很深的盆地儿,像一个瓮,如一个石头城。
崖下一是个大山坡,当地的人叫它黄安口大坡。大坡下面是一大片平川,平川上镶嵌着村庄和小镇。
很久很久以前,黄安口崖里住着一户姓李的人家儿,据说他们二十几辈先祖就住在那山上,座山为王。他们的先人建州女真的第三代首领李满柱,四代撤满哈失里,五代完者秃,六代卜罗多,七代李铜儿,都住过辽东怀仁,从1469年完者秃开始就住在黄安口崖子里;李铜儿1509年在此任建州卫都督,卫址就设在这里,至今已经有四、五百年的光景了。
他们是满族的祖先。到现在还能在茂密的丛林里看见房子的遗址,很多的房身儿,一排排的。有的像是住房,有的像是兵营,还有的像练兵习武的场地,沿着崖顶上有起伏连绵的城墙。年头已久了,有的墙壁只有根基和断墙了,有的早都被岁月的风霜和落叶掩埋掉了。
后来,山上的人都下山了,有的进了京城,有的下到山下来住了。崖里荒了下来,只有打猎放牛采山菜的人到季节才来这里。
老李家儿有一支儿下山后就住在大坡下的老垃子村。年头久了,一个大家族,又分出了好多支,一个个院落,面朝南背靠坡,一年一年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到公元1912年初至少有25辈了。
老垃子村正前方五里路是黄安口小镇,西边约十里远是赫家园子,东边八里长便是图家堡子,这四个地方呈扁平的四边形。
黄安口小镇的再南边是牛毛大山,在山的后面,有一条很长的河,叫冬古河,婉转悠扬进入大雅河再入浑江。。
从赫家园子向西翻过几道山岗,走过几道沟壑和河流便是兴京老城,园子南边是老秃顶子大山,园子往北面是瓦尔喀什村。黄安口老辈的人都认为:黄安口也是借了兴京龙兴之气的好地方。
就在这千百里方圆的大山中间是一片肥沃的黑土地,从远处看上去是一望无际的小平原。
富尔江的江湾子像一个胳膊肘子把小平原一拦两块,东半边属于图家堡子,靠西边这一边当地人叫它赫地,方圆有几百里,是老赫家祖上留下的土地。那土地肥得流油,春天,赫家就把这祖上留下的千百垧地包出去种,到了秋天,收回来的粮食留下家用少许,大多的就全都送到小镇上的粮油庄,也有外面来收购的,一年到头,家里日子过得还算殷实。
在很早的时候,黄安口先有老李家,住在崖里,后来下山住在这老垃子村。赫家老老太爷和老老太太从南边冬古河那边迁来黄安口,是因为赫家祖上在这里置了土地,是来料理土地的。
他们一来到这里就住在赫家园子这平岗上,在这里盖了房,置了家当。为了和当地人融通,赫家老老太爷和老老太太聘了姑娘赫乞兰芝给了老垃子的李都督。外来户能和老李家这样的当地人家结了亲,在这黄安口就有了根儿。后来赫家老太爷娶了老李家的姑娘李腊月,就是后来的赫老太太,满族这种习俗叫“换亲”。
而老图家是因为一个姑娘从兴京那边嫁进赫家园子;这样,就有几户图家人借故奔亲来到小平原东半边儿住了下来,住久了,人过来的多了,这地方便成了图家堡子。
因此,黄安口基本是三大姓,李、赫、图。虽然也有别的姓氏但较少一些。这里的姑娘都不远嫁,年头久了,这里便是亲上加亲。满族人结亲讲究亲上加亲,有时候不计较辈份。
第一章
公元1913年的冬天,黄安口冷风刺骨,北风常常在夜晚刮得山口那边发出口哨一样的尖叫声。
满族人家的房子一直廷续女真时期的北方民宅模式,都说是:筒子房,万字炕,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一点也不夸张。冬天的夜晚,灶坑里柴火总是着得旺旺的,地中间木墩子上有一个大火盆,刚从灶坑里扒出来的红红的炭火,闪着蓝光,烤得满屋子都是热热的。老爷们和小孩子们都可以光膀子在屋子里随便玩耍走动。
过日子的人家,只要男人下力,房前屋后不远处就会有房子一样高的大柴垛,一排排的,今年用不完明年还会有新的大柴垛垛起来。劈柴燃烧时屋子会里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锅下是燃烧的柴火,锅上是蒸的粘豆包,满屋子热腾腾的香气。
小孩子们天天围着大火盆烧土豆,烤核头吃,大一点的孩子管烤,小的只有围在边上等吃。有时候,嘣的一下,烤熟的核头崩上了房顶;老太太就急忙过来扑搂着小孙子的头说,摸摸毛,没吓着……
赫家老太太,年近六十岁的模样,青衣素裹,长得方方整整的面孔,大模大样的,一看就有大家女人的气势,说起话来,不容人辩解,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这个赫家园子的七奶奶,与赫老太爷共同生活了近二十八年,共有十个孩子,八个儿子,两个女儿。图兰格的男人是她的六儿子,在八个媳妇中,老太太最得意六媳妇图兰格。
窗户上就糊了一层毛头纸,可什么风也打不进来,一家人暖暖的,南炕太热了,老太太把孙子外孙女一个个挪到北炕,北炕凉了再一个个挪到东屋去。老太太爱孩子如命,总是心肝宝贝的叫孙子。三九天,她就揭开怀,把孙子揣在怀里。媳妇生第二个孩子,她晚上就搂着第一个孙子睡,有了第三个她就搂着第二个睡,让第一个睡在旁边。孙子就是她的心头肉,她总是说:“过日子,过什么?就是过‘人’!”
冬月十一那天早上,太阳刚刚冒红,见媳妇图兰格快要临盆了,老太太算好时间打发祁玉和车把式拴马车一同去图家堡子接收生婆,这里的人叫收生婆为“老娘婆”。
赫老太太从屋子里急匆匆走出来,一迈脚跨出门槛,站在正房门外的台阶上,拿着鸡毛掸子掸着两袖上的灰尘,声音哄亮地叫:“祁玉啊,祁玉,六媳妇要生了,你和车把式套车去图家堡子接马大吹他老婆去!”然后转过头对在东下屋子里忙碌着的下人张嫂说:“张嫂,你给马头都挂上红布条。给车上放个棉被子”
张嫂嘴里应着:“哎,来了!”。
张嫂在水盆里撩水洗了两把手,分别在围裙左右两边擦了擦就进屋子找来红布条拴在四匹大马的额头上,又放了棉被在马车上。一时间,几匹高头大马显得很威武,张嫂拍拍大老白胸口说:“大老白,家里要添人进口了,你高兴吧,你和你的孩子们受点累,跑一趟,快点回来。”大老白像是听懂得了张嫂的话,点着头,一只前蹄刨地,咴儿咴儿地叫着。
祁玉帮车把式很快套好车,就坐在右边的前辕上,只听车把式老费喊了一声:“驾!”便大鞭子向着天空,拉开阵式左右一甩,叭叭的响声响彻小平原,回荡黄安口。老费一跃跳上车,坐上左边前辕,马车悠悠地出大门上路了,呼呼地下了平岗。马车一路车辙,留下一串串响亮的马铃当声和车把式那嘹亮优美的满家大调《海东青》:
在长白山之上,
脚踏洁白雪花,
看到广阔天地之间
有我飞翔的鹰神海东青。
在深林中穿行,
拉开天赐硬弓。
拉硬弓的阿哥啊,
骄傲地奔走吧。
海东青飞翔,
傲视洁白大地,
搏击风浪,
骄傲无畏。
阿哥奔走,
寻找多彩之光,
勇敢、强壮、隐忍、坚定,
把信仰铸造。
长白山啊,是咱满洲人的根啊,
黑龙江啊,是咱满洲人的根啊
……。
老费一遍一遍没完没了地唱。
赫家园子的少奶奶图兰格,正值三十六岁的年令,在经历了与男人的生离死别的半年后,将要生下他们的第四个孩子。
头一天就交景了,老太太平时住在东屋,是因为媳妇要生产了,这些天才住在西屋媳妇北炕的。
图兰格脸上一脸的痛苦,眉头都往一起聚,可她知道怎么叫喊也没有用,只能强忍着。赫老太太看着痛苦中的儿媳妇一直陪在身边,说:“你就叫两声吧,疼,你就叫!什么事别总这么抗着,叫一叫或许会好受些”。
生孩子是女人生死幽关的事,再说了,图兰格这次生孩子绝对与以往不同,男人没了啊!老太太的六儿子希虬在春天上因为患了急性痢疾啥药也不顶用,三天头上就死了。死后半年兰格生这孩子,这媳妇心里是什么滋味啊?都是女人,谁赶上这事能好过呢,再说那是赫老太太心爱的六儿子,就那么几天,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轻人说没就没了。
老六挖去了的母亲的心,带走了媳妇的幸福和快乐,那时孩子还在兰格的肚子里才三、四个月,赫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的心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老太太在半年的时间里,想儿子想“死”多少次了,看谁都像六儿子,梦里梦见六儿子坐账房里在打算盘儿,老太太上去扑,扑个空,醒了啥也没有了。
如今媳妇才三十六岁,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老太太感觉真是天要塌下来了。可后来有一天,她突然想明白了,这事自己得先挺住,给儿媳妇撑住这个天,不然这个家怎么办,赫家园子不是塌了吗?
这会儿,赫老太太让张嫂一会儿给弄来点汤,一会儿弄来点水,煮了四个鸡蛋,说吃了鸡蛋生产时会有力量。老太太说:“贵儿她妈,壮着点嘴,吃了这些蛋,一会儿会有点劲儿。谁叫我们是女人,女人一生头一件事就是孩子,生了孩子,当了妈,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生孩子是妇道人的本份,可生孩子又是女人一大关口,福气不是白来的啊”。
图兰格忍着痛吃了一个鸡蛋,老太太说再吃两个,图兰格强又吃了两个,老太太说得吃双儿,吃双儿才会生小子,图兰格好容易吃完了四个鸡蛋。
张嫂放下窗帘,放下半边儿幔子。赫老太太,站在炕沿边上,一只手擎着一个长烟袋,挺直着身子,不时在将瓷烟嘴儿放嘴里咶一口,另一只手慢慢地将炕席从炕梢那一边掀开,向炕头那面卷成一个筒儿,筒里用烟笸篓压上,露出半面炕。
原来炕席下面是厚厚的谷草,谷草下面的土炕撒了一层草木灰,这都是前些天让人新铺上去的,是为媳妇生孩子准备下的。小外孙女五岁的卢球球穿着红色的小棉袍,在老太太身边窜来窜去的,弄得老太太手忙脚乱的,说:“你这孩子,一有事你就跟着忙活,你一边玩去,你六舅妈要给你生小弟弟了,一会儿煮鸡蛋管你够吃,去,找你三哥玩去,大人生小孩子,小女孩儿不能看的,看了就不能长大个了,听话,一边儿玩去!”
球球不离开,忽闪着黑核桃一样的两个大眼晴,问外祖母:“要是小妹妹呢?”赫老太太说:“是小弟弟。”老太太说的很肯定。球球跑到外面去了,一边跑,一边说:“要生小弟弟了,要生小弟弟了!”
席子一揭,顿时从谷草缝里爬出两个黑虫子,窜出三个钱串子,像蜈蚣一样的虫子,悉悉嗦嗦地在草里窜上窜下的,老太太将夹着虫子的那一把谷草撤下来在一边儿抖了抖,虫子掉在地上跑掉了,然后把谷草又放回去。老太太将谷草拍打平整,在上面铺一张牛皮纸,说:“贵儿他妈,上来吧!都这么生。”图兰格吃力地从炕梢爬过来,重重的身体把席子卷儿压得几乎扁了下来,爬过来就在牛皮纸上仰面朝天地躺了下来,光着下身子,气喘吁吁而且不停地申吟着,老太太给盖上一个孩子的小被。
老太太一边舒展着炕沿边儿的牛皮纸一边儿说:“现在啊还有个收生婆,我年轻那会儿,哪有啊,我生这十个孩子头两个是你奶奶婆婆给接的包了,后八个都是我自己包的,肚脐带一掐断,放上点棉花灰用带卡子一系就行了,那脐带可好掐了,一掐就断,嫩嫩的。再说,生孩子生多了,也不像刚生孩子那么费劲,蹲在地上,两手攀炕沿像撒尿一样,一使劲就出来了。那穷人家的女人,更是不容易,自己包完孩子,自己下地洗血裤子,煮两个鸡蛋就是头一顿饭啊!哎,啧啧!女人不易啊!”
图兰格从前也听过老人这么进过,一听就直起鸡皮疙瘩,但现在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一阵阵宫缩让她申吟不断,痛苦不堪。
老太太早就准备好了两丈红布和一小团新棉花,拿出来放在柜顶上。红布是给老娘婆的,这是山里的规矩,算是报酬吧。佣人张嫂给烧了热水,当准备的都准备好了,省得到时候来不及。有两个时辰的功夫了车还是没回来,图兰格叫得比早晨更急了,老太太有点着急了,说这么大个家口,有点事没个主心骨还真是不行呢。说话间马车叮当地进了园子,张嫂喊着:“老娘婆来啦,老娘婆来啦!”老太太急忙出门迎了上去:“她大嫂,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