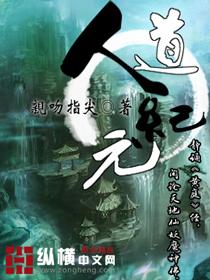猎梦人-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而,事情却在他们有一回抢劫旧货铺的时候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时,大卫正欲跳上雨果的行李架,梅尔兰老头突然从窝棚里蹿出来,冲着他的脑门儿扔过来一只破闹钟。那块废铁砸中了他的太阳穴,使他立马从自行车后座上摔了下来。半昏半醒间他骨碌碌地滚到马路中央,而他的同伙见势不妙,吓得尖叫了两声,拔腿便跑,鼻子几乎贴在了车把上,以便在冲下商业街时减弱空气阻力。旧货商捏住大卫脖子后面的皮,把他从地上提起来,就像拎起一只猫,准备将其抛入水中溺死。问明地址以后,他一言不发地把大卫送回了家。那天真不凑巧。爸爸刚出差回家换上了一双方格拖鞋,准备享受一个长长的周末。旧货商立即把“小坏蛋”的斑斑劣迹悉数抖落出来,他列了一长串被盗物品的清单(不乏夸大其辞的成分),并要求就地赔偿损失,不然他就要上法院起诉。爸爸赔了他一笔钱,脸色变得像蜡烛一般惨白。等梅尔兰老头一走,他便朝大卫走过来,慢慢解开皮带,明摆着要拿皮带抽他。就在这时,妈妈介入了。“如果你敢碰他,我马上走人,”她语调沉稳地说道,“这话我不会再重复。你很清楚不是他的错,他天生如此,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可当时爸爸似乎失去了理智,开始破口乱骂起来。他管妈妈叫巫婆、疯子,说她还不如回她那疯子扎堆的马戏团干活。妈妈并不辩驳,而是回到旧扶手椅旁坐下,点燃一根香烟,任袅袅青烟将她笼罩,仿佛有意织起一片将她与其他人隔离的烟雾。爸爸一个人咆哮了大半个晚上,继而扣上皮箱,一边走出家门一边叫嚷着说:住宾馆也比在这该死的破屋子里开心……如果继续发生这种事,他便不再踏进家门一步。大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更别提哭了。等爸爸一开车离去,妈妈便把他拉到膝前,一个劲儿地摩挲他的头发。“这不是你的错,”她声音犹如让烟草浇上了一层沥青,一年比一年嘶哑。“是你天赋异禀的后果。在上帝赐予你某种能力、某种才华的同时,魔鬼不愿甘拜下风,也会马上赠予你一份用心险恶的礼物。你得学会协调,得用一项缺陷、一个瑕疵来偿还天分。这就是法则。有的人成了色情狂,还有些人成了杀手。你千万别抱怨,我们所遭遇的磨难还不算太沉重。小偷毕竟不是最糟的,我认识的一些人染上了比这更卑鄙无耻的恶习。”
大卫不大明白妈妈这番话的意思。她说的天赋是指什么呀?当然,他画的画倒还说得过去(尤其是赤身裸体的女郎),但也没什么可吹嘘的。他唱起歌来五音不全,跳起舞来更是拙手笨脚。总之,他跟所谓的艺术家毫不沾边。那妈妈凭什么那样说呢?看样子,最后一次行窃的失败搅乱了这个世界的部分秩序,因为继大卫之后,妈妈也在商店打折期间被那胖警长莫里亚尔逮了个正着。当警察在廉价首饰柜台前一把捏住妈妈的手腕时,大卫吓得尖叫起来,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像婴儿一般马上要尿裤子了。“哦夫人,”油头小胡子开玩笑似的说道,“我想咱们有不少事情可以谈谈,咱们可是老相识了,不是吗?好长一段时间您都拿我当白痴。现在您跟我到办公室走一趟,我们要搜查一下。”大卫仿佛在梦中游走。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如此渺小。他知道自己开不得口,除非他想顷刻间哭成泪人儿。莫里亚尔带领他们步入一条狭窄而昏暗的走廊。“小朋友你乖乖坐那儿,不许乱动!”他指着一张锈迹斑斑的铁凳子冲大卫命令道,紧接着便把妈妈推进了办公室,并小心翼翼地关上门。“来吧,现在开始搜查,”警官喜不自胜地大声宣布,“先掏空口袋……还有袖子!”
大卫的耳朵里满是轰鸣声,听不清他们接下来说的话,但那警官突然喝道:“我说过的,内裤也要脱!”紧接着从里面传来窸窸窣窣一阵响,像是有什么东西落到了地上。十分钟后妈妈出来了,只见她一脸凌乱的口红印,头发也乱糟糟的。她拉着大卫的手径直走出了商店,并没有刻意地加快步伐,仿佛对所有营业员的眼光都熟视无睹。
冬夜里的街道显得格外幽暗,他俩一到马路上,大卫便结结巴巴地问:“妈妈,我们不会进监狱吗?”
“不会的,”妈妈喃喃地答道,“对付这种家伙还是很好办的。必须不声不响地接受惩罚。正为有此天分,我们得慢慢地偿还,这就是规则。你将来也一样。就像人家时不时地向你出示账单,而你只能二话不说马上付账一样。”
一回到家,妈妈便匆忙淋浴,在喷头下待了很久。最后,她裹着那件旧浴衣从浴室走出来,倒了杯朗姆酒吞下三片安眠药,然后就上床睡觉了。大卫一个人留在空房间里,难以入眠。好像有东西打碎了,但他不知道是什么。是因为他的缘故妈妈才被抓住的吗?那套迄今为止在冥冥中保佑他们不被追究的命运之轮会不会由于他最近一次行窃失败而失灵了?都怨他,他实在太疏忽大意了,让接连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低估了梅尔兰老头,而且还……
那天夜里他听见母亲在呻吟。他以为她病了,于是轻轻推开双亲的卧室门。他过去从来不会这么干,但妈妈吞服安眠药的场面突然在他脑海中闪现。万一妈妈服毒自杀,万一……
只见她躺在床上,双目紧闭,一股白烟从她张开的嘴里冉冉升起,近乎晶莹透亮,弯弯曲曲地飘入空中,在天花板高处聚积成巨大的一团。起先他还以为是妈妈吸烟吐出的烟圈,但一闻却没有烟草味。空气里飘忽着一种古怪的气息,是电味。他朝床边迈了一步,双手都冻得麻木了。妈妈正在熟睡中,仍然有烟雾从她口中吐出,仿佛她体内着了火一般。大卫胆怯地伸出食指,只觉那烟有种异样的质感,摸上去黏黏糊糊的,不仅温热,还有弹性,是成形的。天花板上的那块烟团此时已有皮球那么大,表面开始有隆起凸出。那东西……宛若一尊雕像。它就像一个白面球在独自将自己塑成模型。那是……一颗头颅。一颗人头……
正是胖警官莫里亚尔的头。大卫吓得心惊胆战,撒腿便跑,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了。那颗白色的头颅被他奔跑带来的气流牵引着,一路紧随他身后。大卫不知往哪里躲好。莫里亚尔的头在过道上浮动,踌躇不定,好似一个随风飞舞的气球。那张脸苍白得没有血色,看上去毫无生气,颇似一件四处飘扬的雕塑,被一根线拴在妈妈的嘴唇上,它飞得越远,线就拉得越紧。“这是她呕出来的东西,”大卫一边遐想,一边蜷缩在客厅茶几下面,“这不是真正的人头。其实它就像黏性烟雾制成的一张面具,不过是一摊会飞的呕吐物而已!”
为了克服恐惧,他尽力运用理性思考,然而胖警官那张可怖的脸依旧到处飞来飞去,撞到一扇扇门上,又弹回来。就这样持续了几分钟,接着伴随一声古怪的脆响,它像肥皂泡一样骤然破裂,溅了大卫一身类似蛋白松糕的奇特物质。
这回他决心要刨根问底。第二天,他找到妈妈,并向她讲述了头天夜里发生的事。见他茫然无知的样子,年轻的母亲一脸惊诧。“哦宝贝儿,”她放声大笑道,“这就是我所说的天赋。我还以为你知道呢。怎么你还从没碰到过这种事儿吗?我们都是通灵者,能让灵媒外质成形。”
“让什么东西成形?”
“灵媒外质。过去人们一直以为那是死者的影像,其实它们是从我们的梦里萃取出的模型。趁我们沉睡之时,这些心理影像便在空中凝结为具体的东西。就像是梦从人的耳朵眼里窜出来,由烟雾幻化成一个个小人儿。”
大卫眉头紧蹙,用心领会妈妈的这番解说。“你在扎哈夫人那里的时候就干这个吗?”他问道,“那你招过魂啰?”
“哦!扎哈夫人对外是这么吹嘘的。”妈妈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事实上,如果顾客想乞灵于某位已故者,在每次出场之前她都会把死者的照片给我,然后我凝神聚力,将人物容貌特征牢记于心,接下来扎哈夫人便对我施催眠术,一边令我沉沉睡去,一边命令我梦见方才见到的东西。于是那张脸孔从我口中飘出,在房间里浮来荡去。顾客们见状十分满意,深信映入眼帘的正是逝者的幽灵。这是一种诈骗行为,宝贝儿。我哪里召回了什么死者,我不过是用烟雾塑成了他们头颅的形状而已。我就是这样和你爸爸相识的。当时他每个星期都来,要我召唤他的一个死于车祸的情妇。很长时间里他都把我看成巫女,后来我向他说明了真相,结果他还挺失望的。”
大卫一脸困惑。难道所谓的天赋就是指这个?一张张人脸会从他嘴里吐出来,继而又像肥皂泡似的逐一爆破?这多傻、多愚蠢啊,除了能在马戏团秀一秀以外,简直毫无用处!难道他不得不迷上偷窥的行当,就是缘于这么一个无聊至极的本领吗?
“我从来都算不上天资过人,”妈妈自言自语道,“我产出的灵媒外质寿命都很短暂。它们爆裂得太快,有时还会走形,变得面目可憎,结果自然是与顾客麻烦不断了。我没法长时间地保持面部五官的和谐——不是鼻子大得出奇,就是耳朵赛似大象。我一醒来扎哈夫人就指着我劈头盖脸一顿痛骂。她吼道:‘给我好好想想自己该干什么,他妈的!老娘我下一场还得重来。’”
说实在的,妈妈并不大明白应该把她的天赋用在什么地方。迄今为止,通灵者的用武之地主要局限于神秘学行业。(一个好的灵媒塑模艺术家如果供职于一家知名工作室,完全能过上很优裕的生活。)除去这一狭窄的市场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出路。
“我可不想在巫师手下干活!”大卫抗议道,“装模作样也不行。想想看,要口吐死人,真够恶心的!”
妈妈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她只知道大卫应该有天分,正如她像她母亲,儿子也应该像她。这是他未来生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至于他是否打算靠这个赚钱,就全看他自己决定了。不知为什么,大卫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好像眨眼间从登台演出的魔法师沦为了撂地卖弄幻术的街头艺人,这滋味可不好受。在随后几周里,他俩在好几次谈话中都提及了这一怪异的遗传,再后来妈妈便又像从前那样沉默寡言了。爸爸几乎没再回家,外面风传他在异乡“另有家室”,在那儿过得自在得多。这所谓的另一个家使大卫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他试着去想象爸爸跟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孩子在一起的情形。起初他还忿忿不平地想:“我们才是他真正的家。”现在他已经麻木了。在他看来,爸爸老不露面,回来看望他们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而且总是匆忙离去,使得他们就像替身演员,永远只能待在后台,相互之间的关系日渐淡漠。爸爸真正的家是“别人”的,是远居他乡的陌生人。大卫和妈妈只不过是影子罢了,就像……肉身透明的灵媒。
十四岁时,他吐出了第一批幽灵似的模型。这一切都发生在夜里,他自己则浑然不知。一早醒来,他发现天花板上飘浮着一团团大杂烩。与他母亲不同的是,他产出的凝结物是非象形的,但却经久不化。“我可怜的孩子,”妈妈轻声念叨着,“这简直是个四不像嘛,倒挺像……爆米花。唉,本来我还打算把你介绍给扎哈夫人呢。”见到妈妈失望的神情,大卫心里很难过,可一想到不用再为哪个搞秘术的骗子所利用,他又松了口气。“一个不会吹、不成形的通灵者,”妈妈绝望地说,“还真是从没见过。”
她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去试着纠正儿子,像运动员的教练一样指导他。她向他展示了一些照片,命令他强行记忆,但大卫做出的梦晶外形依旧玄妙难辨,怎么看都不伦不类。“你吐出的简直就是毕加索的作品,”妈妈叹息道,“如果你能有幸碰上长这样一副嘴脸的顾客,那就算你走运了。”可大卫不愿拿死人来诈骗钱财。他有多喜欢成为一名伟大的小偷,就有多憎恶诈骗犯这一行当。从十七到二十岁之间他造了许多梦晶,尤其是他恋爱的那阵子或是处于青春期性焦躁的时期。爸爸在得知妈妈身体不好之后就搬回家住了。医生诊断出她的肺部有块东西,这该死的病是吸烟过度引起的。只有大卫明白他们弄错了。事实上,那是在妈妈胸部蜷成一团的梦晶。随着人的逐渐衰老,这些秽物越积越厚,而且拒不出来。它们淤滞在支气管内部并不断硬化。妈妈正在死去,因为一个夭折的梦晶阻塞了她的肺。爸爸终于回到了他们身边。他老了,仿佛他那远在天边的“真正”的家已经过分耗损了他的精力似的。
从二十到二十三岁大卫经历了一段潜伏期,当时他还以为自己丧失了天分。为此他如释重负。那三年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