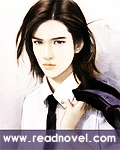岁月如此装x-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可言喻的贡献之后,搭了个车回来了。
至于他俩为什么没爬上去,没人知道,这是个悬案。
从土豆妹的回忆里获悉,土豆领着她在山脚下坐了整整六个小时。
我代表马来西亚亚庇市京那巴鲁山野生生态环境局感谢土豆,土豆的名字会被这里的同胞记住,沙巴最大的商业中心里的某个知名连锁餐馆也以他命名了一道菜,肯德基炸土豆条。
在一家华人餐馆吃了午饭之后,谢君昊撂下包对我说:“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拿个东西。下午按原定计划和另外两个朋友一块去沙巴大学,怎么样?”
过了大概半小时,我就看见谢君昊戴着头盔骑了辆摩托车“咻——”地出现了,“咻——”“咻——”再两声,后面俩哥们一人一摩托,很拉风地亮相了。
他在我跟前刹住车,在尾箱里拿了个头盔给我,:“我们租了三辆摩托,来,带你自驾游。”
我凑近了问他:“这里的摩托随便租?”
谢君昊点了点头。
“要出示中国驾照么?”
他耸肩:“不用,出示护照就行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说:“那我也去租个飞车过把瘾。他就是要驾照就没问题,我手上就一现成的,50块买的,不用白不用。”
谢君昊瞟了我一眼,撒手不管了:“不怕死的你就去。”
事实是我真的揣着护照和假驾照兴冲冲地前去车行表示要租个女款摩托。
店主说:#######。
我认真揣摩了他每一个发音之后,认为他说的可能要么是英语口音的马来语,要么是马来口音的英语,都隶属于我听不懂的语种。
我对谢君昊说:你帮我翻译一下。
谢君昊问:什么是女款摩托?
我说:就是对司机驾驶技术要求不高的,有一年以上自行车驾驶经验即可自行驾驭的摩托车啊;前面有个篮子,可以用脚刹车的那种。
他说:好了张扬,你可以走了。
这天下午我坐在谢君昊的飞车后面,回忆油然而生,想起了考驾照时候和我同车而行的考官。
人都说有了儿女才能体会到父母的辛酸,眼下我对考官当时的心情感同身受,时不时地在心里赞赏一把北京海淀驾校的师傅素质过硬。
耳边有呼呼的风声。
我花了半分钟的时间来思考亚庇这个地方是否有摩托车交通规则,然后我就看见有一个当地的马来哥们骑辆摩托车后座载了个人,俩人背靠背坐着,车后座那人手里提了个硕大的老式收音机。这车一边跑,一边公放背景音乐,场面十分壮丽和谐。
我大声对谢君昊说:“大哥你开慢点,别飙车啊啊啊。”
他空出一只手捉住我的手环在他腰上,无奈地说:“张扬我的T恤都快被你从后面扯下来了。”
我单手圈着他。两边的热带风景一览无余,蔚蓝的大海好像触手可及。
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谢君昊是一个资本主义青年,喜欢端着杯咖啡镇静地和中国人用英语交流经济问题。
现在我一定要承认我的认识是错误的,谢君昊大概是个精神分裂的资本主义青年。
刚才他在主干道上把摩托当飞机开暂且不提;现在我们走在窄道上,谢君昊和另外两辆摩托并排前进,仨摩的严严实实地把后面的汽车全部挡住,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在车队的最前端。
沙巴大学校园很空旷。
路过一段没人的斜坡,谢君昊双手松了龙头,快速冲下去,很带劲。
学校里有片海滩,我们开累了就在海滩旁边的棕榈树荫下坐着,看来来往往的马来美女。
海风里有咸咸的味道。
我开了罐可乐叹道:“开飞车感觉真刺激。”
谢君昊很自在地靠着树坐着,提起可乐和我碰了碰杯,舒畅地笑了笑说:“晚点载你去个地方。”
我说:“哪?怎么我感觉你跟变了个人似的,师兄你前段日子是受什么刺激了吧?”
他带着笑意挑起眉:“怎么说?”
我很难描述自己的感觉,只能和他说有巨大的反差,就跟看见我国伟大诗人李白在开摩托一样,有种违和感。
谢君昊听完哈哈大笑,“不是我有变化。是你对我的态度不一样。张扬我之前总有种感觉,你是不是看见我就想跑?”
我点头说:“你太英明神武了。你是我老板,我看见你不跑难道主动贴上去让你压榨劳动力么?”
他低笑着问:“那现在呢,改观了?”
“是,我现在觉得你和我在一个页码上。交个朋友也不赖。”说完我装作很豪爽地拍了拍他的肩,别过脸去远望大海。
自从上次和谢君昊摊牌,再次见面之后,我在他面前突然就不那么局促了,可以放松下来和他偶尔交个心,像朋友一样。
这样的关系很舒坦,没人逼着我非得做点什么,表达点什么,承诺点什么。
太阳晒得人舒服得想睡觉,我用手枕着头平躺下来,戴上耳机听着歌。
耳边在放五月天的《笑忘歌》,阿信在唱:那一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从头到脚趾都很快乐,我和你都约好了,要再唱这首笑忘歌……
我想我做了个梦。
梦到有一天晚上,星光很灿烂,阿信带着怪兽、石头他们在台上唱着后青春的诗。
有个人伸出手把我轻轻搂在怀里,他的眼睛和星光一样灿烂。
第二九章
这个梦做到一半就被谢君昊拍醒了。
他很严肃地和我说:“要下雨了,上车跑路。”
我说:“哪啊,刚那么大太阳,这地要是能下雨,我立马裸奔一个给你看。”
话刚说完,雨就很有组织有计划地下起来了。
这是一场大雨,劈头又盖脸。我扣上安全帽跳上车说:“开路。”
谢君昊发动了车子,开玩笑地说:“刚说什么来着,大雨里裸奔挺有情调,我开个小摩托在旁边做陪跑的。”
我说:“赶紧撤,晚点一道天雷劈下来,劈死一个算一个。”
接着谢君昊就开着小摩托“咻”出了沙巴大学,“咻”在康庄大道上。我得承认他的飞车技术牛X的不行不行的,那就是一骑绝尘一泄千里,千里之内总觉得会一车两命。
沙巴大学离市区不近,风里来雨里去的,我们驰骋了近一个小时才回到市区;眼见着要到旅馆的拐角,谢君昊打了个大转,换了个方向直挺挺地迎风而去。
此时我已经被完全浇透,开始郑重地思考要不要用把前面的谢君昊踢下去。
谢君昊雨中飞车的目的地是丹绒亚路海滩。
眼前的海上乌云密布,漫长的海岸线找不到一个路人。
我和谢君昊在旁边的公园找了块地开始拧衣服里的水。
我四处瞭望了一圈,不是很能理解谢君昊的深层用意:“你,带我,来这里,游泳?”
“没想到会下雨,原本是带你来看日落。丹绒亚路的日落是世界最美十大日落之一。我们之后的两天半行程都没机会过来。”谢君昊略有点惋惜,他擦了擦湿发说:“现在离7点还有一个半小时,不如我等等看雨会不会停?”
“你在问我的意思?”
“嗯。”
我摊手说:“你觉得我有发言的余地么?这么大的雨,我只能指望你把我驮回去,当然大哥你说什么是什么。”
这一个半小时很漫长,尤其是对着前面乌秧秧一片海天一色,我找不到任何娱乐活动,只能和谢君昊甩开了头发聊天,我们最开始讨论的是一个国际话题:摩托车行老板适才和我对话的时候说的是英语还是马来语?
讨论了两分钟之后我果断换了话题,这就好像你和一个毛里求斯国际黑妹讲成都话和上海话一样,对黑妹毫无意义。
最后竟然发展到感情话题,互相切磋了一下我爸和我爸老婆,他爸和他爸老婆的欣酸往事。
我感慨上一辈的人感情都来得很纯粹,随随便便一过就能白头到老;就拿我爸和我妈来说,年轻的时候我那个号称风流倜傥得没边没边最会跳拉手舞的亲爹,就曾经在舞厅里精神出轨过一回。我爸是大学是学中文的,偶尔舞文弄墨,文艺青年总有点不太着调。他那个时候精神出轨得非常低调,每天下了班不打牌不吹牛,在头发上抹点油奔去舞厅蹲点。
蹲着蹲着就蹲出问题来了,我爸他蹲到了我妈。
我妈一眼就看出问题来了,问出来的问题真是太犀利太有深度太一针见血太焦点访谈了,她说:你的头发怎么这么油亮?
后来他俩就大吵了一架,这一架从成都一直吵到成都东边的乡下我姥姥家,再原路折回来吵到成都西边的另一个乡下我奶奶家。
那个时候我还在小学五年级,隔三岔五就能看见我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坐长途汽车拎一篮子鸡蛋提俩活鸡来我家,并排坐在沙发上训斥我爹地。
我爸也很淡定,拧着眉头闷不吭声,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忧郁地抽完一根烟,在骂声中站起身,把那鸡宰了。
再后来我爸他就转型走“魅惑狂狷”路线,再不梳油亮的发型,整天顶着一头乱发,大早起来上班跟上坟一样的表情,下班就穿一大背心和一众牌友抽烟打牌喝酒;家里一片乌烟瘴气。
我妈伤透了心,在伤心中把我从小学五年级拉扯了一年。
我年纪尚小,认为自己应该担负起拯救“失足亲爹”的重任,写了封信搁在家里客厅桌上。信上用水彩笔描了粗粗的四个字:爸爸必看。
这封信声情并茂地描写了父母不和家庭中的儿童迷惘而忧伤的心理状态;现在我还记得信开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眼泪流成河,最后一句话是:我想离家出走,去一个你们找不到的地方。
等到我初中的时候,我家那个叫“老张”的男人突然有一天,把头发梳得油亮,走进我房间和我说:“张扬,你找张纸出来,在上面写四个字:戒烟戒酒。”
我那个时候认为我的爹地脑袋可能便秘了,不能理解他的意思,从作业本上撕了张纸,写着:借烟借酒。
我爸拿着这个纸就出去了。
后来他就把烟戒了,偶尔还会喝两口小酒,但在我和我妈眼皮底下再没喝高过。
再往后,我的老爸老妈虽然时不时还会吵架,还会从成都东边的乡下吵到西边的乡下。
但老张会时不时地带着他老婆坐火车去趟重庆;和朋友一块吃饭喝酒,吹牛吹累的时候,老张会低着头低叹道:“张扬她妈是个好女人。”说完就招呼我妈上酒上菜再上盘西瓜。
我觉得老张在年轻的时候欠我妈一个说法。
我在主持家庭座谈会的时候,当着他的面问我妈:那时候忧伤吗?
我妈说那肯定的了,就想着离了算了,但想想要是离婚张扬肯定要可怜了。
我转头对老张说:看到了吧,你看你平常还总吆喝我妈做这做那。
老张呵呵地笑了两声,很淡定地说:张扬,这个你不懂。结婚过日子,舒不舒坦自己最清楚,有些事吧,别人看着可能觉得我怎么老欺负你妈啊,但你妈不一定这么觉得,等你有主了就明白了。
他转头说:老婆,你说是吧?
我妈没答话,抱着遥控器特别着迷地看中央八套的《金婚》。
我妈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很忧心地说:张扬,我听说现在二手市场比一手市场还大,你千万当心点,二手的尽量不要;要是二手还搭售小孩的,你找回来,我就找根绳子去上吊。
我爸我妈那个时代的人,对爱情没有那么多想法,晃眼一下就走过了十年二十年,比我们这代人对婚姻对家庭要踏实得绝对不是一点半点。
谢君昊说:“和你认识这么久,总算听到句有点深度的话。“
我看了他一眼:“那是你没好好挖掘,我这种发人深省的段子海了去了,随便来一段就能帮助矫正你的三观。”
他挺有兴趣地说:“要是你爸妈来上海,我得请人吃饭,多亏他们培养得好,时不时地帮我端正态度。”
“谢君昊,那边云好像开始散了。”
海平线上的乌云被晚霞晕开了,放出金色的光芒。
落日余晖流淌在波澜壮阔的海面上,像一首钢琴曲弹奏出蜿蜒波光。
眼前的风景好像湛蓝底色的画布,被人执了画笔一笔一笔描成浅金色,添上一抹染成橘红。适才还是乌云波谲的大海醉在夕阳里,一片安宁静谧。
徐徐微风将幕色吹落,海滩旁的酒吧、咖啡屋和集市点起夜灯,摊主打开遮阳伞,店里响起蓝调,一天才真正开始。
我和谢君昊脱了鞋在白沙上飞奔,用脚趾在沙滩上写字。
谢君昊写了个巨大的Mark。
我蹲在海滩上想了挺久,不知道要写什么。
海滩的日落确实挺美,美得让人一不小心就会悲伤暗涌,想起我那个暗着单恋、明着暗恋了很久很久,最后走开了的那个人。
最后,我挺豪迈地在沙滩上写了一排大字:我饿了,想吃肉!
谢君昊站在远处看着我笑了起来,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说:跟着我,有肉吃。
现在我们在珍珠海鲜酒楼里,桌上摆着螃蟹、东风螺和老虎虾。
价格很实惠,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