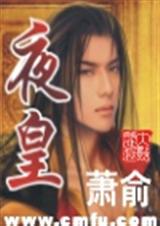唐明皇-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贼!……今天,我,我……”
“你这贱婢!呵哟……!你想干啥!呵哟!燕、燕大人……哎……”
“哼!别说你这两个狗官,就是有两千,两万,大娘何畏你们!今天,我就是那只白象!”说到这里,公孙大娘松开双手,朝后退了半步,猛地飞起一脚,朝王旭的小肚子踢去,王旭只觉得腹部象被利刃深深戳了一刀似的,惨叫一声,仰面倒在了地上。不待燕钦融赶到,公孙大娘纵身一跳又跃到王旭跟前,提起右腿,直着脚尖,径直朝王旭双手护着的滚圆的肚子上踩去。顿时,只见王旭口喷白沫,眼仁乱翻,一张猪头似的肥脸,痛得歪斜着,眼看就要没命了。燕钦融怕事情闹大,不好收拾,连忙从惊惶中赶上前去,伸手把王旭从公孙大娘的脚下拖了出来。公孙大娘哪里容得他救王旭!早又抡起双拳,朝燕钦融的背上擂鼓般击去。燕钦融心里却十分诧异:“嗨呀!想不到她拳、足如此厉害……”他不敢再让公孙大娘乘怒踢打王旭了,忙把那被痛楚和惊骇弄得颤栗不止的王旭往背上一背,迈开步子,就朝通往晋昌坊的小巷跑去。
还没跑出两百步,却听身后脚步声急,燕钦融忙朝后一看,糟糕!只见公孙大娘抡着一条大棒,领着四、五个侍婢打扮的健壮妇人,顺着小巷追赶过来!
眼看公孙大娘越追越近,呼唤吧,时近中午,路上无行人往来;再往前跑吧,王旭又胖又沉,哪里还跑得动?在这紧急关头,燕钦融眉头一皱,想出一个法子,他把王旭放到地上。
王旭可吓昏了。他一头趴在地上,直给燕钦融磕头、哀求:“燕大人!救命呵!我,我要厚谢你!一、一万缗!”
“快跑!”燕钦融却忙着一把把他拉起来,指着去大业坊、转回西市的通衢,“我会挡住她们的!”
王旭这才如下山兔子一样,没命地逃走了……
“哈哈哈哈……”
“好咧!摔伤了胳膊儿,还笑得这么开心!”公孙金菊捧着一碗汤药,一边上楼一边说。
“有劳你了!金菊大姐!”
“你到门口来干啥?躺着吧!燕大人!”当金菊进了他的房间,四下一望时,不觉一怔,“怎么?是你一个人在笑呀?那位王大人没在你房里?”
“他要是在,我就只好让笑留在肚里了。”燕钦融把那裹着膏药的右臂甩了甩,“我说不妨事嘛!你看!这不是很自如么?”
“快喝了吧!你在京城等了这一个多月,好容易才攀上那个斜封官,明日可以当着今上奏报你们许州的军务大事了。如果一只手乌肿了,只怕宫里的人又不要你去见皇上了呢。”
这矮瘦的女店主想得真周到!燕钦融感激地点点头,接过碗来,仰面把汤药一饮而尽。“劳烦你了!”
“你这位大人真客气!”金菊双手接过药碗来,感慨颇深地说,“也真少见啊……”她朝燕钦融道了别,匆匆下楼去了。
大约是公孙金菊刚才的提醒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手伸到窗前,就着夕阳的余晖看着那只受了棒伤的手。看来不会乌肿。虽说肘弯和腋下还阵阵发麻,疼痛。想起王旭的狼狈相他又忍不住笑出声来。心里由衷地赞叹着:“好个公孙大娘啊!”从大娘的浑身重孝,使他联想到今年正月惨死在含光殿前洒油球场白象蹄下的郎岌,他那刚刚有点快意的心怀,又变得十分闷郁起来。
作为河南道许州兵曹的司兵参军,他掌管着许州兵务的武官选用及兵甲、器仗、门禁、军防烽候、传驿和畋猎。但是,从景龙元年赴任以来,他才知道府库内一无所有。连他自己要一匹象样的战马,马厩里也牵不出来。戈矛还是圣历二年,即距今十一年前的六九九年打造的。这些满是锈垢,即使放在油里浸泡,也不能重闪寒光的兵器,连操演使用也不够格,还说什么御敌平叛!而府兵编制,也因地方百姓连年逃失,无从招募;在破帐敝营中,住着不少早已超出服役年限或根本不到服役年纪的白发苍苍的老兵和稚气尚存的幼卒。怀着满腔热血和一片报国忠君之心的燕钦融,并未因面临的困境而丧失热情和勇气;曾经寒窗苦读,驰马习射的这位皇唐州级军官,经历过武周代李唐、李唐灭武周这极其动乱的岁月,把重振皇唐军威的希望,寄托在中宗重新登极上。他上表痛陈时弊,他毫不怀疑今上会追继先君,在赤县神州再次出现贞观之治。
一年过去了!
又一年过去了!
再一年,又过去了!
今年,景龙四年,又已春尽夏来……
他盼望的中兴景象却并未出现。相反,他的府库中,连维持兵卒生命的军粮也时有时无。而兵部尚书宗楚客,却青云直上,登上了宰相的宝座!
最先,他还难解其中奥秘,慢慢地才从州守的幕僚处得知,这位视军机为儿戏的兵部官儿,因正赞助韦后重演武周代唐的故事,而深受皇后宠爱!从此,他陷入了无垠的忧虑之中:皇唐的天下,难道永无宁日了吗?不久,他又听说,各州军粮军饷,竟被宗楚客拨去为今上的两位公主大修寺观。对宗楚客这种误国害民之举,他拍案而起,要上本弹劾。深知朝中掌故的州守幕僚闻讯后,却悄然来到他的衙署,告诉他:“万万不可!”
“我身为大唐臣子,岂可目睹奸臣误国,而不上言君父!”
那好心的幕僚却说:“参军大人为君父、为社稷,一片赤诚,岂不可敬?只是大人可知近日有朝中监察御史崔琬崔大人,弹劾当今总宰一事否?”
“啊!已有朝官弹劾这佞臣了么?”
“唉!崔大人虽冒死弹劾总宰大人,又有何用?……”
那幕僚告诉他,今岁二月,崔琬对仗弹劾宗楚客潜通戎狄,受其贿赂,让戎狄大掠三州而去,致使边患不息,并随弹表,附呈宗楚客与戎狄密信数件;焉知宗楚客竟当着今上之面,愤怒作色,说自己如何忠鲠,还反诬崔琬暗通戎狄……
“今上如何圣断呢?”听到这里,燕钦融焦急地催促那位幕僚,急于知道结果。
“唉!真是不堪设想!”那位幕僚长叹数声,“今上竟然并不下诏查问,反而命崔琬和总宰大人结为兄弟!”
“什么?!”燕钦融听到这个结果,不相信自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简直如在荒谬绝伦的梦中。“真的!今上竟命他二人结为兄弟,和解了事?”那幕僚肯定地点了点头:“要不朝中文武,怎么暗中会呼今上为‘和事天子’!”
燕钦融低头沉吟,很久说不出话来。
“世事如此,你上言弹劾,又有何用呢?”那僚友走了。而留下的这句话,却萦回在他的心中,使他万分惆怅。
执意上言?连朝中大臣也不能唤醒君父,自己这小小参军,又能起多大作用!
听之任之?一朝为臣,即受皇恩,见误国之情袖手不理,岂是人臣之道?
就在他苦闷愁烦之际,他的年近七旬的老母从故乡偃师来看望他。老母见儿子整日愁眉不展,便关切地询问他因何致此?他向母亲倾吐了自己的苦衷。谁知这位世代书香之家出身的老母,却拄着拐杖,对儿子道:“儿啊!我燕氏门中,绝无白吃朝廷俸禄的人啊!快上京去吧!你不能武死战,也该为君父社稷,文死谏!”
慈母的训导使他一扫彷徨苦闷,勇气倍增;他哽咽着跪别了老母,来到了西京。
他跨进西京城阙时,满城芙蓉才绿叶初发;但任他忧心如焚,直到而今——艳丽的芙蓉已万树花飞,他也无计得觑天颜!
京城与许州大不相同:许州是荒凉冷清,这里却繁华喧腾。这忧心忡忡的参军,还不到一日,就从繁华中察觉到了他早已预料到,并为之担忧的情况。就在他刚到长安,为寻一方便住处而四处奔波时,一队队远道从山东、江淮一带向京城运粮的牛车与他擦肩而过。那些赶车人在中使的驱赶下匆匆往皇城而去。他们满面风尘,衣着破烂,神情疲惫已极;而车杠前的牛儿,都耷拉着头,鼻孔里喷着白气,嘴角吐着白沫。他听见其中一人悄悄向街旁一个老者说:“唉!我们关中去年也颗粒无收,一斗米要卖一百缗钱了!……我们从去秋到现在,好不容易才把这点稻米运进京都,伙伴和牛不少死在了途中……”这是什么样的繁华呵!颗粒无收的关中,还得往西京送稂,即或大丰之年,迢迢千里,驱民赶牛,也可能人死牛毙,百姓们家破人亡。这些情况,听说朝中大臣在年初也曾向中宗皇帝上言过,请今上驾幸东都洛阳,以稍稍缩短关中、江淮送粮的道路,但今上因为皇后的故乡在西京东南附近的杜陵,不准东幸之请,还斥责上言大臣:“朕难道是自找产粮之地,才有饭吃的‘逐粮天子’么!”而今目睹运粮百姓的悲惨景况,再回忆许州饥民的怨声载道,先贤所说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言,猛地涌上心来,不觉痛心疾首,心急如火,恨不能长出双翅,飞进殿堂,跪在丹墀之上,向今上痛陈国事日非的险状。
可是,从京东客店到含光门,真可谓近在咫尺,远在千里。这不足五里之地,他赳赳武夫,竟然走了一个多月,还未进入含光门!是官卑职小,无从得进宫门么?但正是今上自己,在景龙二年二月七日敕道:
仗下奏事人,宜对中书门下奏。若有秘密,未应畅露,及太史官,不在此限。
他虽官卑职小,但事涉弹劾总宰,甚至涉及皇后、公主的秘密上言,当然按敕不在此限。同时,去岁,即景龙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今上又敕道:
诸司欲奏大事,并向前三日,录所状一本先进。今长官亲押,判官对仗面奏,其御史弹事,亦先进状。
这些敕旨,向朝野间表明:君是明君,纲纪严密。但曾经这样赞叹过的许州参军,此番却深深明白那不过是一纸空文。倘若他真的按敕旨去做,不做燕氏门中白吃俸禄的子孙,却会作后党刀下的冤鬼。什么欲上秘密之言,即可绕过中书省上呈?什么录本先进?他一概不敢相信。他现在要办到的唯一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找到一条面君之道:只要有那么一天,让他在今上前把要想呈奏的话都说出来,死也无怨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觅夜筹总算把机会等来了。
昨天上午,他在东市徘徊,无意间和来西京的北平县王旭相识。当他得知对方是奉旨进京受封赏的斜封检校官时,心头一亮,很快就和王旭打得火热了。在交游一日后,他便请王旭“携带”,一觑天颜。王旭拍着大乳颤动的胸膛慷慨应允。
时间就在明日:六月五日,来自全国的数千斜封官将去定昆池,朝拜皇帝、皇后,开始为期一旬的“老母节”庆典,其间包括赐宴曲江,临潼骊山朝老母庙,“掷饼大酺”……燕钦融希望明日就能面睹天颜,一抒耿耿忠心。王旭后来发现这位新朋友老是担心明日不能得进定昆池,就不以为然地对他说:“老兄可是亲眼看见的:我不仅是奉诏进京的检校,还是那当今皇后身边,显赫无比的近侍的嫡亲外甥!凭着这么一座靠山,保你得见大家就是!”
当时燕钦融虽不无勉强地向他频频致谢,但心里的愤怒之火灼得他真快要发疯了!他,堂堂朝廷命官,却无从得见天子,吐露报国忠君的耿耿心怀,反要求这斜道旁门买来的滥官才得如愿!“可怜这一片赤诚,满腹经纶,却比不得他狗钻蝇营、几缗臭钱!……”想到这一点,这铁骨铮铮的汉子竟泪水纵横!他整整一夜,都未曾合眼。几度,他从床榻上愤然站起,想立即回到偃师家中,埋名隐姓,奉老母,了余生。可几番,他又似乎听到郎岌在象蹄下的惨嘹之声!“不能啊不能!郎岌,一白衣士子,尚且以凛凛豪气,死之于谏;我燕钦融当遵母命:‘你不能武死战,也该为君父社稷,文死谏!’”
他强忍满腔怒火,满心的厌恶,仍从王旭游……
昨日,他却差点一剑砍了王旭!
那是在黄昏时分,王旭命人请燕钦融去他下榻处的豪华旅舍,共度良宵;谁知燕钦融到了他那下榻处时,王旭早已醉得二目通红,口舌木钝了。他一见燕钦融来了,竟跌跌撞撞地扑过去,拉着燕钦融嘤嘤地哭起来。
燕钦融见他这模样,心里一沉,顾不得那醉鬼一身酸臭酒味,重把他扶到榻上,忙问:“难道受封之事有阻?”
“不、不……哎……!”
燕钦融听他这一说,放下心来。这才转身掩了房门,回到榻前,问他:“那你为何如此这般啼哭?”
“哎!燕兄!我恨我那该死的娘老子啊!”
燕钦融一怔,立即悟到王旭指的何事了。于是宽慰他:“后日才是晋谒之日,令尊令堂,一定会将银钱派人押到……”
“谁稀罕他们的臭钱!呜呜!”谁知王旭听燕钦融这般劝慰,反而一头跳下榻来,怨恨更深地嚷起来。
燕钦融虑到面君之日已近,怕王旭酒后失言,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