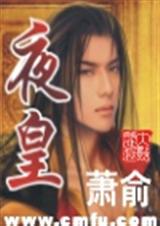唐明皇-第1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哪!”那幕僚一下子明白了主人的用意,忙大声回答,好让州县人役都能听到:“我们这位相爷,连王公大臣,也挨他的骂呢!”
“今上亲幸贵县,”刺使此刻却又一本正经地对县令道,“贵县也确乎应细察在先。殿前廊柱石龙身断,也委实不成体统呀!”
“这这这……”县令一直回不过神来,正在担忧着还有比宰相发怒更可怕的事——龙颜大怒——此刻听上司提及此事,煞白的脸又骇得发青,结结巴巴地向上司求救。
“贵县不必如此,”知道銮舆快到曲阜,出了漏子自己主人也大有干系的刺使幕僚,忙又悄声对二人道,“张相国虽好面折百官,但只要我们州县尽到心意,也就太平无事!”
“尽……尽到,心意?”
“唉!事已至此,就不要闪烁其辞了吧!”
“二位大人勿急,小人闻听朝中友好说过:相国虽广有才智,但却好贿!”
“是么?”
“一点不假!来曲阜前,小人便已想过:圣庙宝藏中,不是有—珍宝,名唤‘记事珠’……”
“是是是,有这件宝物!”
“二位大人设宴接风,便可将此宝献上!”
“啊?!”州县官员却有些迟疑起来。
“献吧!若出了漏子,小人愿以身家性命担保!”
馆驿的夜宴早已收场,州、县官员俱已辞去。正如那幕僚所预计的那样,宰相在席上的兴致颇高,不仅根本不提石龙断裂之事,而且还临席咏得一首踏歌词,亲自调教那六个刺使专道从兖州用快骑接来的歌伎和弦而歌。酒,也因鲁地名厨献上的鲁地特产——鱼肴,饮得十分尽兴。此时,宰相仍兴犹未已地让刺使留下的歌伎伴着他,在才布置起来的暖阁里,击案赏着歌伎们的轻讴漫吟。
但是,中书舍人张九龄,象他惯常一样,酒只饮了三巡,对佳肴也只是箸到而已。刚刚送走州县官员,本想利用与宰相独处僻地,相对清夜、一吐胸臆,但见宰相狎伎而歌的兴头正高,他又不忍去扫他的兴头——一年多来,为了东巡封禅事,他也委实太累了!
但是,面对国情政事,尤其是本次东巡中看见今上的一些举止,他忧虑甚重,多么想尽快和宰相一吐为快啊!可是,他几次临近暖阁,看见须发皆白的宰相脸上现出的欢悦神情,便又黯然地轻轻摇着头,走回自己的寝房。知道他脾性的仆从,为他拨得烛光明亮,烘得锦被生春,早躲得没有了影儿。他重重地叹着气,掩上房门,随口吟道;“幽人归独卧,滞虑洗孤清。持此谢高鸟,因之传远情。日夕怀空意,人谁感至精。飞沉理自隔,何所慰吾诚?……”
他是在车驾未启东都时,听见王毛仲谈到刘家庄一事的。和霍国公对此事有着同感的是:作为东都留守的李林甫,竟明知刘庄冤情不报,指为谋逆请有司清剿,其人其心已可想而知!再加上他和武惠妃日益明显的往来,张九龄已深为惕戒。眼下,王皇后被废而死,大驾回銮,很快就要面临册立新后一事。看平日形状,皇帝选择惠妃作为新的六宫之主,几乎已成定局。这个从皇帝执掌玉玺以来,一直就觊觎着六宫首位的惠妃娘娘,早就遣姜皎暗中疏通过那时还人微位卑的张九龄。从惠妃这种举止上,张九龄品出了这个深受今上宠幸的妃子,居心叵测。除严辞回绝姜皎而外,也曾对宋璟、张说提过要留意于她。现在,如果她真成了六宫之主,必定要促使今上大用李林甫这样的臣工。自然,大受倚重的李林甫,又会推出寿王入主东宫;寿王尚幼,难辨贤愚。但六宫之主是武惠妃这居心叵测的妇人,庙廊之上是李林甫这等奸佞之辈,刚刚趋于鼎盛的大唐江山,只怕又将妖氛万丈;宗庙社稷又将堪忧呵!
张九龄正是怀着这沉重的隐忧,随君上路东巡的。到了郓州地界,只见雷泽、巨野诸县,数十里不见一户人家,阡陌中狐鼠遗矢,看不见一茎稼禾。越往后走,其荒凉情景,越令他触目心惊!正是在这重重忧虑和亲目所睹“国尚未大兴”的现状激励下,张九龄再次上本谏君:“大驾东巡,当以察吏情、视民困、明中兴智术为主旨,若百姓屡受重扰,则不足以告成功于天地!望陛下明渝所从,以副告成之名!”
使他欣慰的是;皇帝不仅准奏下敕,严束从属,不得扰民,而且还常将此本,置之坐隅,以戒左右。前不久,皇帝在泰山脚下行辕中赐宴,还对张说深有感受地说:“朕往昔也曾屡遣使臣分巡诸道,察吏善恶;但本次朕因封禅历经诸道,方知使臣负我多矣!以朕观之,本次朕所见刺使几近百人,然怀州刺使王丘,饩牵之外,一无他献。魏州刺使崔沔,供张无锦绣,示我以俭。济州刺使裴耀卿,上表数百言,皆是规谏之辞!如此三人者,不劳人众以求荣宠,真良吏也!”说毕,还亲自举杯,赏赐怀、魏、济三州刺使。当时,张说率百官离座山呼祝贺,张九龄虽举杯跪地,却被满腔激动的浪涛堵住了咽喉,没有呼出声来。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他又重新佩服张说请驾东巡之举。春秋鼎盛的君王,走出宫禁,亲睹国势吏情民俗,确也对朝阁有益;同时,他也再次暗赞:“今上,明君呵!”
但是,东封一毕,銮舆开始返归东都,张九龄的心情又慢慢沉重起来。不错,眼下的宰相和宋老相国相比,更富智术。可和张说相处愈密,中书舍人就发现:眼下的宰相却没有新罢为开府仪同三司的宋璟的背脊硬!另外,大约因深知自己富于智术吧?这位宰相,也缺乏宋璟那人莫测其际的深沉!这两个弱点,虽存在于冢宰的身上,可和大唐朝今后的前途,是继续趋向鼎盛、还是又出现武周、中宗、睿宗三朝的衰弛,真可谓大有干系。正因为他缺乏宋璟的刚直,在皇帝要册封武惠妃为六宫之主时,他做不到宁死不奉诏;正因为他缺乏宋璟的深沉,李林甫就可能瞒过他的两眼,动摇台省!……那样一来,朝政虽有明君总揽,但武氏和李林甫等人重演韦氏和宗楚客故技的机会却增多了啊!
李隆基虽不愧是一代明君,但是,从一入朝便任言官的张九龄,却也从今上众多的举止中窥出,他和前代明君太宗的志趣举止颇多异处。曾在集贤院供职著作的他,从太宗实录中深刻地了解到太宗登极后,常以隋炀帝失政为镜鉴,在开创贞观盛世之前、之后、直至魂归梓宫前夕,都不敢生骄纵之心;在接受极谏上,虽也曾厌烦过,但总的说来,还是力求“从谏如流”、做到兼听。今上和太宗相比,就深令张九龄担忧。眼下,今上就往往在殿廊上、宫禁中,有意无意地自夸治国之功,和轻易不敢言成功的太宗爷相比,其骄矜之态,业已毕露;在听谏上,不仅已露厌嫌之情,而且从贬“照夜白”为凡马,暗示厌倦极谏到公然罢宋璟相位一事上,已表明今上对不顺他意的直言极谏,已是深恶痛绝了。
对这样的君主,就更需贤良智士不断的规谏,而且要能象宋璟那样,有时敢于逆龙鳞到忘死的地步。
他是崇敬宋璟的。但是区区中书舍人,在即将面临的重大朝政面前,位卑言轻!此番能和宰相一道先来曲阜安顿皇帝祀祭孔圣事宜,正是向宰相进言的良机呵!
想到这里,张九龄决心要去扫宰相的兴了。他出了卧房,走到了歌声琴声更为婉啭动听的暖阁外,朝领人在阁门口伺候的相府总管张寿招招手。
“子寿,快坐下叙话吧!”听了总管俯耳通报,张说拈须一笑,拂拂袖,遣退了兖州歌伎,叫总管把中书舍人请入暖阁。特别看重张九龄的宰相,破例地戴好乌纱,穿好内镶丝毛的厚底朝靴,坐在暖阁的半可仰卧的软榻上,礼秩周到地接见张九龄。张九龄刚撩袍入阁叩拜,他也忙一欠身,唤着九龄的字,指着与自己软榻相邻的坐榻,说。
“子寿久有心腹之语相告,故有扰君侯雅兴,望君侯赦子寿鲁莽之罪!”
“子寿不说,老夫也知。”出乎张九龄预料,张说竟含笑而答,“子寿是为着六宫之主易置一事,夤夜来告吧?”
“君侯明鉴,子寿正是为此而来!”张说的回答,使张九龄悲观的胸间,升起一股希望。他激动地、迫不及待地回答着。接着,又追问道,“难道今上已垂询过君侯了?”
张说拈须微微一笑:“就是我等伴随今上下东岳之夕,今上即已向老夫言及:拟册惠妃为皇后……”
“啊?”张九龄听宰相这样一说,那心房霎时间涌满了乌云,他一下从榻上立起,紧张地追问着张说。
“王皇后大薨之后,老夫即已有所准备;当今上垂询老夫时,我即于鱼袋中呈上表本。”张说眼里闪着得意的光芒,回答张九龄;接着,他朝阁外低声唤道:“张寿!”
“在。”张寿赶紧走进阁来,回答着。
“取爷的紫金鱼袋来!”
张寿忙到自己房中,取来紫金鱼袋,呈给张说,又忙着退出阁去。
张说将鱼袋递给张九龄:“内有老夫所上表章副本,子寿看来。”
“卑职谢过君侯!”张九龄一边接过鱼袋,一边叩谢。然后以急切的心情,从袋中取出副本,只见上面写道:
臣闻《礼记》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公羊传》曰:“子不复父仇,不子也!”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丁兰报木母之怨。陛下岂得欲以武氏为皇后,当何以见天下人乎!不亦取笑天下乎!又,惠妃再从叔三思,再从父(兄)延秀等,并干纲纪,乱常伦,迭窥神器,豺狼同穴,枭獍共林。且匹夫匹妇欲结发为夫妻者,尚相拣择,况陛下是累圣之贵,天子之尊乎?伏愿详察古今,鉴戒成败,慎择华族之女,必在礼义之家,称神祇之心,允亿兆之望。伏愿杜之于将渐,不可悔之于已成。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复自有子。若惠妃一登宸极,则储位实恐不安;古人所以谏其渐者,良为是也。昔商山四皓,虽不食汉廷之禄,尚能辅翊太子,况臣愚昧,职忝台省乎!
“壮哉此本!”张九龄读到此处,早忍不住击着榻沿,赞出声来。他没有料到皇帝竟在东巡途中,便向宰相垂询过立后之事、而且明白指名惠妃;他更没有料到宰相也早就草成奏疏,疏辞又如此犀利、句句直陈利害,如果掩去臣工姓名,中书舍人还以为这是宋老相国的奏疏呢!他一边合上疏本,一边又情切地问,“不知今上御览之后,是何旨意?”
“哈哈哈哈!”宰相却先用敞怀大笑回答张九龄。仅凭这一串笑声,张九龄已定了大半个心。笑后,宰相才回答张九龄,“次日一早,今上便将老夫宣至东岳行宫,对老夫道,‘昨夕朕询卿之事,且作罢论!’哈哈!子寿,你观老夫虽老,‘尚能饭否’吧?呵?哈哈哈哈……”
听宰相转述皇帝的回答,张九龄虽不如右宰那么心满意足,但此事先争得搁置罢议,也很不容易了。事在人为。但却松懈不得!待宰相笑声一过,九龄便恭敬地将奏疏副本送还宰相倚身的几上。退回座上后,又揖手说道:“君侯宏论,子寿赞崇非常!今尚有李林甫,密与武氏联结,与当年韦逆联结宗楚客、太平联结窦怀真,窥测神器、图谋大宝相仿佛,且子寿观林甫,常以顺今上之捐,承恩用事,辩给多权术。君侯不可不备!”
“李林甫?”张说听到这个名字,拈着胡须,似乎在回忆一个较为陌生的姓名似的,好一会,才“哦”了一声,“那东都留守么?……鼠辈何能为!”以轻蔑的口吻说出这句话后,张说微微一欠身,“明日事烦,子寿且回房中歇息吧!”
“有扰君侯了!”张九龄虽对宰相在李林甫其人之事上的态度深为忧虑,但想到宰相年事已高,今夜又已深,不便再作长谈,忙起身告辞。在返回寝房后,中书舍人一再提醒自己:“张相尚不知此人绝非寻常奸佞之辈。子寿呵!你要常常提醒宰相才是……”
“李林甫?哼哼!鼠辈何能为!……”
其实,就在张九龄在房中暗自提醒自己的同时,宰相也并没有歇息。他只叫张寿领着几个贴身奴仆入了暖阁,给他摘去乌纱,脱去紫袍,换上居家皮棉袍、帽,把炭火拨得更旺后,又把他们遣出阁去、放下重帘,在暖气溢荡的氛围中,也和中书舍人一样,想着同一个人:李林甫。
刚才,宰相虽然在张九龄提及此人时,面露轻视之色,但他的心里,其实并非如此。大半生沉浮于风险浪恶的宦海中的宰相,怎么会不留意那从小小御史居然爬到东都留守地位的白脸柳眉后生?在中书省四方馆见过此人履历的张说,了解到他是唐高祖从父之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但是,自长平王之后,这家族的衰落是明显的:爵位终断于李叔良。太宗封赏之制的严格,武周灭绝李唐宗室的严酷,使这曾孙凭着十年寒窗之苦,才登堂入室。不错,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