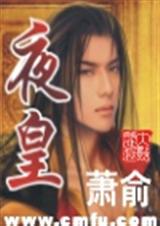唐明皇-第1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寿王将入主东宫,成为大唐储贰。
惠妃自将名冠六宫之首,成为名实皆副的国母!
而今上春秋已高。
如果今上一旦禅位,“则力士尚有立足之地”,但今上一旦归天?!……
惠妃、寿王、李林甫……都知我不曾相附,到了那时,力士被贬、赐死尚是小事,只怕我满门、九族皆难逃其斧钺!
“禀阿翁,清点已毕。”
就在高力士千思万虑之时,宫使们却朗声禀告,暗示着他应下令出宫。
出宫!
出宫!!
出宫!!!
“宫阙入云,虚其一步,必坠地狱!”力士望着楼外浮云,暗自心惊,“力士啊力士!宫闱惊涛,汝经历数番;本度风涛犹为险恶,汝将如何行事?如何行事?”
时近申时,七十里方圆的大唐西京长安,被艳艳斜阳,照映得万壁橙红,屋瓦闪亮。奉敕使大将军高力士领着两班宫使,坐着惨紫篷罩大轿走出兴庆宫南墙中门通阳门,沿着东市的南北大街向中书令府邸常乐坊而去。
“嘡!嘡!嘡!……”就在这批宫使快要临近常乐坊时,从东市方向,传来声声收市钲声,力士感到轿伕们的步履加快了。他从轿后壁窗朝捧着皇帝赐物的宫使们望去,一眼就望见那被放于端盒中的、用黄绫覆盖着的暖炉,他又叹着气回过头来,闭目思忖:“事已至此,也只有奉劝子寿公乞还骸骨了。要他去奉废立之诏,此公也是断不会允的啊。”阵阵酒曲之香,随风送入轿中,“真快,已到了常乐坊了。”这时,轿却一下子停顿不前,力士从侧窗撩帘,伸出头去正欲询问,但他立刻看到原来是一群金发碧眼的波斯男女,男的头缠绸巾、女的面罩垂胸,都抱着一部景教经文,口里喃喃诵着“真主啊真主!万神之神……”向西而去。轿旁近侍见力士伸出头来,忙扶轿低声禀道:“阿翁,这是常乐坊中造制胡酒的胡儿,去义宁坊大秦景教寺院作礼拜者。”力士点点头,放帘缩回头去,借此稳稳心神。
“奉敕使大将军高力士,宣敕到!中书令张九龄接——旨呀!……”轿伕重新起步不久,便又停下轿来,一阵宣告声,使力士知道已到九龄相府,即叫声:“打帘!”近侍应声打起帘来,两名宫中小儿躬身到了轿门,搀着力士下了轿。
相府人役闻听宣告,一边火速入内禀告九龄,一边打开中门,列班恭迎;力士从捧盒宫使手中接过端盒,张九龄已穿戴齐整,疾步来到中门靠右肃立,揖袖迎接宫使。捧着御赐物品的高力士,数月不见中书令,而且今日又是领着这样的圣命前来张府,心中虽有千言万语,却碍着皇家制度,难以倾诉,他只有恭捧暖炉,领着众宫使,昂然而入。
当张九龄导着力士一行,转到中堂,令仆从排开香案后,便听力士道:“中书令张九龄跪接圣上赐物,望阙谢恩!”
“臣九龄,深谢我皇天恩浩荡!敬祝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张九龄如仪山呼跪谢完毕,立起身来,力士便将端盒递去,并趁势向他递了个眼色;九龄会意,即向本府总管道:“花厅烹茶,稍敬众宫使!”
众宫使便由总管等领出中堂。
九龄屏去众人,这才将端盒放置于案上,上前携着力士之手,喘吁地道:“辛苦了!请坐!”
力士并不忙归座,却以目凝视这位大唐宰相。几月不见,九龄两鬓皆白,面呈浮肿病容,语音里渗着痰吼之声,“事已如此,还是休做栋梁作暖炉为好。”力士心里凄凉地想着,反手搀着张九龄,将坐椅移在一处,并椅坐下。
“子寿公何不一视赐物?”见九龄要说话,力士却先强作笑容,指指案上端盒,问道。他想让张九龄看了赐物,悟到皇帝用意,他好一吐心曲。
“九龄不看,也知其物为逆时背势之物。”虽知九龄岁虽高而心思机敏依旧的高力士,听了张九龄这句回答,也不禁深感惊异,半晌作声不得。九龄见力士这副神情,淡淡一笑,道,“随大将军奉敕出赐大臣的宫使,皆捧一白羽扇,唯九龄以一端盒盛物而赐,此中圣虑,乌用揣测。恰好九龄有感遇之诗四章,请大将军转呈今上,以为回报。”
力士忙从九龄手中接过诗稿,仔细看来。那感遇之一曰: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
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
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
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
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其二曰: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其三曰:
幽人归独卧,滞虑洗孤清。
持此谢高鸟,因之传远情。
旦夕怀空意,人谁感至精。
飞沉理自隔,何所慰吾诚?
其四曰: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力士本已看毕,却仍旧注目诗稿,不肯抬头,暗自思谋:“今上心性,已非昔日,此四章感遇,一经呈奏,只怕曲江凶多吉少!……明言不予呈奏,我又能以何言向曲江解说?而且,细揣此诗,曲江亦深揣圣上今日之心性,故而作此《感遇》,我即便不予转奏,他又未必不径直奏呈,仍将取祸于旦夕……唉!难、难、难……”
“若大将军不便转呈,请赐还于我,九龄自当面奏。”九龄见力士面呈难色,揖袖道。
“果不出我所料。”力士心中暗暗叫苦,此时只好抬头笑答,“堂老,非力士有何不便,不愿转奏呈递,只是……”
“禀相爷!”
就这时,相府阍官却匆匆来到中堂,向张九龄禀事,但见高力士正在与之言话,便顿住话头,但又露着焦急神情,望着九龄。
“高将军在此何妨?尔禀事吧!”九龄朝司阍官儿命道。
“是,相爷。”司阍官儿禀道,“惠妃娘娘的近侍牛……”
“他又来了?”九龄猛地切断司阍官儿的禀报,一拂袖,“不见!”
“相爷!他说有极紧要之事,还是惠妃娘娘口谕,要向相爷……”
“叫他走!”
“慢!”高力士听到这里,已知来者是武惠妃心腹牛贵儿,同时听见司阍官儿说他要向九龄密告惠妃口谕,不禁心头一动,忙制止畏畏缩缩正要退出中堂的司阍官儿。
“高将军!……”
“堂老暂且息怒,”力士急急稳住张九龄。然后对司阍官儿道,“将他迎至客厅等候。”
“是。”司阍官大大松了一口气,应着,匆匆退出中堂。
“高将军,你素知子寿心性,我堂堂中书阁臣,绝不与此辈谋面!”
“彼言有惠妃口谕相传,”力士向张九龄提醒着,“或有一使圣上明悟、有益社稷安宁之机运出现,则何不见?”
“高将军!……”
“国事如此,堂老当以社稷为重呵!”
“唉!……”九龄见力士焦急相劝,不忍执拗,只得起身:
“客厅侍侯!”
相府仆役应声而出,搀着张九龄,走出中堂,转至相府前堂左厢小客厅落坐。
“导客入府!”
总管传出话去不久,司阍官便引着牛贵儿出现在客厅门前,那眉清目秀的宠妃心腹奴才,一见张九龄,便一头跪下去,朗声唱道:“牛贵儿领惠妃娘娘懿旨;请相爷安!”
九龄欠欠身,冷冷地用鼻音哼着一般回道:“祝惠妃娘娘安泰!”
九龄并不令他进厅,牛贵儿也不嫌尴尬,叩头之后,走进厅来,垂着绯袍袍袖,立在张九龄座旁道:“小子一来代娘娘请相爷安,二来,尚有娘娘懿旨传降。”
“唔。”
“不知相爷可已将圣上赐物领得?”问着这句话,牛贵儿斜着那双闪悠悠的眼睛,偷觑着宰相神情。
宰相却仍阴沉脸,用鼻应了一声。
“相爷,”牛贵儿赶紧收回目光,道,“那赐物因圣上也曾向惠妃娘娘提及,故急得娘娘心疾复发!”
“呵?为了九龄领此赐物之事么?”
“是呀!是呀!相爷,”机灵的牛贵儿一见九龄脸色稍呈红色,知已被自己的话将其心拨活,忙不迭地说道,“惠妃娘娘虽知相爷不肯奉今上废立东宫之诏,但娘娘深知相爷对大唐江山忠心耿耿,甚是赞佩!圣上不悦,竟赐那……物,娘娘怕庙廊大器,因圣上一时喜怒而折弃,故一病不起……方才,娘娘急遣小子,来此告谕相爷:‘自古以来,有废必有兴。今废立东宫之事,若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望公……”
“呯!哗啦啦……”
不待牛贵儿说完,九龄早朝身边几上猛地一拳击去,几上杯盘应声落地!还不等牛贵儿从震骇中回过神来,张九龄一迭声命道,“与我赶出去!”
“喳!”
相府人役,齐声相应,一下子拥上,拖着牛贵儿,推出相府。
“哎,堂老!”正这时,屏壁后闪出高力士来,他喜滋滋拉着九龄道,“大喜呀!”
张九龄闻言,一甩袍袖、勃然色变:“高将军!你视子寿为何等样人?‘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生为大唐臣子,死为大唐厉鬼,绝不从尔女子裙下求宰相!……”
“唉!堂老!”力士忙收了笑容,附着九龄耳朵密说了一阵。
力士尚未说毕,张九龄早已发急地朝总管命道:“速速备轿!尔等疾去追上牛贵儿,万不可放走了那个奴才!”
第四章
“当!当!当!……”
当东市方向传来三百声歇市钲声时,犹在花萼相辉楼临西阁抚轩沉思的皇帝李隆基,暗中揣度道:“力士早已到了子寿府邸了!这一次,也真难为他……”揣度着,他又遥遥向常乐坊方向眺望,落入他那视力已不如前的眼中的,却是西下的阳光,人流滚滚的京师南部各坊,以及轮廓模糊的、被斜阳衬得半明半暗的大雁塔那巍巍塔影。阳光,人流,塔影,使就要度过五十大寿“千秋节”的皇帝心底,唤起一股股不可遏制的志得意满的激情:“自太宗后,唯朕,才使大唐江山如此昌隆、升平!……子寿虽有泱泱宰臣风度,终是人臣心胸,总欲以俗情视天子!其举止可恶,然其识见堪怜……朕以斯物相赐,也不枉我君臣一场。”自力士奉敕而去,心里总感欠安的皇帝,这样一想,顿觉坦然了;他收回远眺的目光,却又想到了高力士,“谁知我这富有四海、万邦拱服的大唐天子,到了今日,在庙廊上,知朕者,唯一林甫;后廷内,唯一力士老奴……”想到此处,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他又想起方才与力士相谈中提到王毛仲,以震慑对方的举动,不禁暗暗感到愧疚,“彼之心性朕还不知?何必那样?何必那样呵!”
“启奏陛下!御史大夫李适之,有急疏呈递。”就在皇帝回过身去,要宣敕太监传敕尚食奉御,精心安排今夜为力士在沉香亭阁所赐的洗尘宴时,近侍却向他奏报,并向皇帝跪呈了李适之的奏疏。
对满朝文武、尤其是王公大臣负有监察使命的御史台官员,在疏奏、内谒方面,享有其他官员、包括省台阁臣在内的官员不可及其背项的权利。正因为这一点,李适之的这份奏疏可以不必呈放在勤政务本楼的御案上,等待皇帝依秩挑览,他可以直接呈递宫使,而宫使也不敢延误,立即就转呈皇帝。
正要启驾下楼,去往沉香亭阁的玄宗接过李适之的奏疏,命内侍将座榻移向栏边,就着夕阳之光,边展奏疏,边忖道:“难道又是何臣在知朕有废立东宫之意后,有怨尤之举么?……”而在他的脑际,闪出第一个可疑的影子,便是自己的大哥宁王李宪。这位官封太尉,原名李成器,后来避今上之母昭成皇后之讳改名为“宪”的大哥,虽然远比业已去世的两个兄弟岐王李隆范、薛王李隆业惕戒恭谨,“但年近古稀的人,未必就不会在他衰朽之年,做出一反常态之举?而且,如果说他人出面阻扰废立之事尚不足虑,那么大哥出面……就颇费周折了……”但是,当皇帝展开李适之的奏疏一看时,却愣住了:“他为其先祖之事论辩?!……”
玄宗颇感诧异地拭拭自己双眼,再向奏疏看去,分明见其疏头写道:
御史大夫、弘文馆学士、赐紫金鱼袋臣李适之为先祖承乾废、死非罪事特呈奏吾皇,并论辩之……
承乾废、死非罪!其孙李适之上疏为其论辩!
皇帝从李适之的奏疏上抬起头来,略一思忖,倏地站起身来,将奏疏一下抛掷在座榻上,脸色正似楼外天空:渐渐变得阴沉无光。
太宗即位后两月,冬十月癸亥,立皇子中山王为太子。这位当年八岁的皇太子,因生于承乾殿,故太宗以殿名为子名。
李承乾入至东宫十七年,即太宗贞观十七年前,时论皆称其贤。想不到就在贞观十七年春,发生了齐州都督、齐王李祐因昵近群小、谋反作乱一事,由此受到刺激和震动的李世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