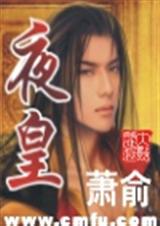唐明皇-第1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十分感动,乃与哥舒翰杀白狗为盟,各自撤去守边兵将。从此,吐蕃畜牧遍野,胡汉往来,亲如一家。
谁知今年初,吐蕃与勃律两邦不和,竟起战事。两邦遣使奏告朝廷,皇帝命崔隐甫前往检视回奏。
那崔隐甫一到河西,见吐蕃未设兵将防边,自欲求边功,便矫诏命哥舒翰袭击吐蕃。哥舒翰强争不得,只得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二千余里,直至青海西,大破吐蕃,斩首二千余级!
乞力徐幸得逃脱,遣人书责哥舒翰背誓,称:“吐蕃从今尔后,再不朝贡大唐天子!”……
“这位驸马公,竟干出这等损我大唐声威之事!”李适之听了,也恼怒异常,“可惜太宗爷在世时,耗了多少心血,才使吐蕃臣伏大唐、使西陲境安民宁啊……”
“是呀!”严挺之离开座榻,痛心疾首地回忆着,“尔后韦氏擅权,诸邦叛离;今上允准姚相三十年不幸边功之请,二十四年来,修好诸邦,重使万国来朝,民享安乐,方有这举世瞩目的大唐中兴之盛景。自此之后,只怕国家又要多事、黎民又将罹于刀兵之苦了……”
“堂老之意?”
“张相要请御史台诸公,将此情从速奏告今上,弹劾那‘伏猎’驸马欺君罔上、逼反吐蕃、大损国威之罪!”
“请公致意堂老,”李适之亦起身正色回答说,“适之等当尽其能除此祸国殃民之辈!”
“林甫等俱疏上奏,”严挺之焦急地告诉李适之,“要今上升赏崔隐甫。故堂老望尊台从速行事才好。如彼等之奏请已获今上之允……”
“事实俱在,纵有圣命,亦不足虑!”
“大夫呀,”严挺之靠近李适之,低声急切地相告,“话虽如此,奈何圣心早存开边耀武之意,如弹劾不力,彼等竟因之而入宰相行,国事更堪忧虑了!”
“哥舒翰的表奏呢?”李适之一听,也骤觉事非寻常,忙问。
严挺之笏嚢中取出哥舒翰的表奏文稿,递交给李适之,又频频告戒:“千万小心些!”
“大人放心,”李适之小心地将那文稿笼入袖内,朝严挺之揖别,“不出今晚,适之便将弹劾之表,送入南内!”
严挺之回揖之后,二人并肩向外厅而去。
严、李二人的身影在壁门处刚消失,中厅的耳房内,走出一个绿袍文吏来。这人青须垂在胸前,犹如一排钢针。白净的脸面上,一双鹰目,在浓黑而粗短的眉下,闪着几缕绿光。他估计二人业已去远,这才重新进入耳房,轻轻地关上房门,迅速走向卷案堆积如山的长条案上,从卷案底部抽出一迭文稿来,就着窗隙的阳光,看那文稿抬头处的文字,只见上面写着:
京兆法曹、臣吉温特具疏奏呈中书侍郎严挺之私情枉法事……
看到这里,绿袍文吏兀自点点头,在案后方几上落座,沉思片刻,然后又从笔架上抽过羊毫笔来,饱蘸砚中浓墨,在那弹劾奏章上疾书道:
……挺之身为中书阁臣,不遵宪章,枉法徇私,频入御史台,密求营解罪囚王元琰,若纵此行,则纲纪何存!故微臣依制奏呈,伏望陛下重究不佞,以彰祖宗之法……
写毕,他又反复揣摸,然后才阖上密奏疏本,在封口处施印密封之后,又提起笔来,在封面上恭正地写道:
呈
高大将军转奏
京兆法曹 吉温谨呈
写好之后,吉温又瞑目静坐沉思了好一会,这才又从案头取过一张纸来,提笔写道:
尚书李公台鉴:
公所命之事,温已遵命行事。宦途半生,方遇明公知己!挺之细事,夫何足道!纵明公欲制南山白额猛虎,亦不足缚也……
“阿翁,夜已深了……”
头裹红布的宫中鸡人,缓敲竹梆,向大内各宫,送去子时已过的梆声,南内供奉小鸭儿,听了这阵梆声,悄声蹬上勤政务本楼,在近侍当值厅里,向仍就灯细看着两份奏章的高力士提醒着。力士听了,从奏章上抬起头来,朝这凹鼻青年供奉苦笑了一下,然后携着他的手说道:“你先睡去吧!人老了,嫌夜长呵……”
“阿翁,……”
“去吧,去吧!”高力士为了舒展一下有些发硬发酸的腰部,携着小鸭儿的手,缓缓站起来,把他引出厅堂,走向楼梯门口,笑着劝道,“明日无事,我们也去城外观看斗鸡去……”
“哼,谁稀罕那玩意儿?我要你睡一觉呀!……”小鸭儿抱怨着,但又怕因此更要延迟高力士的时间,只得嘟哝着,下楼去了。
当这瘦小身影沿梯而下时,高力士恍惚觉得二十六年前死于韦皇后之手的乃父解鸭儿分明又复活了……是呀,时光真如白驹过隙呵!一转眼,就是二十六年……那一位,要“效东方朔以俳优之身谏奏君王广行仁道”,这一个,也“不稀罕斗鸡这玩意儿”,要“以供奉之身行规谏之实”,其父其子,心性品貌都如此相肖呵!
出于对其父的敬重,高力士在和其姑父王毛仲不睦时,仍旧将小鸭儿当作亲生儿子一般看待,也正因为如此,机灵的小鸭儿得以在高、王二人的不睦中,判断出姑父对高的愤慨大多出于因急躁引起的误会。所以在姑父被皇帝赐死永州、姑母明义公主自杀以明其志之后,小鸭儿仍能和高力士相依为命。但是,每每想起亡友惨死之因,高力士便不愿意这机灵儿也象其父那样,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投入宫闱争斗的杀场上去。所以,无论小鸭儿抱着多么强烈的愿望,高力士都不和这亲生儿子般的年轻供奉谈及宫闱及朝廷之事,他要他游戏于人生,他劝他斗鸡、走马、甚至寻花问柳……
正因为这样,他以年高嫌夜长的话来搪塞小鸭儿的催促,而不告诉他自己正面临两封弹劾之章,十分棘手,不能安眠。
宫灯光下,小鸭儿的身影消失了,高力士这才回过头来,向当值厅堂而去。初夏的夜风,拂来龙池荷叶淡淡的清香,送入他的鼻中;这晚风,这芳香,使他觉得自己那沉重发麻的头皮顿时变得轻松灵动些了。他加快了脚步,转回了当值厅堂。
“该怎么处置呢?”高力士缓缓徘徊到栏杆前。珠帘,在夜色里闪着翠绿色的珠光,几个宫中小儿,从帘那边的临轩座凳上,发出细微的、诱人入睡的鼾声。力士不无羡慕地听着这鼾声,而心里却分明更加焦急了:“该怎么处置呢?……”
一道弹劾之章,系御史台御史大夫李适之所上,奏告驸马、陇县公崔隐甫逼反吐蕃一事;另一道弹劾之章,系京兆法曹、奉敕三司会审王元琰坐赃罪的吉温所上,奏告中书侍郎严挺之罔法徇私,暗去御史台营解王元琰一事。
这两道弹劾之章,如按力士本意,本应将李适之之本上奏皇帝,而将吉温之本留中不发。但是眼下,他却不可能照本意办理。
自去夏皇帝因张九龄扭牛贵儿闯宫见驾以来,朝野正直之士,皆贺九龄得仍留掌中书,东宫太子无恙。前不久,皇帝又下敕更太子及诸皇子名。太子李鸿,更名瑛。这些迹象,表明了皇帝不废中兴之志,圣明如初。
然而,深居内廷,随侍皇帝左右的高力士,却透过这太平的表相,洞悉了动乱的隐情。
原来武惠妃被牛贵儿一事气发心疾的当晚,又疾密令牛贵儿去咸宜公主府内,与崔隐甫、李林甫等人急商了对策。第二天,李隆基酒醒闻惠妃发病一事,即去南薰后院探病,那惠妃便依照林甫等人之计,诉说自己并未遣牛贵儿去张相府许以“长处宰相”之事;牛贵儿也跪地说他是去张相府看望宰相,并未造次乱讲,后来是张相胁迫自己在皇帝面前奏告出那番话的……皇帝见惠妃才只一夜不见,竟双颊深陷,朱唇泛着灰白色,两眼红肿,才说几句话又一头晕了过去,也悔恨自己失于详察,便责打了牛贵儿,致爱妃形神俱损。正在此时,咸宜公主又牵着其弟寿王,哭得泪人一般,跪伏在皇帝面前道:“母亲自潞州伏侍父皇以来,贤良贞顺,天下皆知其贤!今竟为东宫之事,大伤凤体。父皇啊父皇,此事传出,朝臣无不感叹,礼部尚书李林甫对驸马言道:‘东宫易主,陛下家事尔!何须宰辅奉诏?至使宫闱不宁,人臣之道何存呵!’……”
高力士暗窥到,阴沉着脸的皇帝,听到“东宫易主,陛下家事尔!……”之话时,剑眉一挑。不久,皇帝便将回答张九龄感遇之诗的敕报收回。
今年二月,皇帝便更太子名“瑛”,而寿王清更名“瑁”,细心的高力士推测道:“太子原名‘鸿’。鸿,万里鹏程之神鸟,正储君之喻也!今更名‘瑛’,只不过似玉之美石罢了!石无论美丑,也只能垫铺于地,而不能上升于天……寿王原名清,其含义甚平平;而今更名为‘瑁’,《周礼》云:‘天子执瑁四寸、天子常持不离左右者,非储君者何?可叹九龄、挺之、适之等满腹文才,尚未窥出皇帝复萌废立东宫之念乎!……”
据此,原本对九龄、严挺之已生极度厌恶之意的皇帝,在李适之上本弹劾驸马崔隐甫后,岂不是对这位继张九龄、严挺之之后的又一位省台大臣,也必将大为反感?那样一来,武氏、林甫等人就更为得势了……“适之之本,不能上奏呵!更况,即或今上能对崔隐甫略施薄惩,今上那开边之心,也是难以遏制的呀!”
想到此处,高力士返身入了当值厅堂,在长案后的榻上坐下来,叹着气,将适之的疏本放入柜中。与此同时,吉温的疏本,却那么显眼地落入他的视线。
看着吉温的疏本,吉温那双隐隐闪射着绿光的、深陷的鹰目在高力士的眼前溜溜旋转。
这位京兆法曹,与他的私交还算不错。在力士尚未认识他之前,便听人提到过这位排行第七的“吉七”在法曹任上连续按理过不少大案,专会倚法附邪,可称出入人命已十数年矣!作过京兆尹、已经故世的力士老友崔日知曾生动地告诉力士说:“这吉七为人巧诋,忍而不忌,有敢损其一毫眉睫者,必引而陷害之;其欲胶固攀附者,虽王公大臣,立可亲近!是一非常之人!”
事有凑巧,就在日知告诉他不久,在他四十生辰之日,这吉温便拜到了他的大将军府。不知为什么,居高位而不忘恭谨待人的内侍省大将军,一见吉温的相貌和这双鹰眼,对这位小小的法曹,便礼遇有加;不久,他就成了高力士外邸客厅里的常客。
他到力士府邸,不象其他来客,其中包括王公贵胄、皇子皇孙那样,开口“阿翁”,闭口“阿爹”、“大将军”,也不象许多外任官那样,将成箱的金银器玩,成片的田契庄院献上。他的称谓恭敬而不卑不媚,他的举止谨慎而不拘束,他的谈吐不多而所言者必当。这一切,都更令力士暗怀惕戒之心,举止上却颇为亲近。无论朝野间的议论对吉温怎么不利,但力士却亲近有加,并许诺将他荐于皇帝。小鸭儿曾愤慨地劝说他家疏远此人,他却笑而不答。他心头雪亮:“这是一柄天生的无心无血无情无义、专以喋血为乐事的斧头。我虽不用彼,自有用彼人呀!……”
三年前的一天,趁着皇帝心情特好,高力士将这吉温推荐给皇帝。李隆基在花萼相辉楼落霞阁召见了他。君臣相见,皆无一言,皇帝便叫“退”。当吉温下楼时,皇帝对高力士皱皱眉头:“是一不良人呵。朕不用也!”
“从那以后,此公久不上我之门了……”力士喃喃地回忆着说,“原来已去李尚书门上走动……为王元琰一案,他竟受遣西京御史台参与按理,看来,当挺之尚在为西陲不宁苦恼奔波之时,李尚书已暗中举此斧相向于挺之了。”力士苦笑着摇摇头,一把抓过那疏本,也往柜中放去。
“噫!”但他又缩回手来,重把吉温疏本放还案上,暗自咬着牙关回忆,“记得就在昨日,今上询及王元琰坐赃一案时,分明问道:‘朕闻竟有阁臣为罪人请托呀?’难道正是指的严挺之?如此,则林甫等辈,分明已奏告在先了。如将吉温之本留中,也不能解救挺之呵……转奏?则挺之大祸立降!唉,你这吉七啊……!”
“梆、梆梆!梆、梆梆!”
“四更了!”
报时梆声,将陷入愁苦思索的高力士催得坐立不安。他再度离开文案,独自在厅堂中踱步苦思。
“喔喔喔!~~”
一声鸡啼,引起了西京城内千声万声的鸡啼,这声声鸡啼,在力士的耳边,通通化成一句问话:“怎么办呢?”
“唔,有了……”力士突然停止了脚步,眉梢渐渐伸展,“林甫等或许已在今上面前奏告过严挺之了,但吉温这道弹劾本章,才是明攻挺之之举。我不如暂将此本留中,待天明挺之上朝时,即令小鸭儿密往中书省,要他上本今上,严究王元琰坐赃之罪;尔后,我再将吉七此本奏上,那样一来,哈哈!林甫呵!我叫你画虎不成,反类犬!……”
力士边想,边回到案边,将吉温之本锁入柜中,然后抬起头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