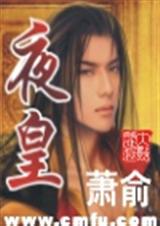唐明皇-第18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长期浪迹萍踪的生涯,练就了他适应环境的能力。曾视京师如万仞天阙的他,一旦涉迹其间,那层神秘的面纱在短短的日子里便被他看破了。而侍候皇帝作樗蒲之戏,更促使他大彻大悟,原来偌大的世界,处处皆是赌场;无论是盛名天下的圣君,还是市井流氓,无一不是赌徒!
这样一来,他不再甘于只掌樗蒲赌账了。在这外表堂而皇之的赌场上,他并非当年腰无赌资的杨钊,而是赌资富有的杨国忠。这赌资,便是他的堂妹们!凭此,他可以赢来万方珍宝、赫赫权势。
曾几何时?皇帝已输给了他乌纱幞头、绯抱金带。
但他并不满足这一局之胜。他要象一个有为的赌徙那样,利用自己的赌资,达到所有的目的。
……
“今上春秋已高,今后掌国的便是东宫。而这东宫,还会让贵府阖族继续厚沾皇家雨露么?真令林甫忧虑……”就在林甫召请他去中书省授给侍御史诰身、印信时,林甫竟完全洞悉他的心思,在文簿山积的大唐中枢廨署政事堂内,为他谋划起“赌势”来了。
他并未想到这一层。但林甫只寥寥数语,他就完全明白这赌场上还存在一个重大的烕胁。但是,对这个对手,该怎么办呢?
“国舅呵!仅椒房之因,欲永操胜券,难!欲使贵府阖族长胜不衰,当毋忘东宫!”
“东宫?”
“贵妃如早育龙种……”
“唔!”杨国忠那旋动灵活的双目,一下子明亮起来,但立刻又黯淡下来了:贵妃承恩,快十年了……或因皇帝春秋甚高之故吧……这绝非人力可及呵……
“国舅不必忧虑!倘无己出,也当另在诸王中扶立一人,入主东宫!……”
“承堂老大人教谕!”
“十郎老矣!”右相却笑盈盈地回揖着杨国忠,“且生平不通权变,唯知愚忠报效圣君,沥血呕心以酬知己!惠妃娘娘生前,十郎受其殊遇,誓扶寿王掌主东宫……惠妃娘娘虽魂归陵茔,十郎自当结草衔环,倾心供贵妃驱使!从此之后,自当与国舅同气,以护杨门恩荣永隆!……”
“东宫!”杨国忠却迫不及待询问着,“不知堂老眼下对那东宫之主,作何处置?”
“东宫近与戚里、户部尚书韦坚,旧属、陇右兼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结谋频繁,所图不轨。”见问,右相笑容顿失,柳眉紧皱,忧心忡忡地答道,“据有司探知,彼等将于明年正月望夜,密谋于崇仁坊景龙观!……”
“呵?那……”
“国舅不必忧虑!只是到了彼时,望与贵妃、三国夫人力谏圣上,割恩正国!”
……
“今日便是正月望日!”杨国忠领着宫使端着御赐佳酿走出南内宫门时,步履变得迅疾起来,“不知那景龙观中,是何动静?!……”他恨不能立即见到右相,问个明白。
“咚、咚、咚咚咚……”
与此同时,子城之西、鸿胪寺后的御史台衙署门前,响起了一阵令人胆丧的升堂鼓声!
头戴豸冠、身着法衣的御史中丞吉温,在升堂鼓声之中,在手擎法杖的人役护拥下,登上了西台大堂。在朱笔横架,签筒并列的长案后归了座。
“何事击鼓?”吉温向役长冷冷问道。
“禀大人!”役长一膝跪地,回答,“畿东风俗使拿景龙观观长于西台,击鼓请大人升堂!”
“带!”
“大人口谕!着畿东风俗使,解景龙观观长上堂呀……”
役长起身,立于堂门,向外威严地传着中丞口谕。
向北而开、象征主阴杀之意的御史台门外,出现了绿袍乌纱的畿东风俗使。依照先天二年九月一日敕令,御史台除遵制按察百宫而外,每年春秋两季,还要分遣台使,以察州县畿都官佐。春正月所遣之使,名风俗使;秋季所遣之使,曰廉察使。
对西京东畿县万年县巡察的春使,又称畿东风俗使。这绿袍使者,虽品流卑微,但连王公贵胄在内,得知其是西台春使以后,也无不退避三舍!此时,他领着随从,押着须发皆白的景龙观观长,步入大堂。就在他向吉温拜见时,两人趁堂上诸人毫无察觉,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吉温已明白景龙观中的网、钳,都已捕到了猎物。
“大使因何拿这道人?”吉温向畿东风俗使一抬手,让那大使让到案侧,问道。
“回禀中丞大人!这妖道联结皇亲、交通边帅、图谋不轨!”那大使指着道长,答道。景龙观道长一进西台,早已吓得面如土色;这时听绿袍风俗使指控之语,一下子从两个挟持着他的西台人役肘弯里滑了下去,瘫在案前,魂飞魄丧地呼道:“老道人冤枉!冤枉呀!……”
“挟起来!”
吉温从签筒里抽出一条法签来,朝道士近前一扔,冷冷地命道。两廊人役,虎啸狼嗥般应了一声“喳!”便拿着挟棍,铁箍,扑向老道士面前,将那老道一把抓起,又打跪案前。然后,拉直双臂,上了挟棍、铁箍,老道士已是吓得不知疼痛,只怔怔地由人役们摆布,既不呻吟号叫,也不抖颤。
“簿书录供!”吉温向案侧簿书吏吩咐一声,簿书吏赶紧在录供短榻上铺开笔砚纸张,屏息待录。
“大使速速推鞫!”
“辰时,”绿袍风俗使简略自陈道,“本使闻东宫车骑去往景龙观,本使亦率随从前往暗护太子车辇。谁知竟逢户部尚书韦坚、陇右兼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皆在这妖道室中!”
“停——录!”
“已录!”
“讲!”
“是。今上严敕戚里不得与边帅狎昵,本使见东宫近戚韦坚竟与边帅皇甫惟明违敕密处景龙观,顿觉可疑!不想东宫来观后,又与彼二人共去道士室中盘桓甚久,才车辇回宫。故即将韦坚、皇甫惟明、妖道齐齐拿归西台按鞫!”说到这里,风俗使而对挟跪在地的道长厉声喝问道:“你这妖道!还不从实招来!”
“快招!”
“冤~~枉!~~”
“哼!你这妖道,分明助韦坚、皇甫惟明以密室,供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谋立太子!汝!速速招来!”
“招!”
“青天大人呀!……我……我……”他一听风俗使所说的罪名,终于清醒过来,欲作急辩。他想说,东宫正月望日朝玄元皇帝神座,乃系常仪,并非他为助韦、皇甫二人交构使然;他想辩解:韦坚、皇甫惟明二人来到观中,不惟他不知渊缘,就连这二人,也不知渊源!……原来两人今日一早,分别被自称为景龙观的青年道士登府相请,说“观中有奇梅,为道长多年苦心密植的珍品,一树之上,花开七色!道长特请大人去观中后院密苑赏咏之!”二人自然兴致勃勃来到观中。但他何曾有甚奇梅,又何曾遣人请过谁来?……三人正在观中称奇,东宫来到了。韦、皇甫二人和老道,自然要陪着储君,去大殿朝拜玄元皇帝神座。又何曾指斥今上乘舆、谋立太子呀……他想说明这一切,但却理不出头绪,反而弄乱了心绪!
“哼!你愿招了么?”
“招!”
座上那鹰目御史,向他逼视着,冷冷催问;身边的人役,却如凶神恶煞一般,在他头上怒喝!……“这,不是已经定……定罪了么?!天哪!……”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绝望,把他推向了恐怖的深渊。
“禀大人!无招!”
“催——刑!——”
“喳!”两名刑吏,手执催箍铜锤,走向了挟棍两端的铁箍处,一个刑吏扬起铜锤,向铁箍砸去,但另一个刑吏却猛地将自己手中铜锤迎过去,两锤相触,“砰”地一声响,只见火星四迸!
“你?”那个刑吏对阻挡他的同行恼怒地喝问。
“嗯?你!”吉温也对那刑吏,投去锐利的目光。
“禀大人!”那刑吏却一手提锤,一手摘去老道士的道冠,扔在案下,然后抓起那头顶的苍然独髻,往后一拉,让那道士的脸向着吉温。
“哼!”吉温一见,气得一跺足,“竟死啦!”
“罪有应得!”那簿书吏却朝吉温禀道,“他招承的这些事,已该剐皮剜心啦!”
“既已招承,”吉温冷笑一声,又朝堂中扔下两只法签带,“韦坚、皇甫惟明!”
幾东风俗使亲捧法签,领着一队人役出了大堂。吉温朝刑吏令道:“大刑伺候!”
“大——刑——伺——候!”
韦坚和皇甫惟明被畿东风俗使的快捕手从景龙观中的后门押出,推入皂葛密罩的车座中,头蒙法布、颈锁铁链时,两人这才明白过来:“中了奸相的机阱了……”
但两人同时也明白了:为时已晚了!
“明知虎伺身旁,何不如贺知章等,早谋一全尸之地啊!……坚今一死,自是命定;只虑阖府两百眷属,皆无生理……”
“韦尚书或可与家人诀别;我皇甫氏眷属远在陇右,何从与妻儿诀别呵!……”
两人正在万般凄楚之时,突然被人喝起。任人推着、掀着、跌着、绊着……
“去了法布!”
吉温的声音,传进二人的耳里。接着,两人眼前一亮,法布已被摘去。然而,面对大堂的景况,二人不寒而栗;作为文官的韦坚,更唬得倒退数步,袍角颤摇起来……
一个大铁鼎,下架柴薪,将鼎内油汤,熬得烟腾油滚;
一座剐桩,残留着血污肉垢,设在大堂堂柱之旁,桩下,一个铁榻上,陈放着令人触目心惊的剐刀、剔刃;
这一旁,刑杖并插架上;
那一边,击顶金瓜横陈……
“啊!……”
二人同时发现,挟棍边,景龙观道长瞪着一双阴森森的眼睛,手臂皮开肉绽地仰面挺卧地上,早已气绝……
“犯官韦坚!”
“……”
“逆贼皇甫惟明!”
“……”
“应点!”抓着二人的刑吏,一声怒喝,同时飞腿打去,将二人打跪在地上。
“哼哼!景龙观妖道,业已招承汝二人,联结李适之、李邕等胡官外任,交构东宫,指斥今上,图谋立东宫、危社稷。汝二人速速招来!”
“招!”
“呵~~”一听这罪名,韦坚两眼一黑,昏倒在大堂之上。
“哼哼!”吉温撇嘴一笑,复对皇甫惟明道,“逆贼!汝还不招承么?”
“快招!”
“……”
“哼!在我吉温案下,不肯开口的犯官逆贼,我尚未见过!来人!”
“喳!”
“让这逆贼吟——细——腰!”
“喳!”
刑吏抓起皇甫惟明颈上铁链,象狠勒马缰似的使力一勒,皇甫惟明咬紧牙关,跌倒堂中。这时,两个人役,抬过一面铁枷,枷在皇甫惟明腰上!另外四名人役,抬过一座铁缀来,缀在皇甫惟明的两足腕上。一切就绪,吉温冷冷喝道:“动刑!”
“喳!”
随着这一声应答,两个健役,扯起枷上两端的铁链,朝前狠狠一拉。
“呵!~~”
皇甫惟明咬破舌尖,仍难熬其痛楚地惨嚎一声。
“止!”
“喳!”
“皇甫惟明!这才一吟呵!尔已受之不了,尔,还是着实招来:今日在那景龙观中,你与东宫、韦坚共谋在何日作乱?东宫叫你调遣陇右河西之军,几时杀入京师?李适之、李邕所拟文告,藏在左相府中何处?尔,招承之后,本御史定奏请圣上,将尔死罪免去!尔,招吧!”
“招!”
“天哪!快……快让我死去!死去!……”皇甫惟明却在难言的痛楚中,向天祷告,“只求苍天速速赐我一死!以免我受刑不过,胡乱承招!……苍天!我若一言有差,不仅成功了奸贼动摇东宫之计;且我满门老小,皆难保全!皇甫惟明啊!唯今之计,且……”他猛地伸出舌头,狠命一咬!舌尖,随着鲜血,掉在了铁枷枷面!
“禀大人!逆贼咬断舌根,死不招承!”刑吏一见,惊慌禀告吉温。
“呵……”吉温一听,鹰目放出绿色凶光,道,“无舌,也可‘吟’!那就,成全他吧!”
“喳!”
牵链人役一声应,便回过头去,将枷上铁链,负在肩上,发一声吼,向前拉去。
“呀!”
“呵!~~”
役者如纤夫上滩,越拉越吃力,那共同使力的号子:“呀”声,也愈到后来,愈变成一种气喘声……
而皇甫惟明的凄厉惨嚎,也越来越细微,但到后来,却又在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叫声中,戛然终止了……而他的身躯,似乎比原来加长;那腰部只有一缕牵连未断;七窍,喷出乌黑的血来。
“禀大人!逆贼已死!”刑吏上前验视一番,回禀吉温。
“这样按鞫,太费时辰!”吉温想了一想,对吏佐们吩咐道,“暂将韦坚收入西台牢中,烦畿东风俗使,即率入将韦坚阖府之人,一并捉拿,解来西台候审!”
畿东风俗使即领命率快捕捉拿韦坚阖府之人去了。堂上刑吏,将韦坚扶着,解往西台牢狱。吉温颇有兴致地望着韦坚的冠、服。耳边,传来月堂议事时,右相的含笑许诺之声:“吉七呀!凭子之才,岂可久居西台副贰?……韦坚等奸谋查实之后,那户部尚书之职,非子莫属: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