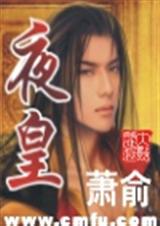唐明皇-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亲赐的高句丽贡参熬成的这盏浓汁,并未使他恢复多少元气。他头上只戴着软绢绣金紫巾,身上也只穿着居家绸面棉袍。那挂在鎏金承衣钩上的华丽耀眼的紫色朝服,以及按制度规定当值朝官应佩带在身,以示唐官威仪的佩刀、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刀子、火石袋等七事,他都不穿戴。耗尽心血才获得这身穿戴的他,不是厌其沉重,而是委实太疲乏了,体力实在有些不支。
也真难为他,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景龙四年——正月元日以来,为了筹备朝贺大陈设和举行朝贺大陈设,在近五十多天的日子里,他每天睡得很少。按理,大陈设后,他应该好好回他醴泉坊的相府舒舒畅畅地休息一段时间,可是不成:朝贺大陈设后,五十五岁的皇帝李显,游乐之兴却愈来愈高。连日来,他在安乐公主新建于定昆池畔的洒油球场上玩得不肯歇手,灯节前一天,他干脆命内侍们秉烛供他击球到午夜之后!而宗楚客也只得拚命支撑着自己那似乎已要散架的身躯,伴君宴游。直到送驾返还大明宫后,他才回府闭目养了会神。但晨鸡初啼,他又得去光范门前待诏了。如不是三天灯节该他当值,他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皇帝身边累昏过去。韦皇后面谕他今岁必须在灯节中当值,是向他肩上压去了一副沉重的担子。虽说当值也仍不能如意地休息,但总算有了个稍事喘息的时间和环境。第一天当值结束,他该对簿消值②,打马回府了吧?不行呵!又是韦皇后,昨日口敕他今日必须伴驾游御乐园,据说安乐公主有奇珍上献,他要应制献诗纪胜!
既是如此,又何必硬要他堂堂大唐宰相来当此三夜之值呢?难道是因为其他几位宰相如唐休璟、韦巨源等人的年事太高,非要他这六十岁刚出头的宰相多劳累点么?其实倒不是这回事。虽说唐休璟已年过八旬,韦巨源也七十出头了,但平日在省中当值的,倒多是这两位老相爷。朝中有那为人刻薄而胆大的官员,就曾称他俩是“值宿宰相”。因为除了当值而外,中书省的一应事情的处置,这二老或沾不上边,或只能看宗楚客的眼色行事。那么,到底又是为了什么,韦皇后偏要命宗楚客在繁忙不堪的新年伊始之际昼夜受累呢?说来,话就长了。但核心要点,却是从去冬筹备新岁朝贺大陈设起,冒出了不少不祥的苗头,使韦皇后、宗楚客等暗自心惊,不得不处处留意,步步小心。
原来按建唐之初的仪典,每岁正月元日,皇帝将于太极殿接受新年朝贺。这一天,太极殿至承天门,喜乐欢奏,华宴大设,满朝文武官员,各国使臣来宾都要云集此处参加大朝贺。其间,按仪度所定,首先由皇太子向皇帝、皇后祝寿;紧接着是王公们向皇帝、皇后祝寿;然后,由中书令奏全国各州贺表;黄门侍郎奏国之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各藩王的贡献;还有太史奏云物,侍中奏礼乐……作为中书令,入冬以来,几乎都在检阅着大朝贺时各省、部拟就的奏章,也就是在这检阅的过程中;他首先发现了不祥之兆,并忧心忡忡地密呈了韦皇后。
原来宗楚客发现,在各省、部奏章中,除黄门侍郎大奏特奏何处神人显圣,何处凤凰来仪,何处祥云奇集等祥瑞之兆外,其余各道奏章,大多语焉不详,或吞吞吐吐地述着旱涝蝗灾灾情!他令供奉们汇集的各州情况,也使他触目惊心,竟有数十州被其邻国如骠国、占卑国、狡马国所掠扰、围困,根本无法与朝廷联系。而户部在谈到山东、河北等道各州时,则奏因其受灾特重,不仅无寸丝粒粟来贡,而且告急求赈文书雪片般飞来,不知如何批复;太宗在世时进贡的各藩属国、邦,现在仅有十分之二、三备薄贡来朝,礼部怕皇帝知晓后降罪下来,因此连贺章也不知如何措辞,特请中书裁夺……这些恼人的征兆,连惯会翻云覆雨的宗楚客也深感棘手,还仗韦皇后、安乐公主协力撑持,才总算把大朝贺敷衍过去了。但矫制的奏捷之章,压不住灾州灾县飞来的告急文书;挡不住忧国忧民的忠贞之士指斥失政的谏疏。万一不慎,其中之一展现于龙目前,那大朝贺时的把戏就会揭穿!真的那样,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这种漏网之鱼,往往就会在这种时候,混进什么贺诗贺表中,来到中书省,如老迈昏愦的唐休璟、韦巨源当值时不予细审,而皇帝又一时兴起要中书呈报佳节时朝野的颂赞之章,那就后悔不及了!当然,这位后来谥号“中宗”的皇帝虽然在发现这种事时,不一定会给他以什么“赐死”、“灭族”的处治,但因此给早已暗中不洽的帝、后间抹上阴影,进而坏了韦皇后的一统大计,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正为此,宗楚客才只好昼夜操劳,拚命支撑了。……
从紫宸殿处,传来了第三通晨钟。
听着余音袅袅的晨钟声,宗楚客暗自叹了一口气。他遣开搀扶他的仆从们,独自步出当值厅堂,下了雕着宝相花形的石阶。一丛怒放的梅花,带着晶莹的露珠闪入他还有些朦胧的视线内,而那淡淡的幽香,却匆匆地窜入他那有些燥热的心脾中,使他顿时感到有股凉气直贯脑顶。至此,他才感到自己的心身脱离了那一直甩不掉的沉重的疲乏,头轻多了,足跟也站得稳多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几分遗憾:看样子,又是一个无雪之冬了!喜欢吟哦的他,多希望在这怒放的梅花枝上,铺着一层洁白的雪花啊!当安乐公主献出奇珍异宝时,他若能在应制诗中以雪壮其景,其韵味当是无穷的!可惜,不会有雪了。去冬没有,翻了春,见了这报春的娇卉儿,就更不会下雪了。多少年了呢?当是在先太后驾崩的五年前吧,京城就似乎总是在无雪中度过冬天。只怕这也是不祥之兆吧?俗话说:“雪兆丰年。”连年来灾异迭起,只怕与无雪有关。那么今年又会如去年似的……或者,这也是天示其警,表明当今皇帝皇祚不永,该韦氏革唐鼎,一统天下……
“当!……当!……当!……当!……”
正当宗楚客的心绪被新的念头弄得再次烦躁时,晨钟四响,使他回到了现实中。他理理腮下稀疏、花白的胡须,定定心神,以低沉而威严的口吻命仆从们:“更衣!”命毕,便转过身来,仍朝当值厅堂而去:还有半个时辰,皇上就要摆驾御乐园了,他须抓紧穿戴,去紫宸殿外率领百官伴驾。
就在宗楚客更换朝服时,外廊上的传事官员朗声通报:“禀大人!光禄少卿杨均大人到!”
一听“杨均”二字,这位平素连皇室宗戚也不太放在眼里的宰相,却忙趿着便靴,迎到外廊上,朝杨均笑着一拱手:“请!少卿大人!”
年纪很轻、风度潇洒的杨均,也忙着含笑答礼,和宗楚客进了厅堂。宗楚客把杨均让在左榻上落座后,正要命仆人伺候,不想杨均连忙一摆手,说:“相爷不必赏茶,杨均即刻还要进宫供奉,此刻前来打扰大人,是为……”说到这里,他以目注视着环立厅中的仆从,宗楚客微拂袍袖,众人立即悄然离去。
“你看这封疏本,杨均这才从袍袖里取出一卷黄纸来,递到宗楚客手中。宗楚客迫不及待地展开疏本,只见抬头处写着:
河北道定州草莽臣郎岌,跪奏吾皇万岁、万万岁……
“郎岌?这是何人?”宗楚客一怔,歪着头询问杨均。
杨均哼了一声:“一个寻死狂生!”
“哦,”宗楚客明白了几分,重新回头去看那疏本,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到底来了……”可是,当他愈看到后面文字,那白皙的脸面愈变得铁青。不及终本,他便把那卷黄纸“叭”地一声掷在榻下,然后阴沉地问杨均:“大人在何处接得此本?狂生现在何处?”
“适才杨均奉皇后懿旨进宫,在光范门外,遇这狂徒拦道求上疏本。眼下已将他带在外廊来了!”说到这里,杨均那原本俊秀的双眸中却漏出一片杀机,“在这样的时候,真该杖杀!”
“是呀,如果这卷黄纸,落入肖至忠辈手中,今天的时辰,就难捱了……”
“哼哼!苍天岂佑狂徒!宰相大人……”
“少卿大人,杖杀太便宜他了,宗楚客摇摇头,站起身来,边踱步,边对杨均说。忽然,他象咏哦时偶得佳句似地兴奋起来,急急地对杨均说:“好啊!安乐今有奇珍献奏两位陛下,我们少时也把这定州士子,变为异物博两位陛下一笑吧!”
“他?一介狂生,能变成什么异物?”
“哼哼!”看着杨均疑惑的神情,宗楚客恶意地冷笑两声说,等会让他在含光殿外的洒油球场见见皇上——也不辜负他一片忠君报国之心!”
“当!……”
这时,从紫宸殿里,传来了五下钟声。
从朱雀大街正中的朱雀门而入,经承天、重元门往禁苑之西而去,过永安渠,便是宫中花团锦簇的风景区——御乐园。
当紫宸殿内五通钟声敲罢不久,中宗李显,皇后韦氏,李显之妹太平公主,就在匆匆赶到的宗楚客伴随下,在一派笙箫鼓乐之中,来到了永安渠畔。
当今皇帝李显,为唐高宗的第七个儿子。眼下虽说年未花甲,但因他在青壮年时代经历了武周翦灭李唐宗室的惊涛骇浪,正是那些担惊受怕的岁月,使他未老先衰。须发全白了,目光也显出垂暮之人的朦胧、迟钝。自神龙元年,即公元七〇五年春,张柬之、姚元之于东都玄武门起兵,斩关而入,逼武则天在长生殿退位,拥戴他二度登极至今,他又作了五载大唐帝国的万乘之尊了。但看上去他却明显地缺乏一国之主应有的威仪,常常会不经意地露出几丝惶骇的神情。只有在玩他最喜好的击球时,他那朦胧迟钝的目光才变得明快起来,身手也显得反常地矫健。今天,为了游乐的方便,他的头上只戴着黄绫软巾,暖和、轻柔的狸毛箭衣外,罩着一件黄绫彩绣夹袍。唯有足下却穿着厚底长筒的亳州绢靴。这,既可使他有些佝偻的身躯变得高大一些,同时,又便于在他击球之兴发作时,随时可以翻身上马,驰入球场,畅挥击杖。
与中宗比肩而行,差点高出中宗半个头的韦氏,却有着震慑群臣的皇后威仪。她那精心修饰过的娥眉,虽障在帷帽的薄幔之后,近侍也清晰可见;而她那双闪动的眸子,即使在帷幔之后,也时时向外界射出一种令人寒颤的冷光。她那旋成微微后仰的高髻,被帷帽罩住了,但斜插于髻中的一支吐珠蔚蓝凤簪,却从帷幔中露出,和绚丽的晨曦争艳斗彩。她内穿酱色宋州“轻容”薄纱制成的窄袖襦衫,外套桃色棉褂。衣领上镶着酱色织锦花边,衣衫上则精绣着八瓣菱形宝相花。由肘延向袖边,是用豆绿色丝线绣成的双圈连续花纹。那鹅黄色长裙高束胸前,裙裾宽舒,长垂曳地,使她原本高挑颀长的身躯,更显得仪态万千。
紧随在皇后身边的太平公主,其身躯可与嫂嫂匹敌。她的头上,戴着惨紫帷帽(唐人呼淡色为惨色),身上用一袭惨紫油缎斗篷裹得上细下圆。她的这身打扮,令侍从们隐隐记起当年则天圣后东都赏雪的妆束。而她那深藏不露、外似随和的风韵,却更使一般老臣觉得这则天圣后最宠爱的公主和则天本人一样令人敬畏。
当銮舆前队仪仗刚到渠畔前的含春桥头时,便听见一个拖曳着阴嗓尾音的声音从桥的对面奏道:“安乐公主桥前接驾献珍呀……”
随着这声奏报,前队仪仗迅速分立桥头两侧,中宗、韦皇后、太平公主则由四妃、九嫔、九婕妤、九美人、九才人、二十七宝林等六宫宫嫔拥着,来到含春桥头。但桥对面的石阶草坪上,却不见安乐公主及其献珍仪仗,只有刚才那传禀太监,垂手跪接。
韦皇后微挑蛾眉,问那太监:“公主在何处接驾呀?”
那太监娇媚地朝皇后一笑,却并不回答什么,只是举起手中拂尘,向身后的梅林扬了三扬。应着这拂尘三扬,在那枝干盘旋、香蕊繁绽的梅林深处,闪出灿若星辰般百十盏灯来。也就在此同时,随驾乐班突然中止了吹奏,肃静的仪仗队里,却爆发出一片惊叹之声。中宗、皇后、太平公主,这才看见在灯光环照中,显出了奏请献珍的安乐公主。
她的乌黑油亮的长发,在头上旋成了双屈高髻,髻上无半点首饰,这就衬得她粉面如玉,眸似流星。她将双手笼于袖内,平举胸前,而身子却端坐在一匹毛色如淡淡的云烟般的白龙驹上。她那上身穿着圆领袒胸的乳白色襦衫,长裙裙裾垂至金镫环下。此刻,善揣人意的奏事太监见两位陛下和太平公主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安乐公主的裙裾上了,便急忙走到白龙驹前,缓缓地移动着缰绳,那白龙驹便随着太监的移动,载着安乐公主,或中,或侧,或左,或右,向中宗、韦皇后、太平公主等展示着。那裙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