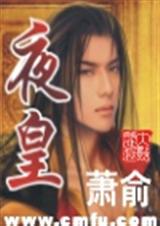唐明皇-第7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殿而去。法台上下众僧,早就奉命为专门抚慰蝗灾而来的钦差大人大做法事,今见钦差竟不驻步台前,一个个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莫明其妙。
就在钦差一行刚进入相国寺不久,一伙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手执粘竿、网具、弩箭、牛角钢叉的人,却从相国寺大门前悄悄退开,在香案相接的街上走着。在快上汴河街中拱桥时,道绝行人,他们中一个眉间较宽、骨骼特别粗大的年轻人,向众人抛去一个眼色,朝河畔上一指:“去那里看看,或许会碰上一两只呢!”
众人会意地点点头,跟着他顺着桥侧护梯,转入河畔斜坡。斜坡上,一丛丛蝗虫不吃的臭笆茅,摇着缨枪似的茅花,遮护着汴河长堤。
这伙人朝臭芭茅茂密处钻去,然后有的张开了网,有的竖起粘竿,有的架起了驽箭,似乎在屏息等待猎物的到来。实则,每个人都脸色紫胀,太阳穴“砰砰”乱跳,那执竿拿箭的手,冰凉、发颤,都沁出了一手心窝的冷汗。
“看清楚了吧?那狗钦差了?”领头的骨骼特大的年轻人,见众人都已蹲好,便低声问着。众人点着头,回答了他,他却还不放心似的,又稍稍放大声音说,“站在倪大人身边那个,朝寺门匾额上看了很久的红衣官儿,就是新来的狗钦差!”
“二十八哥,这还用你叮咛么?”他身边一个尖脸猎户恨恨地说,“他化了灰我也认得清了!那眉毛象两把剑,眼睛贼亮、阔嘴厚唇的家厮!”
“中,我好眼尖的兄弟!”那被唤为二十八哥的猎户头儿,听尖脸人一番描述,显得很放心了,他夸赞了尖脸一句,然后用手招招众人,又用眼朝头上不远处的街中拱桥示意,“等那狗钦差走到桥中,我就向他连发弩箭,你等众人则在桥两面点起炮仗,掷飞叉、尖镖,使那厮难辨皂白,我们便从茅丛中顺堤往南壁的尉氏门、保康门逃走!众人听明白了没有?”
“二十八哥放心!”
“今天要叫皇帝老倌的奴才,有来无回!”
众人咬牙切齿地回答着二十八哥。二十八哥充血的双眼却泪盈盈地,跪在茅丛遮蔽的斜坡上,望天祈祷:“苍天在上!今朝廷不仁,屡派花鸟使前来汴州,催逼我等缴纳异禽!逼得我汴州猎户,家破人亡,难以生存!今我众猎户,齐聚汴河街中桥下,诛杀狗钦差,以泄我等之愤!望苍天护佑,助我等一臂之力……”祷毕,二十八哥又率着众人,望天朝地,拜了三拜。然后,一一朝街中桥两侧散去。
绕刺使衙署前街去相国寺朝拜,再由汴河街中桥上返回衙署,是本地的惯例。钦差在相国寺各殿进香完毕,便于寺外上马,仍由倪若水为前导,往汴河街中桥上而去。曾经繁华异常的汴河两岸,如今少见行人;只有残香余烛,出现在道旁地上。钦差脸色阴沉、目光严峻地勒缰缓行,心事重重地望着凄凉惨然的汴河两岸。
执事仪仗,上了桥头。声声道锣,使寂静荒凉的汴河两岸显得阴森、窒息。
前卫紧随仪仗,上了桥头。疲乏的卫士们,似乎已擎不起戈矛,他们任马儿缓蹄徐行,冷漠的目光散乱地注视着四方。
倪着水在卫队后面,也上了桥头;他关注地轻轻勒了一下坐骑,让在道旁,待钦差的坐骑迈上街中桥后,才重新催马走到钦差马前,缓缓前导。
后卫的钦差随从、汴州州佐们,继这二马之后,上了街中桥。
就在这时,钦差马旁魁伟的佩刀侍从那原本凶狠的眼神,突然露出惕戒的神情,他猛地拔出佩刀,朝桥的两边望去:无风拂拨的茅丛,为什么有几处在摇晃?
他正要向前后卫的折冲将官提醒一句,谁知还未等他发出声来,从南面的芭茅中突然飞出一串弩箭来!那首尾相衔的锐器,闪电般直往钦差的头、胸处穿去!
“呵!”近侍大喝一声,跃身而起,旋动手中钢刀,遮挡弩箭:但是,晚了一步!已有两支弩箭,直扑钦差的咽喉!
“大人下马!”那青袍卤簿,早一纵身冲向钦差的马前,抢过马缰,按下马项,朝钦差急呼。
就在马低项失蹄,摔下钦差之际,那两支弩箭空飞而过,坠于桥中,倪若水早已惊得滚下马来,对愣于桥上的武土们大声狂呼:“捉拿刺客!”
“捉拿刺客!”
前后卫队中百名武士这才回过神来,发声狂喊,横枪跃马,扑向桥身两侧的斜坡,朝茅丛里搜索着。与此同时,桥身两侧,响起了无数炮仗,霎那间,在呛人的硫磺烟雾中,飞叉,短镖象雨点般朝桥上泻来!仪仗和州佐们乱成一团,胡乱朝桥两头狂奔逃命。
“当!当!当!”
下得马来的钦差,却从一名侍从腰间拔出佩剑,扫荡着飞叉、短镖,并朝护卫在他身边的使旋刀的武土命道:“毛仲!速去率众捉拿!”
“陛下!……”
“哈哈哈哈!”以钦差名义察视河南等道的皇帝,此时却笑着,催促王毛仲,“一小股刁民作逆罢了!速去!”
“倪大人!”这时,扮作卤簿的姚崇,也忙对倪若水下令,“速速关闭城门,把守出城要道,务将逆贼生擒严审!”
倪若水急应一声,飞身上了坐骑,前往衙署传令去了。
城内的百姓,远远听见街中桥前杀声震天,吓得纷纷弃了香案,关了铺门,躲回房内。使原本变得萧索不堪的汴州,更如死城一座。不久,无数队人马从汴州军营狂驰而出,奔向各城门及迩关要口。死城上空,回荡起一片马蹄声。
王毛仲飞身上了坐骑,领着护驾武士,潮水般涌下了街中桥。
“官军住手!”
突然,就在王毛仲所率护驾武士和汴州官兵漫布汴河两岸,向街中桥围拢时,离桥身最近的一丛芭茅间,站起一个人来,他挥着手中弩弓,对桥上喊道:“要斩要剐,有我二十八子在!”
王毛仲和众官军见了,先是一怔,接着便呐喊着,向二十八子逼去;无数的刀、枪、剑、钺,举向了他的头,对准了他的胸……
“住手!”
立在桥前的李隆基,朝桥下喝了一声,然后将手中之剑顺手递到身边的姚崇手里,这才铁青着脸,朝桥下静静望着他的兵将们说道,“带回刺使衙署!”
“呵!”王毛仲暴怒地狂吼一声,一转手中的旋刀,照着睥睨他的二十八子的膝部,就是一击!被那刀背猛击一下的二十八子,一下子扑倒在坡边,王毛仲将自己腰上的铁箍板带解下来,躬下身子,把二十八子的双臂反翦,恶狠狠地绑起来。
随驾御医给皇帝用药酒擦了背脊和项部,又在寝房四周点好安神香,便悄悄地出了房门。在通道上,他被王毛仲拦住,低声问:“大家伤得很重吧?”
“将军放心,”御医满脸堆笑,拼命掩饰着内心深处对这护驾凶神的无名恐惧,仍不无怯懦地回答王毛仲,“只是坠马时,擦伤了一点皮肤,圣体安康哩。”
王毛仲放心地垂了垂眼帘,松开手,放那御医去了。他重新拔刀在手,向布在皇帝住房四周的卫士们缓缓走去。时近黄昏,衙署内灯稀烛疏,更需他加倍留神。步下通道石阶时,他下意识地用大拇指和食指在李守德遗留给他的旋刀刀刃上试了试锋芒:不错,十分锋利!明早,他要亲手砍下二十八子那伙逆贼的头来,象劈瓜那样!
依在榻上,那药酒烧得背脊和颈项一阵阵发木;四周是这么静,静得真象是在深山旷野中一样。
然而,恍惚间,李隆基却分明觉得自己被宋王成器,岐王隆范,薛王隆业簇拥着,在宫娥们的踏歌声中,进了新修的兴庆官金明门,在龙池前的龙堂上坐了下来。宋王正喜滋滋地指着龙池对他说:“那便是汴州花鸟使新近携回的中原奇禽:鵁鶄、鸿鹜。”
随着宋王的奏禀声,他朝龙池望去。只见罩子池上的用竹丝和纲绳织成的池向下面,一种大脚、高冠、青胫的五色锦羽的鸟儿和一种比鸭略小,尾羽似船舵,纹彩亦鲜艳多姿的鸟儿,正在水面嬉游。
“陛下细审之,”又是大哥那兴致盎然的声音在继续奏禀,“那大脚高冠的鸟儿,就是《尔雅》中所说的鵁鶄。你看它那双旋动的圆睛,靠得那么近,好象要交叉传递似的!江东人几乎户户养它,据说它能禳厌火灾哩!那比鸭儿略小的,就是鸿鹜。世传凡有这种鸟儿栖止的地方,就气朗风清,没有邪毒之气……”
……
“呵……呵……!”
突然,一阵娇媚的号子声,将宋王的奏禀声掩尽了,宋王和龙池中的奇珍异禽也悄然逝去,李隆基恍惚觉得自己正立在白日经过的汴河街中桥上,看着汴河风光。映入他眼中的并不是荒凉惨景,而是旌旗招展,鲜花遍地,岸上,上万锦花妆饰的少女,正拉着彩球浮坠的纤索,缓缓地喊着口号,沿岸前行;汴河中,一座高达四层的龙舟,和一座稍小于龙舟的翔螭舟,随着纤索,正徐徐向街中桥驶来,望后看,一艘接一艘的高约三层的大舟,上造金碧辉煌的宫殿,悬着“漾彩”、“朱鸟”等名号的大船,也泛波而采,似乎永远也望不到尽头。
那龙舟和翔螭舟越来越近了,使李隆基惊异不已的是:虽说他和此二舟距离尚远,但他却分明看见那并肩而行的双舟舷窗前,一边坐着隋炀帝,一边坐着皇后萧氏。并且分明听见隋炀帝醉意模糊地对萧皇后说:“卿以为朕不知道天下不少百姓在骂依、图依么?朕才不管他呢!活一天,就得尽兴醉游一天!……”李隆基听到这里一怔,接着,又听见隋炀帝对萧皇后叹息着说:“好头颅,不知该谁来斩它!”
“呵!”李隆基听到此处,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摸摸自己的脑袋。
“好头颅,不知该谁来斩它!”
……
“昏君!你害苦了天下百姓!今天也吃天下百姓一刀!”
就在隋炀帝那句使他惊骇万般的话一声大于一声地回荡在他的耳畔时,突然一声大喝,如炸雷般响起,他分明看见,那汴州猎户二十八子,变得象中岳般巍峨高大,他那遮去半个天日的脸上,目光如电,一手提着血淋淋的隋炀帝的头颅,一手仗着寒光夺目的长剑,飞身跃向街中桥,向他逼来!他惊得大叫一声……
“大家!大家!”
“请醒来!大家!”
在一片焦急的呼喊声中,他醒过来了,却见王毛仲和几个近侍正围在榻前。
李隆基神志异常清楚。刚才恍惚间看见、听见的一切,此刻都那么清晰地一一浮现在眼前、耳中。他勾着头,借夜色来掩住满脸羞赧之色,低声问道:“朕刚才怎么啦?”
“奴婢们听见大家睡得不安稳,”一个近侍额头上挂着豆大的汗珠,颤声答道,“奴婢们就急请毛仲将军进室来了。”
“哦。”他放心了。心想,“没有呼出什么声音来……”
“大家此时安否?”王毛仲却发急地奏问。
李隆基一时不去回答王毛仲,却屏息静气地思虑着什么,好一会,才抬起头来问王毛仲:“什么时辰了?”
王毛仲身后的一个近侍忙回答他,“亥时刚过。”
“召倪若水速来见朕”
“大家……”王毛仲担忧地要劝谏他。
“去吧!朕有要事相询。”
“领……敕。”
厢房内增添了灯烛,显得十分明亮。倪若水应敕走到厢房门前,便一头跪下,伏身奏道:“臣、汴州刺使倪若水,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隆基早已由近侍伺候着,从榻上起来,戴好白纱帽,穿好黄绫夹袍,腰间不箍玉带,却扎着银白色的、三指来宽的衬底半硬绸带:这样可以使他那微有不适的背、项舒服些。他听见倪若水的朝奏声,便从厢房内侧踱到门坎前,沉着脸,细细打量这位四十来岁的汴州长官。眼光在那瘦削的双肩处停了一会,这才移开目光,却不叫倪若水平身,唤道:“倪卿!”
“臣在。”
“谋刺逆贼,可审理明白?”
“启奏陛下,已经审理明白。”
“奏来。”
“领诏!”倪若水抬起上身,目光里掺和着相当复杂的情感,恳切地望着门坎内那年轻的君王,说,“经臣审讯,二十八子等,尽系臣治下猎户……”
“哼!”
“彼等本是良民百姓。”倪若水象没有听见皇帝那一声不满的鼻响似的,说下去,“确因穷途末路,才逼出今日之逆举……”
“此乃何意?”李隆基倏地倒悬剑眉,大怒难遏地诘问倪若水。
“陛下!”倪若水眼里泪光闪闪,嘴角纹路向下拉去,反映出他内心的极度痛苦。他高揖两手,辞意刚直地回奏说,“今蝗灾方急,而陛下却频遣花鸟使,前来本州,督捕禽鸟,以供新建离宫龙池!水陆传送,食以梁肉,道路观者,莫不以陛下贱人而贵鸟!而被督猎户,其怨毒尤深!今,陛下方总万机,以中兴之志昭告天下,正当以凤凰为凡鸟,麒麟为凡兽,况鵁鶄、鸿鹜,曷足贵乎!以游乐害民,昔炀帝丧国取死之道!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