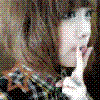心机乱-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姐怎么了?”门外两名侍卫听见这声叫喊,便跟了进来,我听得出,说话的人还是那两个昨夜站岗的人。
两个妇人来不及回答他们,先冲过来,在我床上好一阵折腾,灰尘如同瓢泼大雨一般落了下来,我死死捂住口鼻,好不容易才强忍住不咳嗽。
“小姐不见了!”一个妇人首先叫了起来,“你们两个赶快去禀告将军!”
“慢着!”
又是廖婶的声音。我伏在床下,只见一双三寸金莲缓缓地绕着床转了一圈,不由得有些担心:难道她竟发现了我的所在么?
“这儿有个字条。”她又说。我顿时松了口气。
房间里暂时没有人说话,想来她正在读那张字条。
再开口时,廖婶的声音已经变得怒气冲冲了:
“你们两个夜里守卫,难道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紧接着,一团绳子被扔在地上,廖婶大声骂道:“小姐逃了,你们难道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
那两名侍卫也慌了,但他们到底是行伍出身的人,当下就仔仔细细地将半夜听到窗户开阖的声音、自己掉以轻心的事情说了。
廖婶叹了口气,说:“走吧,咱们一同去见将军。我看得马上去追人。”
又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四人从房里走了出去。过不了一会儿,楼下众马嘶鸣,车行辘辘,竟是去追公主去了。
我见那廖婶也被我骗过,长出了一口气,这才从床下爬了出来,掸掉头上和身上的灰尘,照了照镜子,将身上的衣服收拾妥当,悄悄溜出旅舍。慢慢走了半天,方才买到一匹瘦马。一路上所遇到的人尽是朝着出城的方向走,见我这个满身尘土的年轻人竟要进城,都出言阻挡。
“黄天羲要来!”一个挎着青布包袱,领着儿子儿媳以及五六个孙儿孙女的老人含含糊糊地对我说:“小官人不晓事,千万不要进城了,赶快随着我们,逃远些是正经!”
我苦笑,将身边的一些碎银子给了他们一家,让他们好好赶路。
“官人要进城?”第二次问路,一个妇人又对我说,“不知官人是要寻亲还是要救人?如今城里十室九空,官人的亲友多半都逃了出去,官人还是自己躲开吧。听说北朝那个人明日就要到虎偾口啦!”
我谢过她,依然朝着京城走。那种明知是死地仍旧执拗地想要归去的心情,连我自己也不能理解。自己追忆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对于南齐竟然有了如许深的感情。也许是在以往我呼唤做父皇母后的人将天下最贵重的珍宝堆在我面前,却似乎还不知道应该怎样疼爱我的时候;也许是以往大哥偷跑出御书房陪我去抓蛐蛐的时候;也许是在皇叔不顾自己的安危,在城破之际心心念念地要将我送出宫的时候……他们对我,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怀疑,我在他们的怀抱中,安乐幸福,从未有过在西赵宫中所受的欺侮、穷困和窘迫、恐惧。在南齐的那个皇宫中一点一点的长大,我竟然已经那么自然地将他们当成了我最近的亲人。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弟弟和母亲还在西赵那帮人的手中,我想我或许真的会待在南齐,真的将自己变成那个长公主齐青枝。
行到正午时分,遇上了一群商旅,他们也是要到京城去,只不过是去城郊接自己的家眷。我不敢与他们搭话,便慢慢跟在他们身后,随着他们向益州行去。一路上他们打尖,我就打尖,他们起行,我就也起行,好在一路上人口众多,他们并不在意我跟着他们。
一路上,路途渐渐地变得越来越熟悉,人也越来越多,我认出这正是京城附近的官道,心中顿时放心。
晚上,这群商旅在路边的空屋中歇宿,我也在附近找了个地方,却不敢睡着,只是吃了些干粮,坐了一夜,第二日清晨,起身又向前行去。那群商旅反而落在我身后,迤逦来到城郊的山上。此地已经靠近虎偾口,并能居高临下远远望见益州城门了。
离京城越近,我开始有些担心能不能混进城去。最好是先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可是不表露身份,又该如何进城呢。正在踌躇间,忽然听见前面的商旅们一阵惊呼,抬头一看,他们正在向不远处指指点点。我顺着他们所指的方向望过去,只见对面远处的平原上出现了一支精骑兵,缓缓地朝益州城这边行来。跟在那先行兵之后的,竟是绵绵不绝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遍体黑甲,黑压压的如同一片乌云,旌旗森森,遮天蔽日。那淡青色的旌旗上,赫然绣着一个黑色的“辽”字。辽东乃是黄天羲的封地,这支军队自然就是黄天羲的人马了。
正午的骄阳之下,只见那些骑兵呈一字型一齐摆开,虽然散漫,却带着不可一世的傲气,令人凛然生畏。那队人马渐行渐进,城外的人都纷纷逃进附近的密林之中,浑身颤抖,只怕他们会就此开始杀戮。然而队伍一直行到益州城门前都没有异动,城上的守兵张弓搭箭,严阵以待。队伍直到临到城门下,这才向两边一分,一人一马,缓缓从队伍中越众而出。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人的身上。
离得太远,我看不清那人的面目,只能勉强看得见此人未穿铠甲,只穿了一件白色的云纹锦袍,脚下踏着一双黑色的朝靴,靴子尖上镶着明珠,在阳光下莹润闪耀。他身下骑着一匹白马,那马儿的四只蹄子上金光灿灿,竟然是纯金打造,正好应着那人手中马鞭的颜色。那马鞭粗重有力,似乎带着片片鳞甲,就如同一条金龙一般。此时阳光耀眼,照在那人身上,说不出的尊荣华贵。
第十一回 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
这种时候,即使不问也知道,那阵前的人,就是北朝的辽东王了。
他身上除了那柄马鞭,连刀都没有一把,身边的士兵又都离他有七八丈远,设若城上的守兵同时射箭,说不定能将他射杀在城楼下。可是他身上自然而然地有一种凶狠霸道的王者之气,让人不寒而栗,城楼上密密层层的守兵,箭弩拔张,却没有人敢射出一箭。
正在这时,城门忽然洞开,城楼上的守卫也全部收了弓箭。
皇叔一步一步都走了出来。
他上半身袒露,将双手以麻绳绑缚在背后,脖子上挂着南齐的兵符和金印,神态低微,那样的小心翼翼,简直是一步一叩首。
黄天羲就在马背上冷冷地坐着,毫无表示。直到摄政王快走到他面前了,才有一个将士将他脖子上的兵符和将印取了去,检视妥当,递了上去。
我站在城郊的山坡上,远远望见黄天羲接了金印,在手中玩弄片刻,随手往身后一抛,冷冷地对皇叔说了句什么,便扬鞭策马,进城而来。他身后的骑兵随之跟了上去。尘土飞扬中,只有皇叔还茕茕孑立,站在马匹扬起的沙土中,仿佛被那片沙尘淹没。过了许久,他才迈步走进城里,脚步迟缓,就好像负了千斤的重担一样。
我心中没来由的一阵疼痛,同时却也松了一口气:我就怕黄天羲会忽然发难,将皇叔斩杀在马前。
一直等着皇叔进了城,我才远远地跟着他,朝城门走过去。
城门没有守军。
一听见黄天羲在益州,别人逃都来不及了,谁还敢进城去。
我一步一步地挨进了城门,眼前尽是一片凄凉。
只见不少民舍与商铺都已经起火,浓烟滚滚,盘旋上升。呛人的烟雾中夹杂着北朝兵士押送俘虏和平民的喝骂声以及被绑缚着的人们呼儿唤女的惨叫声,还有几个小孩想来是与父母走失了,抱着家门前的廊柱,不肯被北朝的官兵抓走,撕心裂肺地哭泣。
当年的西赵国,也是这样么?鸡飞狗跳,断壁残垣,满目疮痍。
当年的南齐,也是这般对待西赵的子民吗?
不!一定不是。皇叔是个儒雅沉稳的人,不会做这等事。
我向前走了几步,忽然看见皇叔呆呆地立在长街中央,看着自己的子民不断地被杀、被捆绑带走。尖叫声、惨呼声,充斥着我的耳畔,也必定让皇叔内疚万分。他忽然踉踉跄跄地跪倒在地上,放声大哭。
我呆若木鸡地看着,竟没有留意到三个北朝士兵已经走到我背后,一把将我扭住,喝道:“跟我们走!”
长刀架在我脖颈上,划破了皮肤,丝丝刺痛。不远处,有个南齐的兵士已经被砍死,鲜血从伤口处汩汩流出。益州往日繁华昌盛的街市,都变做尸体堆积之处。远处皇叔的身影还匍匐在地上。我抑制不住悲愤,奋力挣脱他们的扭绑,拔出腰间的匕首,高声叫道:“退开!火速去禀告你们的王爷,南齐长公主齐青枝求见!你们再敢有任何不敬的举动,我立刻自刎于此!”
或许是这名字和气势震住了他们,他们竟立刻放开了我,其中一人还讷讷地向城楼上一指。
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不远处的城楼上,在士兵的簇拥中站着三人,当中一个人白衫玉带,正是昨日队伍中那个领头的人,黄天羲。城楼附近,旌旗摇曳,青烟腾空而起,似乎已经开始焚烧附近的房舍。我心里难过,怒火中烧,也不顾那些兵士的阻拦,径自向城楼上冲去。刚刚上了一半楼梯,已经有兵士抢先一步将枪横在我胸前,喝道:“大胆!”
一个清朗而低沉的声音缓缓说:“放开,让他上来。”
那些兵士听见这人的命令,才让我上城楼。刚走一两步只听背后刷的一声,有人亮出长刀,抵在我背后。
事已至此,我反而镇静了不少,整了整衣服,走上楼去。
只见城楼上,众多军士簇拥着三个人,最中间的一人正是黄天羲。他背对着我,居高临下地观望着一片狼藉的益州,一只手背在腰后,另一只手轻轻地摇晃着一把泥金山水扇。
他身旁还有两人,都只有二十出头的年纪。两人的长相颇有相似之处,一望而知是血缘至亲。其中一个稍微年长些,穿了一件黑色的貂裘,上面绣了龙虎云纹,这等装饰似乎是北朝最高一等的王爷才可以用的服色。这人位份虽然高,年纪却很轻,又很沉稳,脸上隐隐含着一丝笑意,眉清目秀,眼神柔和,眉毛轻轻地斜飞起来,嘴角似乎永远向上扬着,那笑容尊贵而宁静,令人见之忘俗。另一个人着戎装,一身铠甲,头发上束着一个金冠,皮肤微黑,眉毛斜飞入鬓,双眼炯炯有神,一脸按捺不住的虎虎生气,趾高气扬,扬起了头看着我,表情中微微显出诧异的神情。
“这就是辽东王。”
身旁的兵士指着中间那个人,大声对我说。
我望着那个背对着我的影子,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天上开始飘起了雪花,风声四起。朔风中,站在城楼之上,几乎分辨不出方向。仿佛你的视线所及之处都是密密层层的冰雪,它们被北风席卷着向你裹席而来,使你无法逃避。
即使憋紧了呼吸,那种冰冷凛冽的刺痛仍旧直抵胸膛内的某处,停留不散。
我在这一片寒冷中颤抖着开口说:“民女齐青枝冒昧前来参见辽东王殿下,殿下万安。”
声音被风吹散了,不知道他那里听起来是不是很微弱。我言语上说得客气,却并没有怎么行礼。
他终于转过头来。
我猛然看见他的脸,差点惊叫出声来,还好反应得快,生生地将这声叫喊压在喉头。
北风之中,阴沉低暗的天光之下,只见面前的那人右脸颊上从眼角到嘴角赫然有条极长极深的伤疤,伤口两边的肉翻了开来,在那道脸上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旧伤口。
尽管如此,他依然是我此生见过的最俊美威严的男子。他的面色苍白,白得仿佛长久没有见过阳光,几乎连嘴唇都只有淡淡的血色。脸颊瘦削,清癯得仿佛久病方愈一般。那张脸上,眉毛如同刀锋一样,既黑且长,配上那如同烟雾一样变幻莫测的眼神,显得分外地摄人心魄。那双眼睛竟是纯黑色,不带一点褐色,在那道眉毛的映衬下,严厉而轻柔。如此的长相,本来是有些过份清秀了,但是他神情中带有中阴郁而痛苦的神色,眉目间天生有种不卑不亢气宇轩昂的度量,任谁也不敢小看。就连那道伤疤,似乎也替他添了种英气勃勃的神态。
“公主为何作如是打扮?”他冷冷地说,“来人哪,把徐将军押上来。”
第十二回 身心苦役君知否
辽东王话音刚落,有军士将一个青年将军押上城楼来。这人浑身都是伤,却仍旧倔强地将头高高昂起。一见他的脸,我忍不住惊叫了一声,想要走上前去,却又不敢。
徐彦,那是徐彦。
我终于又见到了他。
整年思念,万万没有想到是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他。
他清瘦了,脸庞晒得黝黑。那张曾经饱满清秀的脸上满是尘土和血渍,往日江南阳光下那个温雅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当时的轻裘肥马,变作了厚重的铠甲。
只有他的眼光还是一样的。刚一看到我的时候,他怒目而视的神态立刻变作了惊讶,再由惊讶,生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