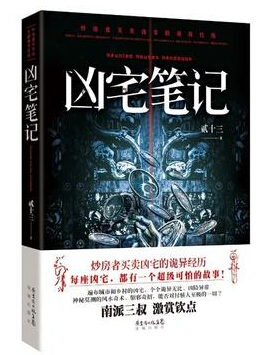情爱笔记-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位绅士和一只蹼足目的鸟类,两个女人,两个或者三个男人,以及可以想象出来的种种结合,只要总数不超过三人一伙,或者最高是四人一伙的限额)在寝室秘密的亲热活动中,可以与荷马、菲迪亚斯、波提切利或者贝多芬赛上几个小时。我知道您没有理解我的话,这没有关系;假如您明白了我的意思,就不会愚蠢到了让自己的勃起和高潮与一个名叫休·埃芬尼先生的钟表同步了(一定是足金、防水表了?)。
这个问题是属于美学的,它先于伦理、哲学、性学、心理学或者政治学,虽然对我来说,此话是多余的:这样的分类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全部重要的内容最终还是美学的。淫秽刊物剥夺了情爱的艺术内容,让它能性的东西压倒了精神和心态,仿佛情欲和快感的主角就是荫茎和荫道,仿佛这两个情爱的辅助品不是为主宰我们灵魂的幻觉充当纯粹的仆役一样,淫秽的东西把Xing爱从人类的其它体验割裂出来。反之,情爱把我们全部的存在和拥有统一起来了。
与此同时,对于您这个淫秽书刊的读者来说,Zuo爱时唯一有价值的就是She精,如同一条公狗、一只公猴或者一匹公马一样,那么我和卢克莱西娅,您就得羡慕我俩了:我们在吃早餐、穿衣裳、听古斯塔夫·马勒的音乐、与朋友们谈话、欣赏白云或者大海时,也是在Zuo爱。
当我说到美学时,您有可能认为——假如淫秽和思想是可以共存的话——我走这条捷径会落入群居性的陷阱您会认为:由于价值观念是普遍共存的,在这个领域里,我很少有自我,更多的是他们,也就是说,部落的一部分。我承认有这样的危险;但是,我日日夜夜不停地与它斗争,经常运用我的自由,顶风破浪,捍卫我独立的人格。
请您弄懂这个道理并加以判断,否则就得读一读这篇小小的特殊美学论文了(我不希望很多人分享这篇文章,因为它是可以变通的,可以粉碎,也可以重塑,如同技术湖熟的陶瓷工匠手中的漂白黏土一样。)。
一切闪光的都是丑陋的。有的城市闪光发亮,比如维也纳。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黎;有闪光发亮的作家,比如翁贝托·埃戈、卡洛斯·宫恩特斯、米兰·昆德拉和约翰·厄普代克;有闪光发亮的画家,比如;安迪·沃霍尔、马塔和塔皮耶斯。尽管这一切都闪光发亮,对于我来说,却是可以放弃不要的。现代所有建筑师无一例外地都是闪光发亮的,为此,建筑已经被排斥在艺术之外,成为广告和公共关系的一个分支,所以应该把建筑师整个排除在外,只用泥瓦匠和木工师傅和外行们的灵感最好。没有闪光发亮的音乐家,虽然他们为之而奋斗终生,几乎闪光发亮的作曲家也有,比如毛里斯·拉威尔和埃立科·萨蒂。电影,如同散打一样让人开心,是反艺术的,不应该列入美学研究,虽然也有几个西方导演和一个日本导演可以例外(今天晚上我打算挑出维斯孔蒂、奥尔索·韦尔斯、布努埃尔、贝尔兰卡和约翰·福特和日本人黑泽明)。
凡是写下“核子化”、“筹划”、“科学化”、“视觉化”、“社会化”,特别是“地球化”的人都是表子养的。凡是当众使用牙签。强迫别人接受这个大煞风景的讨厌场面的人也都是龟儿子(或女儿)。那些抠面包渣、揉成球、放在餐桌上排队的可恶家伙,也是狗娘养的。您不要问我这些丑恶现象的始作俑者为什么都是表子养的;那点知识他们凭着直觉看会了;有些灵感就能掌握;那是天赐的,用不着学习。这句骂人的话,当然也适用于任何企图把英语威士忌非得用西娅牙语拼写出来的男女。这种人应该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猜测他们是在虚度年华。
电影和图书的责任是让我开心。假如我在看电影或者阅读时走了神、打瞌睡或者进入梦乡,那就是它们的失职,那就是坏电影和坏书。突出的例子是:罗伯特·穆西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以及那个名叫奥利费·斯通或者昆廷·塔兰蒂诺的骗子的全部影片。
关于绘画和雕塑,我的艺术评价标准非常简单;凡是我在美术和雕塑方面有可能做到的一切,都是臭狗屎。只有那些我不可能模仿的艺术家。超出我平庸的创造能力之外的作品,才能证夜明他是艺术家。这个标准让我一眼望去就可以确定安迪·沃霍尔和芙里达·卡赫洛那类“艺术家”的全部作品都是垃圾;反之,乔治·格罗茨、奇利达或者巴尔塔斯最肤浅的设计图也都是天才之作。除去这个一般性的规则,图画的责任也是要我兴奋才行(我不喜欢“兴奋”的说法,可即使我再不喜欢,我还要用这个说法,因为它把一种欢快的因素引进了最严肃的范围内,本地人比做:“让我完全做好甜蜜的准备。”)如果说我喜欢这幅画,可是它让我感到冰凉,没有任何戏剧性Zuo爱挑起的想象力,也没有勃起前睾丸上的些许做痒,哪怕它是《蒙娜,丽莎》、《手在胸上的男人)、《格尔尼卡》、或者《夜巡》,那也是没有意思的玩艺儿。因此,如果您若是知道我对戈雅的态度,肯定会大吃一惊:戈雅是又一个神圣的魔鬼,我仅仅喜欢他画的有金扣拌、高跟、缎子鞋面、伴有针织白袜的鞋子;这是他在油画上给那些侯爵夫人们穿的。还有一点也会让您吃惊:雷诺阿的画,我只是怀着慈悲心肠(有时是高兴地)看看他笔下农妇粉红的屁股;她们身体的其它部分,我避而不见,尤其是那戴着廉价首饰的面孔和萤火虫式的眼睛,居然抢在《花花公子》——拿开它!——那些“母兔”前面了。关于库尔贝,我感兴趣的是那些搞同性恋的女人们以及让紧皱眉头的欧仁妮皇后脸红的巨大肥臀。
对我来说,音乐的责任就是把我带入纳粹感觉的眩晕中,让我忘记自己身上最厌烦的部分,公民和行政的部分,消除我的烦恼,让我躲进一个与这个肮脏现实隔绝的飞地里去,用这种方式,让我清醒地去思考那些幻想(通常是情爱的,总是以我妻子为主角),它们让我的生存变得可以忍受。因此,如果音乐到处都是,因为它让我太喜欢了,或者过于喧闹了,那就会让我分心,不能思考,如果音乐要求我注意去听并且果然吸引了我,——我马上举出卡洛斯·卡尔德尔、佩雷斯·布拉多、马勒、所有的民间舞蹈和五分之四的歌剧——,那就是坏音乐,是要从我的书房里驱逐出去的。这个原则当然就让我爱上了瓦格纳,尽管他的曲子里有讨厌的长号和短号;还让我尊敬勋伯格。
我希望这些匆匆举出的例子,我当然没打算让您跟我保持一致(更不愿意如此),只是希望它们向您说明:在我肯定情爱是一种私人游戏(伟大的约翰·赫伊津哈给“游戏”下了最高的词义)时我要讲的意思:在这种私人游戏里,只有自我、幻觉和游戏人参加;游戏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游戏的秘密性质、游戏与公众好奇心之间的隔绝程度;因为从公众好奇心里只能派生出使情爱游戏无效的力量来歪曲和操纵这一游戏的规章。虽然女性腋毛让我反感,但是我尊重那个说服同伴冲洗和热敷腋毛的业余爱好者,他们的目的是用嘴唇和牙齿戏弄腋毛,以便喊叫着高音C而获得心灵的陶醉。但是,如果他购买——比如在前女飞行员比阿特·乌赫斯遍布德国的性商店里——各种形状、体积、气味和颜色的人工腋毛和荫毛(吹嘘最昂贵的是“天生毛”),他绝对不能陶醉,而最多是同情那个被自己幻想的任意性歪曲了的可怜窝。
法律和观众对情爱的认可,会使情爱归市政府管理,会废除了情爱,会使情爱堕落,把情爱变成淫秽,我认为这对于精神和物质都是贫乏的人们来说,情爱是桩悲惨的事情。淫秽是被动行为,讲究集体主义;情爱是个体行为,讲究创造精神,虽然情爱有时是由两个或者三人进行的(我重申:反对增加参与情爱活动的人数,为的是这样的活动不偏离个人欢乐的方向、自主意识的训练以及避免被披着群众集会、体育锻炼和竞技的外衣所玷污。)。“垮掉一代”的诗人阿伦·金斯堡的论据只能让我鬣狗般地哈哈大笑(请看他在接受艾伦·扬格采访时在《所多玛的领事们》中的谈话),因为他在为集体于黑暗的游泳池里性茭辩护时说什么:这种混杂性茭是民主和公平的,因为借助同样的黑暗,可以使得美和丑、胖和瘦、年轻和年老的人有同等的享受快感的机会。这是多么荒谬的理由!简直是特派大员的口气!民主仅仅与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大小有关系,而爱情——欲望和快感——如同宗教一样属于私人天地,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差异,而不是与他人的一致。性是不可能民主的;性是讲究“精英化”和“贵族化”的;来一点专制(经过双方协议)往往是必要的。那位“垮掉一代”的诗人作为情爱模式推荐的在黑乎乎的游泳池里集体性茭,很像牧场上公马和母马的交配,或者很像乱哄哄的鸡圈里公鸡对母鸡不加区别的蹂躏,因此不能与生气勃勃的美丽虚构创造、肉欲想象的创造混淆起来;灵与肉、想象力与性荷尔蒙。品德的高尚与低贱都以平等的资格参与这一创造,对于这位骨子里要确保私有财产的无政府主义加追求享乐的可怜诗人来说,这就是情爱。
按照《花花公子》的方式进行的性(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到这个话题,直到我死了才能罢休,或者这个杂志关门),依我之见,取消了爱情的两个基本因素:冒险和羞耻。咱们来弄个明白。吧。在公共汽车上,那个克服了羞耻和恐惧、解开大衣、在几秒钟之内给一位没有顾忌的接生婆——命运安排她与他面面相对地旅行——展示他勃起荫茎的可怕男人,是个胆大妄为的无耻之徒。他明明知道这个瞬间怪僻的代价可能是一顿毒打,一场私刑拷问,监禁和传播给公众的一场本来要带进坟墓的秘密、现在成为哗然的丑闻,而且有可能宣判他为应该下地狱的疯子和反社会的危险分子,可他还是“我行我素”地干了。他还是冒了险,因为这次小小的显露给他带来的快感是与恐惧和克服羞耻心分不开的。他与身上喷着法国香水、手上戴着劳力士金表(还能是别的手表吗?)的大款之间简直有天壤之别——恰恰等于情爱和淫秽之间的距离!后者坐在环境幽雅的豪华酒吧里,听着布鲁斯舞曲,打开最新一期《花花公子》,它在向他显露,它确信向世人显露荫茎就是在展示沉湎酒色、放弃了偏见、时髦和会享受生活的人。那个可怜的傻瓜!他没有想到自己显露的东西就是自己束缚在陈词滥调、广告、毫无个性时髦的通行证,就是自己放弃自由,就是自己拒绝借助个人的幻想摆脱系列化的隔代奴隶制度。
因此,对您,对这本早已熟悉的杂志及其同类,对一切阅读——甚至翻阅——这种杂志的人们以及用这种下流的半制成品当做食物——我说是消灭情欲——的人们,我谴责你们充当了使性失去神圣、变得庸俗的巨大行动中的先锋,这是当代野蛮的表现。文明掩盖性,使性变得精美,为的是更好地利用性,文明给性包裹上礼仪和法典,其丰富程度为恋爱前、Xing爱中和孕育后代的男女准备厂出乎预料之外的规定。走过了一条漫漫长路之后,情爱游戏的逐渐雕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脊柱,通过不可思议的道路——放荡的社会,宽容的文化——我们又回到了祖先的出发点:Xing爱再度成为一种半公开的体操,无缘无故地在人工制造的刺激下训练,这些刺激物不是潜意识和灵魂制造的,而是市场分析人员的工作结果,这些刺激物愚蠢得如同那种假造的母牛荫道一样,在牛棚里拿着它从公牛鼻子前面走过,刺激公牛She精,然后用这种方法储藏人工受精的精子。
您去购买您喜欢的最新的《花花公子》吧,它已经活活地自杀了;请您在创造那个会She精的男女太监的世界时加上另外一颗小沙砾吧,在那个世界里作为爱情支柱的想象力和幻觉一定会消失的。至于我本人,我马上去找赛伯伊王后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在一次演出中联袂Zuo爱,这个演出的脚本我不想同他人分享,尤其不与您分享。
一只小脚丫儿
堂利戈贝托心里想:亲爱的卢克莱西娅,现在是清晨四点钟。如同几乎每天一样,自从卢克莱西娅搬到圣伊西德罗区奥利瓦尔大街以来,他总是在黎明漆黑潮湿的空气中醒来,为的是举行这个天天重复、不和谐的仪式:从梦中醒来,按照那些养肥了他幻觉的笔记本的要求,创造和再创造妻子。“从我认识你那天起,你就是笔记中的女王和导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