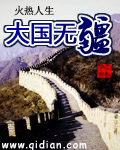大国无兵-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总”、“从六品”或“正七品”而已,那还不是匍匐疆场,困顿终生!
四、八十万人齐解甲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总人数约为88万人(八旗兵22万人,绿营兵66万人)。
英国远征军总人数近2万人(陆军12000多人,海军不足8000人)。
中英军队在中国陆海空间的人数比为44:1。
但中国败了,英国胜了。
我们说“八十万人齐解甲”,没冤枉清军。
2万人打败了88万人,或88万人没有抵挡住2万人的进攻、没有完成保家卫国的职责,不论怎么表述,都是一个严重的国家问题。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谁都知道该花这个“养兵”钱。但“一时”到了,“千日”费了,人民便有权力对军队与国家的存在产生怀疑。因为从本质上讲,是“人民”分出自己的劳动创造养活了“军队”并维持着“国家”。
清代的八旗兵与绿营兵均实行薪给制。月有“饷银”,年有“岁米”,依照职级,多寡不等。百姓种庄稼,还有水旱之灾、绝欠之虞,当兵则旱涝保收,故谓“种铁杆庄稼”。“种铁杆庄稼”的人多,兵饷即多。有清一代,在不发生战争的常规年份,兵饷约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一半。
如清初,全国每年财政支出凡银2739万两,兵饷银为1349万多两,占全国财政支出的49%以上。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全国财政收入4854万两,支出凡银3370万两,兵饷支出银约为1700万两,兵饷占全国财政支出的50%以上。
拿出国家一半的钱养兵,这兵还不能保卫国家,这是个大讽刺、大笑话。
每逢战争,军队还要向国家伸手。
学者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额外支出军费2500万两白银,而英国远征军的累计军费仅900万两白银。花了大钱,仍吃败仗,这再一次印证了清朝军政的腐败。中国人谈鸦片战争,真应了一句俗话:“花钱买教训。”
教训还不在白白花费了金银,战争、流血、失败、赔款,这一切,都雪上加霜地摧残着一个国家的军心与民意。失败是噩梦,失败是瓦解力,失败是传染性病毒,在失败的打击下,最易于产生的共性情绪是自暴自弃,自甘沉沦。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百年期间,中国人凡与外国对阵,几乎每战必败。面对这一连串的失败史,你在理性上几乎无所解释,余下的慨叹或许是:中国人被外国列强打怕了、打服了、打得灵魂出窍了!这时候,如果再阅读中国文人的“武侠小说”或“历史演义”,你会哑然失笑:
在一个尚武精神全民性失落的民族中,最廉价的自我安慰竟然是梦呓般地赞美武侠与歌颂英雄。
如果让思想降落到地面上,让议论针对着战争,我们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的军事弱势便会有一个常识性的把握:
第一,极端化的专制皇权与无人治军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皇权高于一切,皇权又不可能转化为有效的军权,造成“皇权”与“军权”同时丧失。
第二,国虽有兵,兵虽有防,但清朝“国防”既无战略思维,又无战略准备,一旦临战,即无战略运作。这种“战略体系”的缺失,先是隐性的,后是显性的,但不论如何,都是致命性的——这正像一个半身不遂或全身瘫痪的人,既无法保护自己,更无力回击别人。
第三,不知己,不知彼,凭想当然打仗。
第四,兵器极端落后,形不成战斗抗衡。
至于军内腐败,失于演练,将无谋略,兵无斗志,则又在其次之其次,姑且不论。
[注释]
① (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二卷P372。
② 《清史稿·仁宗本纪》,《清史稿·宣宗本纪》。
③ 《清代野史大观》卷一,《宣宗俭德》。
④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狐裘不出风》,《缀补套裤》。
⑤ 《道光实录》。
⑥ 《清朝文献通考》卷33。
⑦ 《清史稿·圣祖纪》。
⑧ 《乾隆实录》卷55。
⑨ 《清史稿·时宪志》,《清史稿·南怀仁传》。
⑩ 《清史稿·郭世勋传》。
第二篇:锦绣江南的“战争补课”
锦绣江南的“战争补课”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几乎是中国老百姓公认的生存环境评估。
“天堂”的富庶,是百姓经营之功,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政治的大背景,还有晋室东渡、宋室南迁。中国的政治中心既然安在苏杭一带,天子脚下,皇恩浩荡,你想不居住在“天堂”也不行啊!
北方一乱,即行南迁。一条大江,阻隔了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相对而言,江南的战祸确实少于北方。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江南便不再太平。
鸦片战争,是围着“江南”打的。最后,在“江南”的六朝繁华古都南京,签下了停战、赔款、割地、通商的伤心条约。
“帝国主义”的兴趣似乎固执在做买卖上,他们对“江南”的侵入,是边缘性、散点性的。鸦片战争后,“江南”还是江南,“天堂”还是天堂,“天堂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和平的风,吹拂城乡……
洪秀全发难,太平天国兴起,“江南”首当其冲。“天京”建在“南京”,“天国”建在“天堂”,洪秀全们很有眼光,把“清妖”的“天下粮仓”占住了,即便不搞什么劳什子“北伐”,饿也能把大清朝的“八旗”男女老少饿死呀!
问题是,“天国”没建成,“天堂”却糟蹋了,“和平”没了,“战争”来了,“天国”的梦幻者,被埋在“天京”的废墟里,“天堂”的百姓,遭逢史无前例的浩劫。
先辈们为躲避中原战乱,一拨又一拨来到江南。没料想,他们的后代,却因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而命断沟壑。有的学者在统计后发现,1851年至1864年的14年中,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死亡人数一亿六千万人!而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至少在一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七千万。给战争中心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所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则达五千四百万人,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五千万人的死亡纪录。①
呜呼!伟大的太平天国的“太平”与“革命”!
洪秀全们给锦绣江南进行了一次血色的战争补课,也让中国进行了一次人口“减肥”。
江山毁弃,百姓蒙难,可是在“意识形态史学”的逻辑判断里,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却成了他们的研究珍存。
其实,铺陈此篇的目的,倒不是进行太平天国批判或洪秀全批判,近二十年来,渐渐走出意识强加的历史研究者已经借助未加淘洗的历史事实,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太平天国主流话语,表明了有力的驳诘。
本书想要提醒的是,关注战争对中华民族的摧残——较之异族入侵,本民族制造的战争灾难似乎更为惨绝人寰!太平天国,仅为一例。
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
跳出神话的虚说,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天兵”、“天将”是在“太平天国”的背景下显现威力的。
回过头来再说太平天国的“天兵”、“天将”,那也是一帮了不起的时势英雄。单是他们创造的战争神话,便在险些颠覆了大清皇朝的二百多年江山社稷后,又长期地迷惑着中国人的历史情感。
骤然而兴,暴然而起,嚣然而胜,太平军兵锋所向,无坚不摧,无防不溃,八旗军、绿营兵,纷纷败北。于是,当历史学家从纯军事的角度评价太平军所以胜、清朝政府军所以败的战争角逐时,他们基本的定性词语是:“八旗绿营,腐败不堪。”②
面对一支“腐败不堪”的军队,虽胜何荣?
否定了敌人,其实等于否定了胜利的价值。
历史的真实状态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都还是十分强大的武装力量,并未“腐败不堪”。虽然在与太平天国的较量中,“八旗”、“绿营”的战略主力任务逐步让位于初有“团练”之名,尔后具有“超团练”性质的“湘军”与“淮军”,但作为国家常备军、政府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的战斗力并不是后代历史学者所贬抑的那样不堪一击。“卫国”固力不胜任,“残民”则凶狠有加。
正确地评估“八旗”、“绿营”的战斗力,是为了较为恰当地评估太平军的军事实力。借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追溯“天兵”战斗力的源泉,另一方面又可以接近本书的“元命题”之一:“国家军队”何以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人民”武装起来,又何以不能真正地拯救“人民”?
闭上双眼,我们即刻回到太平天国时代。
睁开双眼,我们则在“天兵”的队列里看到“神性”的张扬。
“神性”,是“神”的属性。“人性”,是“人”的属性。二者本有人、神之别,这正如人与禽、兽、虫、鱼的区别一样不可逾越。但“人”很聪明。聪明到能够打破“神”与“人”的隔阂。
洪秀全就是这样的聪明人,一场神经错乱的大病之后,他居然成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要巩固这个精神发现的成果,于是一个充满“神性”的组织便在广东花县的山村里建立起来。这组织,即“拜上帝会”。史籍又载:“拜上帝会”是由“上帝会”、即“三点会”(或“三合会”)发展而来的,而“上帝会”、“三点会”的创始人原是洪秀全的同乡与老师朱九涛。③ 朱九涛死,洪秀全遂成会首。无论如何,总是洪秀全将“拜上帝会”做成了规模,做出了气候。这与晁盖创业,却是宋江将梁山泊事业做大做强相仿。
先是秘密地扎根串连。但“根”扎不下去,“连”也串不起来。本乡本土,知根知梢,爹生娘养,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兄弟,谁信?大抵只发展了冯云山(表弟)、洪仁ㄗ宓埽┑仁耍樾闳惚幌缛瞬嗄慷恿恕U庥α艘痪渌谆埃耗芎逄煜拢荒芎逡槐R患住�
接着,洪秀全远走他乡,赴广西贵县赐谷村传教。时在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与洪秀全同行者,为冯云山。经半年游说,信上帝者亦仅百人左右。洪秀全再一次灰心丧气,打道回府,又到广东老家当起了教书匠。但冯云山“神性”坚刚,转移于广西桂平县北的紫荆山区,佣工、教馆、传教不怠。三年功夫,居然发展“拜上帝会”信徒三千多人。
冯云山创造了一个宗教奇迹,他让天主教、基督教所尊奉的“上帝”,在中国安了一个家,有了中国香火。扩大到政治的、历史的范畴,也可以说是冯云山完成了对洪秀全的“神化”过程,并为未来的“太平天国”打下了“神性”的桩基。
三年时间,三千信徒,这都是为洪秀全准备的。时来运转,洪秀全就是不想当“神”,也由他不得了。听了冯云山的工作汇报,洪秀全大为神气,自然乐于再去广西当他“天命所归”的“天兄”首领。
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这些以后太平天国的诸王领袖,也大都是在冯云山传教时期先后加入到“拜上帝会”行列中来的。
需要“神”,就能“造神”。
你造了“神”,你就变成“神”。
这是宗教魔术,这也是政治魔术。
本来,“神”就不是天生的呀!同样的道理,“天兵”、“天将”、“天兄”乃至“天王”,也都不是天生的。只要主观上“想”了,客观上“扮”了,一切一切的神圣角色还不是人演的吗?
在拜上帝会的旗帜下,万姓奔集。
整整八年的宗教酝酿。“神性”在自我暗示与相互哄抬中取代了“人性”。“宗教”膨胀之后,鼓起了洪秀全们的“政治”幻想,“太平天国”呼之欲出。
三十刀兵动八方,
天号地呼没处藏。
安排白马接红羊,
十二英雄势莫当。
这首江南儿歌所藏玄机,除强调了“红羊之劫”(道光二十七年,即公元1847年,为农历丁未羊年)的必然,还暗示了聚众起兵的最佳时机(三十,即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英雄”,则泛指“拜上帝会”诸头领。④
应了“三十”的天时,一进道光三十年拜上帝会便加快了力量集结。正巧,入了正月道光皇帝旻宁便大病不起,并于正月十四日丁未驾崩。消息传到广西,洪秀全等更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因为一过年(正月初四),胡以晃就变卖田产,全力支持“天父天兄”的事业。这一优秀“典型”,被萧朝贵以“天兄”托命代言的方式加以表彰曰:“胡以晃算得尔真草(心)忠草(心)。”⑤ 受了胡以晃毁家相从的启示,这才有道光三十年八月初拜上帝会七人小组(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开会,正式号召信徒卖田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