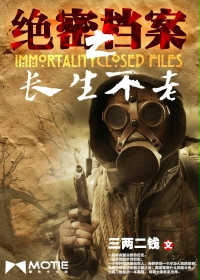红色家族档案-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识里已经接受了上山下乡的安排,并且把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当成今后的革命目标。所以对四汉的说法也不以为然,认为是他没有当上兵,心里不高兴,所以改变了往日忠厚老实与人无争的禀性。可是不知怎么又想起了另一件四汉发火的事情。
收获的季节,我们从山上“捍”谷子回来。一条手指粗的绳子的中间部分用来捆谷子,两头剩余部分挽成两个圈圈,套进人的肩膀,使谷子和人联成一体,或者说是让谷子长上两条人腿,人和谷子一同走回家。山高路远,进村的时候,天已经擦黑,朵朵、毛毛和我以及三捆谷子走到场院的时候,我发现朵朵开始以一种怪里怪气的姿势晃动肩膀。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她是没有力气把肩膀从圈圈里挣脱出来了。我想上前帮她…把,但是发现自己双手和双肩也都麻木得不能动。毛毛一定也和我们处在相同的境地,因为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容易才从那一大捆谷子中脱身,我和朵朵恍然大悟,嘻嘻哈哈正准备照章办理。只听得背后有人凶巴巴地说:“操心!闪了腰!”我和朵朵肩上同时伸过一双手,每只手一边使了一点向上提的劲儿,那点儿劲别提多合适多妥帖了,使我和朵朵一齐卸下了肩头的千斤重担(显然千斤不是事实而只是比喻)。帮忙的是四汉。我们想道谢,只听得四汉更凶狠地说:“瞎球实闹!一群女子,何苦来受这苦!”说完,自管自走掉了。天已经黑,看不清四汉的表情,但他的口气简直要把我们一日吃掉。真不知道他的火气从何而来。这里是贫困的地方,土地贫瘠,单位粮食产量一直在一两百斤。现在每个百十人的村子里凭空来了十几号大男大女,我第一次想到,也许这里的人并不欢迎我们?看样子,不管我们怎样想,怎样说,在他们眼里,我们和他们不是一回事。
这年冬天大汉也从监狱里放回来,说是保外就医。因是戴罪之人,大汉很少走下自家的涧畔,远远地望着大家,他果然是一脸刚毅,神情中有一种优越和隔膜,大概不是因为打死过人,而是曾经拥有一段与众不同的生活吧。
大年初一早上,四兄弟齐刷刷从村中走过,大约是给父母拜年。走到与我们知青窑洞一沟之隔的他们父母窑跟前,他们大出来迎。我才发现四兄弟的父亲并不太老,虽然腰微微地弯了,但仍然是个健壮男人。这汉子脸上现出感动的样子,一家人大约很难这样凑在一起。五个魁伟男人站在村子里,不知怎样就聚起了一股雄浑之气,四周的山都矮小了许多似的。我正在这样看着他们时,心里忽然出现了一个怪念头。我对自己说,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回头看我,我从此把他们当亲戚或者可以信任的人,把杨家湾当亲戚或者可以信任的地方。如果没有人回头,就从此井水不犯河水,熄灭自己进入杨家湾人生活的念头。我敢肯定,他们感到了我的目光,但从始至终,没有人回头。
我就是在这一刻感到了悲观和虚无。无论对别人接受再教育的哗众取宠还是对自己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真诚都大感失望,一堵高墙升起在现实和我的理想之间,身处其中的杨家湾一下子遥远得只可望而不可及,轻盈得可以随风而去。
听说杨家湾现在已经很富了,那整条川地底下发现了更多的石油,油矿打井,付给农民许多钱,农民拿了钱,没了地,所以许多人已经不种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当年被玉米花子闹得心烦意乱的地方现在都树立着采油树了。四汉说过,“迟早你们是个走”,他说对了,当年的知识青年中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梦里我没有见到四个汉子,实际上我已经记不太清他们的样子。但我当然是应该梦见他们的,当年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没有一个人回头看我,对我是太大的恩惠,至少使我知道井水河水确实是不一样的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有难以测量的距离,使我在热情狂热的革命年代少走了许多弯路。
杨家湾,你为何始终这样轻盈、遥远?
四好汉,你们的儿子孙子现在还像你们一样,想离开这个遥远的村庄么?
注释
①十五英寸等雨线是一条假想的线。国际史学界一些学者用它来说明地域降雨量与原始生产方式的关系。这条线从中国的东南走向西北,线之东南平均年降雨至少有15英寸。参见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第三章第25页,三联书店1997年5月北京第1版。
25。没有家的日子
他的话使他们枯萎的意兴重振,凋零的希望复苏。
——《失乐园》230页
1970年冬天,当我和朵朵在生产队请准假回到北京城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家了。一家九口,爸妈和在清华读书的二哥猛猛三个住监狱,朵朵、我还有弟弟了了三个下乡插队,大哥、大姐和二姐三个在外地工厂做工。是个整齐的无家三三制。组织上的说法是:北京没有人,所以不必再安个家嘛。所以,有没有家完全听从革命的安排。
毛毛说,住我们家吧。毛毛说的家不是原来中南海里的家了。邓小平夫妇此时被隔离。但是他们家里有个奶奶。这个老太太既不能上山下乡,不好去工厂做工,也不合适安排到监狱里去。所以,中央办公厅给他们在宣武门外找了两间平房,让老太太住下来。
奶奶精神矍铄,面孔和善,一看就是个勤劳俭朴的人。对我们来说奶奶家里永远有干净的床铺和热腾腾的饭菜。推门进去或开门出来,身前身后永远是奶奶善良安静的眼睛。尤其奶奶做的四川菜在我们来说是世上无双的美味佳肴。住在这里会忘记外面的寒冷和动荡,因为奶奶脸上总有压倒一切的气定神安。宣武门外方壶斋里两间温暖如春的小平房,在中国最乱的时期之一,在我们没有家的日子里,带给我们的安慰和镇定使我终身难忘。一个像奶奶如此善纯淳朴的人有这样大的精神力量,也是我终生需要认识和理解的事情。
那时候在和平里住宅区有一幢五层居民楼,附近的人都叫它“黑帮”楼。因这里住着一些“黑帮”的家属而得名。所谓黑帮,不是指我们现在说的杀人放火走私贩毒的黑社会帮派组织,而是那个年代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别称。住在“黑帮”楼里的孩子,和我们年龄情况大致相同,不同的是,他们尚有一些原因使革命给他们在北京城里留下一个落脚之处,而不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这里有家。这个地方很热情而自然地接待了我们。
我们的真正基地是林枫①的儿女们的家。林家住三层,同一个门洞里的五层是乌兰夫②的儿女们的家。一两家鸡犬相闻,高兴时两家加上两家儿女们的朋友统统合成一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盆里喝汤。很多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饭刚做熟,一大帮客人拥进门。主人头皮发乍,但绝没有把人饿着的事情发生。“黑帮”楼里最经常的饭菜品种是炸酱面,面条可以随时下锅,炸酱可以随时加盐。大家公认当年在“黑帮”楼里吃过的咸得发苦的炸酱面是最令人回味的。
经常在这里出入的孩子都是家里有“问题”的,他们的父亲都是当时一些最著名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吕正操等等。这些孩子们当时都是15岁到18岁的样子。在一起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尤其是林枫的女儿林京京,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带着九岁的妹妹,靠着每人每月25元的生活费过日子,这种“黑帮”子女领的生活费是由国务院管理局从父母冻结的工资里扣出来的。京京还要定时去看关在少管所里的,此时害着严重肺病的哥哥林炎志。提到这个少管所还得提上两句,少管所在北京西苑,全名叫北京少年犯管理教育所。不知这个机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文革”中这里成了关“黑帮”子女的地方。据我知道,先后在这里关过的人有许多,年龄最大的是文化名人邹韬奋先生的儿子、叶剑英元帅的女婿、曾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
京京的家,是所有没有家或者有家而不愿意回家的“黑帮”子女的乐园。不知道她操持家务的本领是从哪里学来,反正只要进了她的门,她就有本领让你吃饱喝足,抽烟的人还可以找到不错的烟抽。但你要以为她是个只会操持家务的温柔女孩就大错特错了。京京更多时候是个琴心剑胆,义薄云天的女侠形象。
“文革”时,走资派是第一专政对象,这个楼里的“黑帮子弟”自然是管片儿民警第一注意的地方。凭良心说,管这片的民警是个相貌挺不错的人,皮肤白皙,五官端正。只因为下巴较长,就被我们起了外号叫“手枪枪儿”。手枪枪儿有事没事的,老到京京家来。看到他不顺眼的,或者面孔生的人就带到派出所去问话。想来他没有真正为难过我们,顶多是带去问问话,又放回来。有时他还会问问这些孩子们的爸妈的情况,满足他的好奇心。我们虽然并不真正怕他,但是却很讨厌他,因为他老是显得很无聊,让我们觉得他来,或者带人走,仅仅是因为他很寂寞。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有一次他来查夜,警察来查夜都是深夜两三点钟,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听见敲门声,京京一个鲤鱼打挺儿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把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我拖到地上,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三把两把把我搡到一个离地一人多高的顶柜里去,又扔上来一个大包袱把我遮住,然后随手把柜门关上。前后只有一两分钟。等我惊魂稍定,京京已经开开门了。我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心里非常紧张,大包袱更挤得我喘不出气来。但我依稀听到京京和他们说话,镇定安详,应对有度。临走好像还说说笑笑起来。但是也有叫手枪把儿得了手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正吃饭,手枪把儿上来非要把一个比我们年龄都小的叫席修明的男孩子带走。说起来也怪,修明可不是“黑帮”子弟,他爸爸在中共中央联络部工作。有共产党国家的重要领袖来华,比如胡志明等人,修明的爸爸都出来陪,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修明爸爸的名字。但不知道修明为什么老往我们堆儿里混。京京说他,人家没家住,没饭吃的人才来我们这儿。你老爸又不是“黑帮”,你有吃有住,干吗老在这儿混?修明不管,有机会就来。他觉得我们这里没有父母管,好玩儿。这天手枪把儿不知怎么看修明不顺眼,非要带他去问话,因为修明的爸爸仍是革命干部,所以他被警察带走大家都不真正紧张。京京更是虚张声势地在凉台上冲手枪把儿大喊:“你可看好了这小子,腿儿快着呐,溜了你可再找不着。”手枪把儿原来走在修明前面,听了这话赶紧走到修明后面去,我们则都在楼上笑得肚子疼。我们饭还没吃完,修明回来了。果然进了派出所,手枪把儿第一句话就问,你爸是谁?修明扔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过去,指着一则胡志明访华的消息,用当年很流行的短句式说:“自己找,我爸,姓席的。”手枪把儿在《人民日报》上找到了修明爸爸的名字,只好放修明回来。临走他也用短句式跟修明说,“别跟他们混,回家,听我的,没错儿。”后来见不到手枪把儿的面了,听说他去参加警察合唱团。我们就说手枪把儿不能站第一排,要不指挥一伸胳膊就碰着枪把儿了。现在想起来,手枪把儿不是个坏警察,他挺忠于职守,而且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他尽量使自己的所有活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
我们没有家,除了在京京家落脚之外,还到别人家里去玩。有一次,我到刘少奇儿女们的家去玩。他们家在北京站附近一个新建的高层建筑的十几层楼上,在当时算是很漂亮了,不仅房间布局合理,他们的房子里还有非常贵重的家具,听说是他们外婆的,由于是私人所有,所以允许他们带出来。那一天停电,电梯停开,我兴致不减地拾数百级而上,敲门进去,像进入了什么漂亮宫殿一般。记得那天他们家大姐爱琴,还有园园、婷婷、小小、爱琴姐姐的儿子索索都在。他们作为主人亲切周到,但我总觉得他们有点心不在焉。由于停电,房间里十分冷,一直到吃完晚饭,房间里的照明灯也没有亮。有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冷了场,这时我听见窗外一列火车驶过,我忽然觉得这火车很孤独,这么冷的天,它要开到哪里去呢。
园园深深地出了一口气,点亮了几只蜡烛。我们每个人的杯子里都被重新倒满了葡萄酒,空气一下子凝重起来,我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园园举起酒杯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让我们祝爸爸平安。”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吃惊,震动,还是感动,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园园又说了一句话:“爸爸是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