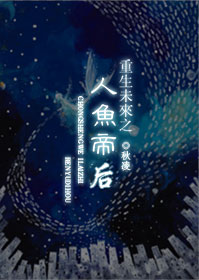人鱼-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温如寄
【第一记·海上花】
1945年8月15日,秋。
是我一生中最欢喜也最悲伤的一日。
那一日,我同乳娘离开这座我日月相伴的城市,远渡日本,去投靠远在千里之外的姨父。
以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亦不知道我的前程是否能够安然,只是我知道,我这一生,恐怕是再也不能踏进沈宅半步了。
也幸好再也不必回来了。
渡口忽然刮起疾风,吹得渡口的芦花簌簌飘散,终于入秋了,那些枯黄的叶子腐败在这大片的水洼里,将夏日的凛冽小心仔细的收拾起来,我想,记忆终于圆满。
天空,忽然飘起极细透明的雨丝来,落在身上,也落在了心上,说不出的凉意。
我的眼眶里忽然涌出了眼泪。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为这么多年的委屈,为这么多年虚假的欢愉,世人善自欺,我也免不了俗。
很多年前,我也是站在这个渡口,送我心尖上的少年远行,那时我还是豆蔻未央的小姑娘,踮起角也只到少年的肩膀,他修长的手指穿过我的发丝,抚摸我的耳垂,然后用惯用的语调唤我——
乔乔,乔乔。
我猛然转过头去——渡口空无一人。
一切都不过是我的幻听罢了。其实我的潜意识也知道,再也没有人会这样叫我了。
阮少游没有来送我,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那个儿时为我打架,少时为我簪花弄梅的少年再也不会出现了。儿时玩伴,少年相许,末了却是一场曲终人散,远走他乡。年少的j□j终究极端,不是之子于归,便是离散老死不相往来。
“三小姐,我们快些,快赶不上轮船。”乳娘催促道。乳娘姓莫,自我懂事之时就陪着我了,我没有见过母亲,是她为我纳鞋补衣,是她陪我度过那些无赖的少女岁月,即使这一次我离开沈家,远渡日本,也是她陪着我。对于她为我做的这些,我并不是没有感激的。
“嗯。”我低眉螓首地应了一声,却没有抬头看她。
“小姐可是牵挂老爷?”乳娘安慰道,“到底是亲生女儿,老爷一时气话,终是还会有再见之日的。”
我避而不答,只是一步一步踏上游轮,海风吹得我的眼颇不舒服,我不想让我眼底的泪花被别人看到,以前都是我送别人离开,这一次,终于轮到我离开了。
我站在甲板的一头,风将木杆上的旗帜吹得猎猎作响,我几乎也要被吹翻过去,索性我将头上的发髻解开,任头发随风吹乱。
这本是我为少游挽的发,数日以前的我总以为如今的我会为人/妻,像嫂子们一样穿着或潋滟或素净的旗袍步入我的良辰美景,而不是像这样去国离乡,远渡重洋。
这是为穷人开行的航班,价钱廉价,船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种均有。白日老弱妇孺大多呆在船舱里。出海的壮丁青年聚在甲板赌博,粗言秽语不断,不时有卖唱的歌女或者提着篮子的卖花或卖零嘴的女童来来回回走。
除了旅客,船上的人大多都习惯了海上的生活,都有面对海上恶劣天气的方法,所以妇女大多是以头纱覆面,婷婷袅袅走在这船上,倒也是一道风景。
我忽然低头看自己的妆容,清汤挂面,天青花色的洋式旗袍,想必是狼狈至极,不成体统。可我又算什么呢?被赶出家门的孤女?被人当众拒婚的弃妇?
“小姐,海上风大,还是进船舱了吧。”乳娘再次劝我。我摇摇头。乳娘终究是拗不过我,只是说进船舱给我拿一件外衣。
夜色渐渐暗下来,海上还是风潮不息,空气漂浮着歌女们飘飘渺渺的歌声,夹杂着赌徒们与之打情骂俏的声音,如此不真实。我又仔细听了听,却是歌剧《茶花女》。
在三四十年代封闭的中国,处于港口城市的沈家是为数不多的开放的家庭,父亲从小就不反感我们接触洋玩意儿,我也时常看些西洋片洋喜剧,《茶花女》也是我最爱的故事之一。
我低声跟着轻吟了起来。
“想不到小姐,也对茶花女也有如此见地。”我抬起头,看见了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浓密英气的眉毛下,眼里掩不住咄咄逼人的光芒,“在下秦知年。”
我向他行个礼,微微颔首,“秦先生见笑了。我是沈乔,只不过你不应该叫我小姐,而是阮太太。”
秦知年愕然,随即又笑道,“想不到小姐年纪这样轻,就已经结婚了,不知是哪位阮先生有这样的福气。”
“他不在这里。”我淡淡地回道,对于阮少游,我并不想多谈,我不想在外人面前展示我是一名弃妇。
我很快就把话题转向了别处,与秦知年深谈,我才知道他是日本留学的一名律师,此次出行正是回到日本,他的确是真正的绅士,一举一动都显示着优雅与从容。
我想,与一名绅士同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我与秦知年言谈甚欢,不知觉也忘却了那些失落与阴霾,他说他曾经去过很多地方,英国的大不列颠群岛,好望角,法国的葡萄庄园,日本的北海道……他环球旅行的故事都很有意思,不知觉天已经全黑了。
“说起来,倒是有一件发生在这东海上的怪事,这件怪事是听我日本的友人所述,我那位朋友一向不太正经,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什么样的事?”我倒是有些好奇。
“我那位朋友也是华裔,却是久居日本多年,据他所说,这个故事从祖辈的游记笔记来的,他说呀,这东海之中,有一座无名岛屿,那是鲛人所居……”
“有这样的奇事,真是有趣。”我不觉莞尔。
甲板上的人们纷纷散去,一点点静下来,我想,夜深人少,孤男寡女在一起终究不便,便起身告辞,秦知年也没有多加挽留,只是含笑将一直背着的手伸开来,手里竟一直握着一朵白山茶。
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在甲板上的卖花女那里买的,难怪他的左手一直背着……
“这?”我正疑惑着,他却忽然弯下腰,将白茶别在我凌乱的发间。
“花面相映,果然与沈小姐最是相衬……”我心中一怔,他仍是坚持叫我小姐……
我“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企图掩饰这尴尬,“那我不成了名副其实的‘茶花女’了吗?”
“你不是茶花女,也不会有茶花女的命运,你只是沈乔……”他信誓旦旦看着我,眼底盈满了我熟悉的笑意。
秦知年,我们可曾见过?
我滞了一瞬,又觉得自己真是多想了。
所以这样一句,我终究没有问出口。
【第二记·殒】
船一直在海上航行了三天三夜。
在茫茫海上,时光无赖,我只能勉强分清日月的界限。
到第三日,海上的薄雾渐渐散开,倒是一个难得的晴日。
可我和船上许多乘客都不知道,那时船已经迷失方向足足有两天了。为了要安抚船上旅客的心情,他们并没有把这一情况告知乘客。
船上依旧是一派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糜烂生活,谁也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正在悄悄的逼近。
我倚在船头的栏杆上愣神,海水被晨曦染成瑰丽带着光泽的玫瑰红,倒是十足像一位眉黛朱红,柳腰妙曼的旧式中国美人。
忽然,背后袭来一阵山茶的香味儿。
不用回头,我就知道是秦知年。
这一些天,秦知年似乎成了我专职的说书人,每天都给我讲了太多太多的故事,我几乎要以为他的本职不是律师,而是说书的了,上这班船就是为了向我兜售这些故事的呢。
可是,我心里也明白,秦知年这样的男子,习惯了欢场奉迎,怎么会单单只为了说故事的呢?究竟有几分当得了真,又有几分存了目的,也未可知。精明如秦知年,大抵不会做无谓之事。可我一个独自远行的孤女,没有财势,没有背景,他究竟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
我想了许久,也想不透,便也不再纠结。
我接过秦知年手上的山茶,抿了抿嘴,笑道,“想不到秦大律师倒是有充当花童的癖好!”
“愿意为美人效劳。”秦知年闻言一呆,随即哈哈大笑,嘴角勾起一个撩人的弧度。
我拨弄着这娇嫩的白色花瓣,忽然想到这么多年阮少游从来没有送过我花,倒是小时候,不懂事,时常偷偷溜去后山才一种叫做灯笼草的香草,好几次都因为分赃不均大打出手呢。那时候阮少游虽然对我忍让,却也有被惹毛的时候,小小的年纪绷着脸,倒是有几分小老头的意味,十分有趣。想到此处,我不禁笑出声来。
“沈小姐想到什么好笑的事了?可否让在下也开怀笑一笑。”
“也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我笑了笑,把话题转向别处,“这几日天气真是无常,都是雾蒙蒙的,难得今日晴空万里,只是有些闷热。”
“的确。”他附和了一句。
岂料过了午后,天气又恢复了一片灰蒙蒙的景象,只是天色较以前更加暗,更加低沉。我坐在船舱里,闷得甚至出了汗,望了一眼窗外天边浓烟滚滚的墨色乌云,怕是山雨欲来。
一刻钟以后,海上起了凛冽的狂风,刮得轮船上的帆布猎猎作响,很快豆大的雨滴就倾盆而下,扑天盖地的横扫袭卷整个海面。
我探出头去,海面上大浪滔涌,甲板上的人们早已经乱成了一团,纷纷朝着船舱的方向涌现过来。
甲板上的雨水如同撒落的珠子一般跳跃着,不一会儿,船上就积满了一定深度的水。又一个大浪涌来,船身剧烈的摇晃着,不能够站稳的老弱妇孺直接翻进了海里。
“沈小姐!沈小姐!”
我闻声见是冒雨而来的秦知年,立即应道,“我在这里。秦先生,我在这里!”秦先生终于发现了我,快速地奔向我,在断裂的桅杆上奋力一跃,终于握紧了我的手。
“还好,我找到了你!”他又惊又喜,不顾礼仪的抱紧了我。
“不!”我忽然想起乳娘还在船头的厨房里,脸色大变,“乳娘她……她还在船头……”
我的眼直勾勾的盯着浪翻滔涌的海面,不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你莫急,我去给你带她回来。”
秦知年将外面的西装一脱,就向船头的方向而去,此时船上重要的桅杆已经细数的断裂,船身在剧烈的摇晃,加上凛冽的狂风,行走已经非常困难,他不得不匍匐着身体,一点一点的挪动着身体。
我又急又恐,我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我的眼里只有那漫天的雨水,我的耳边只有呼啸的海风。
我望了一眼天空,乌云如铅压境,雨势较之前又大了许多,风浪又要袭来,我急切地呼唤,“秦先生,小心!”
只听得“咔嚓”一声巨响,船彻底断成两节,船的另一端彻底淹没在大浪之中。
“不——乳娘,秦先生……”
船舱外面依然是电闪雷鸣,海风狂啸。
船身受到猛烈的冲击之后,船舱开始渗水,我已能真切的感受到船舱下沉的速度,那是死亡逼近的速度……
想不到我竟会葬身于此!
墨蓝的海水一点一点漫过了我的脖颈,我再也听不见那些海啸咆哮的声音和人们哭喊的声音,世界终于归于安静。
冰冷的海水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我陷入一个巨大的梦魇……
我忽然感觉这种感觉如此熟悉,好像前世的记忆在一点点复苏,我隐隐约约听见有一个女孩在哭喊,不甚真切,那声音那样弱,细细的,如同风雨中一掐即没的烛火。
它这样反反复复,在我的耳边晕开,我终于听得真切,她喊得却不是我的名字。
——“月笙姐姐,救我。”
——“月笙姐姐,我好怕……”
——“月笙姐姐,好冷……”
那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急切,带着比海水还冰冷的绝望。我想这定然是同我一起从船上跌落海中的孩子,循着声音想要伸手去够孩子的衣角,除了海水却什么也触不到。
我的意识越来越涣散,直至想不起这一切所有的缘由,终于陷入无边的死寂之中。
我觉得……我真的梦见过一条人鱼,它的尾巴银光一现,隐没在这没有边界的海水中。
【第三记·劫后】
我再度醒来时,发现我被潮水带到了一片海岸上。
月光静谧地照在这片杂石滩上,东方却已开始微微透着点点白光,天已经快要亮起来,世界在混沌的幻觉中复苏。我就这样静静的躺在白石滩上,缓缓的睁开了眼睛,那天边映来的一抹红光在我的视网膜上清晰具体起来。
我想要起身,却在一瞬间,我的头剧烈疼痛起来,几乎快要裂开,海水腥臭的气息在我的口腔中翻涌搅动,我感到剧烈的恶心感。
我平躺在海滩上,眼睛迎着晨曦,眼皮却异常沉重,睁开眼,似乎只能看到灰蒙蒙的模糊了界限的海平面,我努力回想昨夜的那场海啸。
就在那个狂风骤雨的晚上,我似乎真的听到了记忆潮退的声音,在那一场无涯的幻觉之中,瑰丽而久远的记忆如鳞片一般一点一点地从她身体里边剥落,随着海潮散去,最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