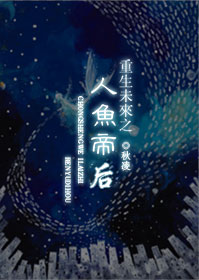人鱼-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叫什么?”她小心翼翼地问。
“哦,这个呀,红豆,又叫做相思子。”
小幽忽然觉得这几个字几乎要烫伤了她的耳廓,那灼热的温度一直从耳廓蔓延到脸颊,她忽然觉得这种感觉实在不太好,又低头继续写,红豆,又名相思子,春采根秋采藤,根叶皆可入药……
她却忽然滞了笔,皱眉,抬头对少年说,“笔画这么……复杂,我不喜欢。”
少年却专注于自己手上的那一卷书,并没有理会小孩儿的抱怨。
可惜时光终究不能理会一个孩子的喜恶,纵然她从一开始就说自己不喜欢,不想要,可是还是把所有的前缘后果种到她的心上。
那个小毛团闯入小幽的世界的时候,是一个午后。
小幽在颜吉这里养伤,本来就很少知道,除了月笙,还有送她过来的那几个人,就没有人知道了。这几日,颜吉一直把小幽锁在院子里,不让她出去,她甚至连自己身处哪里也不知道。
这一日的午后,颜吉出门,照样把小幽锁在院子里。临走的时候,把厚厚的一叠的药典扔给她,要她各抄三遍。
“抄……那么多,干……干什么?”小幽很是不想触颜吉的逆鳞,可是她想到前几天她已经把这本药典抄了十遍了,就忍不住问。
“问那么多干什么?”颜吉不耐烦,“我可以拿去卖,再不济,可以撕着玩……”语气是理所应当。
小幽拿起笔,小小身子半个趴在阳光里,有些不适应,金晃晃的刺眼。
秋日午后的阳光并不灼烈,就像有一下每一下的挠着自己的心窝,虽不至于难受,却撩拨着那绷紧的感官。
后来,小幽忽然觉得心里的挠得慌,演变成了耳边果然听到窸窸窣窣的挠门的声音,开始声音并不是很明显,可是要了后来,她再也无法无视这些声音。
她扔了笔,跑到院子的大门边,将耳朵贴在门上,门的一端果然有挠动的声音,还有“嗷呜嗷呜”的叫声。
小幽心念一动,拉了拉门,果然,颜吉出去的时候上了锁。
小幽搬了不远处晒药材的梯子,翻上了墙头,往下望去,果然有一团灰色的毛团,小爪子不停的挠着门,眼神哀怨。
小幽大喜,朝着它吹口哨。
这牲口最是认主人,这几日小幽不见了,就到处找她,他记得小幽的味道,循着味道,走了很多弯路,终于找到了她。见小幽蹲在墙头,不停的蹦跳,想要跃上这墙头。
她无奈,忙道,“别……急……”
她下了墙头,左顾右看,终于找到了一个竹篮子,系了绳子就往下面放。狼崽抖了抖耳朵,一跃,就耷拉着将着身子缩在里面。
狼崽回到小幽怀抱,打闹了一阵,已经是黄昏,颜吉回来了。
小幽忙把狼崽赶到桌子下面,示意它不要出声。
“写完了没?”少年回来第一句话就是问这样一句。
“没。”小幽心虚,眼睛不停的往桌子底下瞄,小东西见到小幽这样害怕的声音,觉得眼前这个人是在欺负小幽,身上的毛都炸起来,嗷呜了一声。
“什么声音?你背后藏了什么?”颜吉皱眉,瞥了一眼小幽后面。
“没……没……”小幽答得没有底气,不住的后退,试图暗示背后的小东西逃跑。
可惜一个人与一只狼沟通的确有些困难,小东西得了命令,往前一冲,就将颜吉扑倒,对着他又咬又添。
“噗……”小幽极力的任何笑,又被颜吉咒怨的眼神下注,马上把狼崽抱下来,一人一狼,站成一排,乖乖等着挨训。
“呵呵……真有趣,这个狗崽子听你的?”
“咦”小幽惊愕,她没有想要颜吉不恼,反而可劲的揉把小东西的短毛。
小东西耷拉着脑袋,很是温顺,怪不得颜吉把它认成了狗。
“嗯。”小幽也不辩解,只是一个劲儿点头。
“他叫什么名字?”颜吉来了兴致。
“没有……名字。要不,你给它取一个。”小幽想了一阵。
颜吉大手揉乱了小孩的头发,哈哈大笑,“小笨狗,跟他的主人一样笨,不如叫阿笨好了。”
小幽摇头,表示不好。就算是狗,也是有尊严的。
这回颜吉到真的认真的想了一阵,忽然想起今日看的史书,忽然起了恶极趣味,道,“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不如叫做阿蒙吧。”
小幽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前面的那半句话,她自然是听不懂,可是那是颜吉费心想了那么久的名字一定是一个好名字。
“哦,阿蒙,给我唱一个……”
一人一狼面面相觑。
“那你会唱歌吗?”颜吉忽然问,纳笙的姑娘可是从小就会唱歌的,不要说月笙,就是阿绛之流的,也是有一副能唱的金嗓子的。
小幽摇摇头,表示不会。她从小就甚少与人接触,不用说唱歌,就是简单的口语,都不能说好。
颜吉的脸上掩不住失落,“果然,什么都不会,连阿蒙都会嗷嗷叫呢?你说,小孩,养你有什么用。”
小幽却没有反驳。
不过,颜吉除了要养一个破小孩,还加了一只狗……不,狼。
【第四十二记·欢愉短】
小幽在颜吉家养伤一个月,身上终于好得七七八八。
她没有想到,那是她6岁的最后一段的欢愉时光。
小幽伤好,又回到了学堂。依着她闷不隆冬的性子,自然也没有别人在意她。小幽摔断了腿,便是死了埋了,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日子变得跟从前几千个日子一样,变得毫无区别,亢长而繁复,可是总归有些东西是不同的了,可究竟是什么,小幽也说不好。
可不管别的人怎么待她,月笙依旧待小幽很好,那一次小幽坠落山崖,她始终心存愧疚,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终归是因她而起。
因此月笙不管做些什么,有了好吃的,好玩的,都要叫着她,月笙总是笑盈盈的说,“小幽,你要多笑笑才好。”
“真的?”
月笙重重的点头,嘴角轻轻翘起,展开一个和煦如风的笑来。
小幽表情呆愣了一瞬,终于挤出了一个十分勉强的笑来。
小幽那时并没有多少察觉到,脸上的狐狸胎记有多么难看,可是她知道,自己终归是不好看的,可是月笙姐姐说,多笑笑就会好看起来,她却当了真。
以后的日子里,她果然把笑容挂在脸上,吃饭的时候笑,干活的时候笑,快乐的时候笑,苦闷的时候笑,落了泪还是笑。
甚至连身边的人都以为这孩子摔落悬崖,摔坏的其实不是腿,是脑袋吧,要不怎么就魔怔了,成了痴儿呢?
可是小幽却仍旧呵呵笑,那是她于月笙姐姐之间的秘密呢。绝不属于第三个人。
她才不要告诉第三个人呢。连阿嫘婆婆也不愿意。
岁月无期,转眼就是一个秋冬,在这一年里,小幽疯狂的蹿个子,一年下来,她居然蹿高了半个头,虽然不能跟月笙比,但和其他的同龄孩子已经差不多高,眉目也逐渐有了清丽女子的轮廓。每当阿嫘婆婆看了她的眉目,总是忍不住叹息。
这一年里,她已经学会了很多字,已经能过**的阅读书籍,此时她才忽然想起之前颜吉为阿蒙取名字的情景,感情之前颜吉一直在戏耍她呢。
可是她还是对那个外表跋扈内心脆弱的少年恨不起来,只是他给了阿蒙一个名字,一个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阿蒙过了一年已经不再是当年毛茸茸的小毛团了,它已经有半个人那样高,逐渐显现出成年狼的形态,再过一些日子只怕瞒不住它是狼的事实。所以小幽一再叮嘱它低着脑袋走路,夹着尾巴做狗,不要招摇。
阿蒙甚是鄙夷小幽这样掩耳盗铃的行为,它的风姿又岂是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所能了解的?可还是乖乖低头。
可是这样的人生虽然算不得好,但是小幽却觉得满足。
唯一让小幽隐约不安的事,便是那些光怪陆离的梦境,那些从地狱而来的声音扼住了她,让她不得喘息,冷汗直流。可当黑夜散去,海水退潮,所有的感官与错觉都会褪去。
索性也没有酿出什么祸事。
可真正酿出祸事的,却是阿蒙。
事情要从那个冬日说起,那一日,小幽从书堂回家,正好遇上了大批大批的往一边赶的族人和小孩。
“听说豺狼袭击村民,咬死了阿水伯,阿水伯的儿子半根胳膊也被生生被咬伤了。”
小幽听得心头一惊,也往热闹处走去。
那村头果然围了不少人,然后小幽挤进去,果然见到了传说中的“巨狼”。
它被绑在木架子上,指头粗的大麻绳捆了好几遭,可那畜生竟然还没有停止挣扎,“嗷嗷”的几乎每时每刻都要冲破绳子上来撕咬。
没有人看清野兽背后的挣扎,可小幽却看懂了它的不安与恐惧。
那是她的阿蒙,曾经我在她怀里怎么也叫不醒,曾经被她扔进水里冷得缩成一团,她知道狼残暴的本性,可是,在她日复一日的教化下,她不相信阿蒙会这么做。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在众口一至处死恶狼的声音中夹杂着这样一个微弱的声音。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这声音的来源。
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儿从人群里窜出,挡在了巨狼前面,“别……伤害它,它不是狼,是阿蒙。”
“它怎么不是狼,瞧它她锋利的爪子,凶残的模样,小孩儿别靠近它,它会吃了你!”人群中的一人大喊。
小幽听了这话,也没有害怕后退,反而靠着狼又近了一些,他伸出手来覆膜他的毛皮,蹭它的脸。
原本暴怒的野兽忽然之间变得平和温顺起来,连喘息都平静了不少。
人们惊诧于这野兽竟然如此听一个小孩儿的话,继续说,“那又怎么样?我们亲眼看着它袭击,生生撕碎了一个人的!”
那人忽然想起了什么,“小孩儿,莫不是你,把这头野兽引进了纳笙!”
“阿蒙,它很乖,它不会伤人……”一定是有什么因素刺激到它了。
可是村民却依旧不依不饶,呼喊着要杀死野兽,驱逐小幽。
阿蒙咬牙切齿,工着身子,怒意凛冽,似乎随时可以扑过来。
“阿蒙,停下来。”阿蒙闻言十分不情愿铺天盖地就要溢出来的怒意,老实的盘腿蹲了下来。
“膨——”的一声,小幽重重的跪了下来。
一人一狗,不跪天,不跪地。为了活下去,对着纳笙众人跪了下来。
“后来怎么样了?阿蒙当真在这场事故中被处死了吗?它为什么会在那天故意伤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
婆婆却摇摇头,说,“小幽看似软弱,其实爱恨决绝,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会完成它,要守护的东西,撞到南墙也不回头。我刚到的时候,小幽已经携着那狼逃走了……后来,我们安葬了阿水伯,才发现那狼发狂的理由,那一日的事情,倒是牵扯出阿水伯父子一桩家事,原来阿水伯的儿子与他的后娘通奸已久,对着阿水伯很早就起了杀心,至于那畜生为什么会发狂,大抵用了什么让野兽发狂的药物,只不过,那药效实在太强,竟然连阿水伯儿子的胳膊也咬断了。”
婆婆叹了一口气,继续说,“可是这一些,都是后来的事了。”
小幽和那孤狼那日携着逃跑,没有人知道他们躲到了哪里去,甚至有人怀疑她们早已经出了海,没有人能够找到他们。
纳笙人本来料想着一个小孩带着一个受了伤的畜生,实在不能走去哪里,可是搜寻了一整天,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只有一个人知道。
那一日,小幽同阿蒙从山下跑出来,跑着跑着就到了悬崖边上,大浪滔天,竟是无路可去。
阿蒙望着断崖下汹涌的海水,仿佛丧失了所有的力气,耷拉着脑袋,萎靡不振的样子。
真的……走不下去了吗?
她从小遇到的困难与挫折不在少数,却是第一次生出这样的情绪,沮丧的,无力的,想要放弃。她知道自己在这座岛上向来不受待见,如今阿蒙又闯了这样的祸事,只怕这岛上再也没有容身之地。
她眼里突然泛了泪花,伸出手去揉阿蒙的杂毛,笑,“阿蒙……你也很累了吗?我好累,走不下……”她双手抱膝,肩膀不时的耸动着。
她低声蒙头啜泣了一会儿,觉得实在是太丢脸了,忽然抬了头,生了笑意,“阿蒙,你知道吗?从小到大,对于我的阿爸阿娘,阿嫘婆婆从不肯说。唯一的一次,婆婆不耐烦的哄我,说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知道岛上的浮生花再开,他们就会回来,可是我已经找到了浮生花,为甚么,他们还不来接我。”
她那么委屈,可是却没有人看到她的委屈,也没有人愿意听她说起她的委屈。
海风飕飕而来,小幽觉得很冷,朝着阿蒙身体的热源凑了凑,远远看上去,是彼此依偎的模样。
“可是,我却一直知道,我的阿爸阿娘是世界上最好的阿爸阿娘,甚至比月笙姐姐,阿绛的都要好……他们不来接我,我们去找他们,好不好?”
阿蒙望了一眼小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