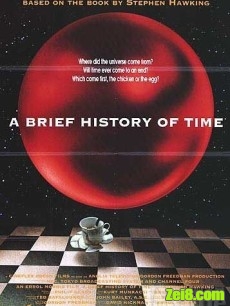时间的血-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则。可能,他的头脑根本就没有长大。他仍然是那个因为病痛而吃尽了苦的孩子,他的父母把他推到同龄小孩的嘲笑和拳头下。
对,这个理论能够成立。因而,他的仇恨浮了上来。
他的残忍只是他的痛苦的反射,在他眼里,孩子们是他的痛苦的起因,孤独的根源。
他把自己的苦难发泄出来。
这说得通。
至于凯奥拉兹……弗朗西斯·凯奥拉兹的性格是人尽皆知的,杰瑞米已经作过一番详尽的描述。这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习惯获得一切,无止境地拥有,渴求尽善尽美,一直到迷失了自己。
对权力的胃口造成荒唐的螺旋形堕落。
可是,凯奥拉兹是个文明社会的人,身上烙着文明教育的印子,虽然今天他觉得自己可以凌驾于道德准则之上,却干不出用在死去孩子们身上的残暴行为。
于是,他利用了蛊。
他操纵着黑巨人,就像是个真正的木偶戏大师,他扯动绳子,把这个受伤的人引到仇恨的道路上,启蒙他投入罪恶的发泄渠道。这是一种绝对的解脱,也是一种快感之源。
而凯奥拉兹就以特权为乐,躲在后面观察他的魔鬼的卑鄙行为。
就像是弗兰肯斯坦,他就是吸引了所有目光焦点的魔鬼身后的那条黑影。
不,杰瑞米纠正,得在最终报告里指明,凯奥拉兹不仅仅以统治别人,决定生与死为乐,他甚至更加下流:他真的获得快感!在最后那名被害孩子的犯罪现场,屋顶上找到的精液就是证明。
就在蛊扑到孩子身上时,凯奥拉兹站在一边窥伺,满足他猪猡的性幻想。
杰瑞米阴沉地点点头。凯奥拉兹跑不了了。
狡猾的百万富翁诡计多端。他甚至绑架自己的孩子以赢取公众舆论的支持,在感觉受到案件调查的威胁之时,他要巩固自己无辜的表象。对于杰瑞米来说,凯奥拉兹属于那种极个别的人,除了自私,他永远处于求生状态,因此没有任何真正的牵挂,绝少感情,特别是自身对世界彻底漠不关心。凯奥拉兹把自己看做是游戏当中的头脑。任何东西,任何形式的生命只是他本人找乐和个人发展的工具。
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究竟冷漠到什么程度?他能让自己的骨肉去死吗?杰瑞米攥紧拳头。凯奥拉兹得垮台。
为此,只缺一样东西:证据。
一样把他和这些罪行,以及和这个……蛊联系在一起的证据。
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杰瑞米付了咖啡账,然后到警察局去了一趟,确定没有任何留给他的口信。全城都在沸腾,独立分子在城里来来去去,搞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所有身体健全的男子都被招去弹压叛乱。
游行示威活动正在蜕变,几年来政治暗杀接二连三,却找不到任何令各派系满意的协定。
杰瑞米躲过征用,朝开罗城区方向走去,他刻意从北边绕了个大圈子,避开中央道路上的冲突。
他花了一个小时才找到昨晚帮助他与当地人交谈的那个翻译。
他付了些钱给翻译,以此为交换,翻译替他统计阿齐姆失踪的晚上帮他一起捉鬼的那些人,并且找出他们的住址,以便收紧钳子,挖出蛊的洞穴。得从昨天见过的教长开始,他该认识大多附近居民的住处,这是个最合适的起点。在证言中,或许可以综合些其他元素,运气好的话,甚至能挖出蛊的老巢。翻译得把所有这些问题问一遍,如果他能获得有用信息,就能得到相应的报酬。
杰瑞米去火车站区吃晚饭,在那儿,暴乱好像没造成什么影响。
然后回家。他视线模糊,刚灌下去的葡萄酒在蒸发。
暮色降临在开罗城。
他没有醉,远远没醉。只是有点灰,正好可以暖暖心,给自己壮壮胆。
当他经过连着火车厢的帐篷时,侦探还是摇晃了几步才站定,他看见视野所及之处有点不同寻常的地方。
一个硬纸筒搁在一只箱子上,就在门边。筒子有四十厘米长,和图书馆里用来收藏地图的那种相似。
杰瑞米打开硬纸筒,从里面取出一块羊皮纸。还有一纸考克医生的短信。
天还不是很黑,杰瑞米凑近还可以辨认上面的字迹。
“这是一份行政文件,多半写于十三世纪。文件内容有关一座宫殿地下室的维修保养,以及为建造卡拉温苏丹的医院所用的花费。
文件注明,封住连接小宫殿和大宫殿间的秘密地道的可行性。我的朋友附带给我一份说明,这些秘密地道大约处于现在的汇赛因清真寺和埃尔·阿扎尔大学之间,它们至今还没被挖掘出来,不过,好几位考古学家在为此努力。你知道吗?在朋友给我的考古学家名单里,有一个是我们的客户:弗雷德里克斯·温斯路,一个半月前,那个中了一颗子弹而死的家伙,也就是你说的那个‘烂案子’。据说,就在被杀之前,他号称找到了秘密地道的一个入口。明天早上给我打个电话,或者,过来一趟。你的朋友,考克医生。”
愤怒的杰瑞米真想揉掉这封信,但又制止自己的手指作出任性的举动。酒让他的脑袋晕眩了片刻。
温斯路不仅是被人草率杀害的考古学家,也是个熟人。在城里几次有钱人的晚会上,杰瑞米和他经常在一起聊天。温斯路的名声不好,人家说他“很会修修补补”,在考古发现时作些小动作,让遗址显得更有价值。他不遵守惯例,一向自己单干,他作考古挖掘不是为了哪家博物馆,他只肯为出得起最高价的收藏家服务。那确是一桩“烂案子”,杰瑞米没有忘记,他曾强调嫌疑人数之多:考古雇佣军里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刁滑同事;满口高喊保护古迹的狂热分子。
线索众多,可以通向四面八方。放下这件案子接手孩童谋杀案时,杰瑞米始终什么也没找到。
杰瑞米迅速作了总结。
从现在开始,即使最迟钝的法官也不能再否决他的结论。他和这些谋杀案之间的联系不只一个。凶手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损害他。凶手始终是在围着他打转。
再一次,事实比虚构走得更远。不是假象,从开始起就只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罪人,是时间把一切掺和乱了。没有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中的戏剧性结尾,只有简单明显的事实,现实总是显而易见,简直没有味道。凯奥拉兹是他第一个怀疑的人,到头来,罪魁祸首就是他。
杰瑞米想道,在一篇虚构的小说里,犯罪的本可以是医生。他生活在鲜血中,又是大战中的老兵,受过刺激,留有后遗症……他通过基金会认识了这些孩子,他本可以某日在医院治疗蛊时结识他。
而且,是他解剖了考古学家温斯路的尸体,他可以潜入温斯路的家偷偷查看他的笔记。
如果是一本女作家写的小说,杰萨贝尔也可以作为最理想的罪犯。一个心理失衡的女人,没有真正的根,一个寻找方向的孤女。
可以有那么多疯狂的理论。
杰瑞米小心地卷起羊皮纸,放进衣袋里。
他正想踏进火车厢,却又急忙收回跨出的脚,以至于滑了一下。
门开着,他刚才没注意到。
大脑里的酒精一下子跌落到内脏深处,又多释放出一份警惕。
他正好听到,有脚步声,在地毯上悄悄后退,发出轻轻摩擦声。
42
弗朗西斯·凯奥拉兹。
玛丽咏几乎感到失望。罪犯好像太明显了。然而,就像杰瑞米强调的那样,事实经常就是这样简单。没有最后时刻的戏剧性变化,没有邪恶的阴谋诡计,只有一条平常的个人轨迹,渐渐滑向悲剧。根据她在巴黎法医研究所当秘书的经验,她知道犯罪调查主要围绕相同的几样东西:妒嫉,贪婪,觊觎。大多数暴死原因都不会离开这三点。
这三点中的这一点或那一点指引了这个世界上凶手的手或头脑。
除了系列杀手。
他们不同,不能与其他坏家伙相比。许多概念,诸如个人的寻求或发展、心理平衡、求生需要在他们的恶毒阴谋中起着作用。
但是,在这些非典型的魔鬼之外,其他人犯的罪都以不同的方式反射出是妒嫉、贪婪和觊觎三者在作祟。
凯奥拉兹完全是另一类人。玛丽咏用自己的工作术语来概括他的特点。他从强迫性施虐狂过渡到自高自大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他自己的成功把他的野心毁了。两者混和,造就了毁灭性的变态。
这些用词可能有些过火,但是玛丽咏很为自己的分析得意。她把自己想象成那个美国女作家,巴特丽西亚·康威尔,她曾经是太平间的计算机操作员,后来用自己学到和听来的东西创作小说。
“我没她有天赋,尤其没有她富。”
毕竟,杰瑞米·麦特森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谁是罪犯。在一个瞬间,玛丽咏想试着自己来调查这个案件,到网上去查询这一切是怎么结束的。但她立刻撇下这个念头,还有几页没读。
有谁会比坐在第一排的人能更好地叙述这出波澜起伏的戏的尾声?
还有二十多页,她不久就会知道得一清二楚。
怎么评价这个……蛊呢?
玛丽咏听任自己被这个故事牢牢套住,她只想与杰瑞米一起思考,不想自己去寻找各个谜的答案,尽管她有能力可以猜出几个。
接着,她花了些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
蛊。
当然,那是人,不是鬼。一个被严重感染吞噬了皮肤的人。起初,玛丽咏想到的是麻风病,杰瑞米在日记中也这样推想过,但是这个解释站不住脚。她于是记起了另一种病的名称,这种病如今还在尤其像非洲这样的地方肆虐。
诺马病。纯粹的痛苦。
蚕食嘴巴和脸部皮肤的坏疽性感染。玛丽咏对这种病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她在电视里看到一部关于这种疾病的片子,之后,她又重新打了一份关于诺马病的长篇报告,当时,有个婴儿在巴黎郊区的一幢肮脏住房中死于这种病,玛丽咏的报告作为备忘录被发到法国所有医院和法医科。
她记起病的正式名称:CANCRUM ORIS。
大多人都没听说过这个名称,但它却像是噩梦一般。这种病不会传染,只涉及极其贫穷的那些人,口腔卫生和营养条件都相当恶劣,除了很少的几个移民病人外,在法国看不到这种感染。尽管如此,专家们却认识到由它而引起的所有可怕后果,它摧残身体,造成畸形,也带来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后果。
在二十年代,得了这种病意味着被排斥,被仇恨,被视为渣滓。
这个黑巨人,除了被疾病蚕食,还遭到嘲笑、欺负、恐吓。他不得不远走他乡,在痛苦中生存。他孤独一人,又不得不躲着别人,于是难以找到食物,难以把食物变成流质,难以生存下去。他在身体上完全被摧毁了。
玛丽咏想象他过的生活。
他对孩子们的野蛮残酷无法让人宽容。然而,对于玛丽咏来说,最具有悲剧性的是,弄明白从哪里来的力量让他摧残天真的孩子。他自己早就失去了童真,他对其他人一定只有仇恨,更不用说孩子,他们一定在街上不是嘲笑他就是畏惧他。杰瑞米很好地勾勒了他的轮廓。作为猎手,他简明扼要地分析了魔鬼的诞生。
就要结案了。玛丽咏接着往下读,她把毯子盖在腿上取暖。
暴风雨在消散,风继续在外面呼啸,修道院里如果有一扇门打开,风呼地就伸进一条胳膊。
一种尖利的哀鸣声从修道院的内脏里升起,涌过螺旋楼梯,就像是吹过天笛,整座美尔维耶开始鸣奏起来。
风骤然落下。
石头管子一下子被排空,当作嘴的门缝沉静下来,当作簧片的台阶停止了震颤。
就在这个空隙,玛丽咏听到门锁喀嗒一响,似乎有人试图掩盖发出的声音。
她浑身僵硬。
谁把她锁在里面?是对面那扇门,就在天桥上,一个半小时前,她就是从这扇门经过的。玛丽咏记得自己用钥匙把门锁上了。
有人开了门。
动作缓慢,为了不让人发现,利用风声作掩护。
那人躲在另一边,他想趁玛丽咏不注意偷偷靠近。
那个神秘的戴风帽的人。肯定是他。
这个人和1928年在埃及小巷里游荡的蛊如此相似,如果不是眼下这情形的话,玛丽咏还会觉得很有讽刺意味。
玛丽咏把书放在毯子上,不出声地站起来。
她不是在当警察探案,她来不及逐步收集线索,最后揭露窥伺她的人。
她得采取主动,引蛇出洞。
她在柱子间蹑手蹑脚地走过,然后登上天桥楼梯,在门前站住不动。
她屏住呼吸,跪在地上。
嘴里分泌出太多唾液。
她轻轻地把口水咽下去。
玛丽咏张开手贴着门,眼睛凑到锁眼上。
小洞里一片漆黑。
她盯着黑暗深处。
没注意到一条影子悄悄地出现在她的背后。
一个穿着僧袍,脸上罩着风帽的影子,穿过宽敞的骑士大厅。
玛丽咏什么也看不清,她只是肯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