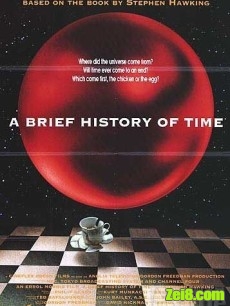时间的血-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把我送回家。过了几天,我的父亲终于把麦特森埋在沙漠里。关于他的失踪,警察局立了个案,但是什么也没找到。听那些对他最为了解的人说,最后几个月里,他变得越来越冲动,时常爱大发雷霆。他的脾气在变,本性中的兽性露出头来。本能渐渐超越了猎手的理智。至于我,我假称什么也记不得了,我撒了谎,是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得出结论,说杀害孩子们的凶手就是这个黑巨人,大家都很满意。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杰萨贝尔一直在找麦特森的日记,一无所获,他告诉过她这本日记的存在,她很担心地想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我始终没能告诉她是我拿着这本日记。”
乔治接连咽了几下口水,然后让玛丽咏当中间人作判断:“从现在起,你还怀疑杀害孩子们的真凶的身份吗?”
她想开口,然而,她却没有力气吐出一个字。
“你在想,这是为什么,对吗?”乔治猜测道,“为什么他会干出这一切?这是一个受折磨的灵魂,一个完全不知道感情为何物的人。正如杰萨贝尔那晚到他的火车厢中见他时说的那样。她摸不透他。因为他不是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人。他已经不再是真正的人。
从某种角度讲,他是一个精神失衡的人,但他意识到自己的变态,他为此而痛苦。我想,如果杰萨贝尔对他来讲如此重要,那是因为她个性很强,又很与众不同,这让他感受到了从来没法感受到的东西。
他犯下的罪行,不仅极其残暴,而且让他激动。他只是一具空壳子,对着虚空哭泣。只有用反常的、极端的感官刺激才能填补虚空。”
高于海平面一百米以上的修道院教堂顶上,一长串蝙蝠掠过站在那儿的两条人影。
“要摸透他,你就得知道,他指责我父亲变态的大部分胡言乱语只不过是从他自己身上搬过去的。那几页心理分析只是把他自己的真实面目转移到了他编造的替罪羊身上。这样既清除了情敌,又让自己显得很清白。说到这儿,读他的日记,他为我父亲编造的犯罪心理过程非常可笑,不过,如果把它放到杰瑞米自己身上,就完全讲得通了。只要把陶醉于权力——这是他放到我父亲身上的转折点——改成战争的可怕后果让杰瑞米·麦特森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这时,我们才能理解。”
裘击了一下手掌。
“他实际上命中注定要下地狱。战争让本来只是个孩子的他丧失了人性。”
玛丽咏一震。
战争。杰瑞米亲眼目睹那个可怜士兵遭受酷刑。
乔治指着日记。
“按住第一页,把封面撕了。来,别怕。当年是我装的封面,做的伪装。”
玛丽咏听从他的话,用力一扯皮封面。封皮刷地撕开了。
“行了。”乔治指挥她道。
他弯腰用手指尖在封皮下摸索。
“找到了……”老人抽出一张黑白旧照片。
“给你,看看吧,这就是杰瑞米·麦特森。”
玛丽咏接过照片,有点忐忑不安地见识日记作者的真实容貌。
他长的正如日记中描写那样,是个美男子,但某种表情让他的脸庞显得阴沉,甚至有点令人担心。目光中有种不可捉摸的光,有点模糊、多变,就像是全息相片,换个角度看,脸部表情就会发生变化。
某种冰冷的怒气,似乎永远也化不开,玛丽咏不是很有把握地琢磨着。或者是一种持久的痛苦,把他烧成了灰烬。
另一种直感同时向她袭来,更加让人心神不宁。
他眼中的这种光来自一具没有生命的躯体,飘浮在他的内心深处,那是他的灵魂的光。
那是种让人害怕的光晕,很久以来就死了的良心的光晕,抛弃了躯体,任它去漂流。
他掩蔽的是自己的尸体。
杰瑞米的身边站着个漂亮的女子。玛丽咏没费劲就认出了她。
高贵和冲动都写在她的脸上:杰萨贝尔。
照片是在一片沙滩上拍的。杰瑞米穿着游泳裤,一种比较长的短裤,这是当时的款式。他赤裸着上身,前胸上有一道隆起的长长痕迹。
玛丽咏翻过照片。
“亚历山大,1926年9月。”
“我找到日记本时,照片被夹在里面作书签,”乔治解释道,“这是杰瑞米犯的一个错误,就因为他对杰萨贝尔太钟情。”
乔治这才透露了杰瑞米·麦特森这架疯狂机器的最后一环:“与我父亲和杰萨贝尔共进晚餐的那个晚上,有些喝醉的麦特森向他们讲了一则故事。你可能已经猜出来了,关于这点,他也撒了谎。他并没看见这个年轻士兵被无耻的下士们长期殴打和强奸。他没有看见,而是亲身经历。他就是那个士兵。”
玛丽咏用食指划过侦探胸前的长条疤痕。照片在风中抖动。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杰萨贝尔在那晚哭了,”乔治强调道,“她全明白了。当他讲到用刺刀摧残士兵和胸口上的疤痕时,她记起他身上的这一长条伤疤。她意识到他在战争中所经历的痛苦。每次肉搏,每次他得向德国人发起冲锋,回来时一边惊讶自己还活着,浑身沾满战友的血肉;一边却要面对另一个地狱。然后又要去冲锋,去被打得皮开肉绽。”
玛丽咏细看照片,这个让她分享了他的存在的男人,让她经历了他的探案过程,让她看到了他的痛苦。她想象他在舒布拉的阴暗小巷里游荡,跟踪黑巨人,接近他,和他说了几句阿拉伯语。接着,她的眼前又出现另一个画面,他让他的“爪牙”到地下室,把他藏在那里,许诺给他食物,唆使他在他找来的孩子身上发泄他的怒火。
杰瑞米津津有味地在一边观看。
他还杀死了考古学家朋友,因为他向他透露了自己的新发现,这个理想的藏身处。他残酷地杀害了阿齐姆,因为他将让他的全盘计划毁于一旦。
是他撬开了凯奥拉兹基金会的门,偷看孩子们的材料,以便更好地接近他们和收买他们。玛丽咏闭上眼睛,她意识到,可能他有意选择那个得血友病的男孩,大量的血流个不停,让他得到最大的满足。
整部日记在她的脑中串在一起,人物,岁月,酷热,开罗的房屋建筑,她又把阅读时在脑海中放映的这部电影用快镜头重温了一遍。
忽然,画面静止无声。
一个新的场景加了进来,这个场景不是来自日记,而是来自这个备受伤害的老人的回忆。
1928年3月的一个下午。
玛斯佩罗大街上满是行人。法国妇人躲在遮阳伞下大声说笑着卖弄风情;开罗女管家在棕榈树荫下推着童车散步,棕榈树在街道和壮观的尼罗河之间构成一条绿带。穿西服的男人在人行道上摩肩接踵,礼貌地道歉。他们的身后是摩登大楼,全部用石材和钢材建造的五层楼房,顶楼的玻璃窗开着,窗帘挡住了逼人的太阳光。
簇新的轿车在车道上发出轰鸣声,汽车喇叭让骑骆驼的人和骡子拉的大车靠边站。马路当中,大家给驶近的有轨电车让路,电车发出铁器清脆的叮当声,头上的辫子冒着火星。
一个意大利口音的妇人弯腰对着一个小男孩,他穿着白袜子、皮凉鞋、短裤和沾着茴香糖污迹的衬衫。一个卖橙子的货郎,在他们面前停下,拿出一只橙子兜售。妇人斩钉截铁地打发他走,显然对处理这种情形很在行。
“别忘了做音阶练习,”她提醒男孩,“要天天做。”
电车咯吱停在他们面前。
门开了,小男孩和意大利妇人道别,然后上了车。
“下周见,”她高声叫道,车门在她面前关上,发出很大的响声。
车厢抖了一下,开动起来。车窗玻璃的鲜艳色彩在人们眼前闪过,电车开过了有钱人住的街区。
车上的人挺满的,没有空座位,小男孩犹豫着是不是要到后车厢去,那里是妇女的专用车厢,还有几个空位。但是他没有动:“不可以这样”,大人经常这样告诫他。
他抓住扶手,正想观看窗外的漂亮汽车,却在乘客中间认出一张脸。
这是一个长得相当高大的男人,正盯着他,嘴角挂着微笑。这时,他的笑容更加舒展,露出兴高采烈的神情。
“你好!乔治。”他招呼道。
乔治认出他,他是昨晚到家做客的那个人,是个警官,他父亲对他说过。
“你认识我吗?”
小男孩点头说:“你好,先生。”
男人说话声不高,只有男孩能听得见。
“我的运气不错,在这儿找到你,”他说,“我还怕错过了你。
我是跑着才赶上电车的,你知道吗?”
乔治礼貌地点点头,他的目光却立刻被一辆轰鸣着超过他们的汽车吸引住了。
“你喜欢汽车?”警官问他。
“对,我最喜欢汽车。我爸爸有一辆本特利。你知道本特利车吗?先生?这是一辆开的很快的车,最快的车。”
在他们旁边,有两个男人在读报,神态严肃。再远一些,另外有一个一边抠着鼻孔,一边望着窗外的风景。
“啊,当然,我知道本特利。你知道吗?我的车比本特利还快!”
乔治皱了下眉头,仿佛觉得这是不可想象的。
“真的,我向你保证。如果你愿意,我带你去转一圈。”
乔洽像任何一个小孩子一样,一脸不信的样子,但又很向往。
“好吧,不过,在这之前,”警官接着说道,“我得告诉你,是你的父亲让我来的,所以我才知道你是在这辆电车上。他让我把你接去看他,在马球场。你看过马球比赛吗?”
“没有。”小男孩立刻兴致勃勃地回答。
“对,我想,你的爸爸就是为了给你一个意外惊喜才这样安排的。你得跟我来,我带你去见他。”
乔治羞涩地点点头。他还是有些迟疑,但又不怎么敢违抗一个成人。
“我们坐你的汽车去?”他问道。
警官轻轻笑出声来。
“对,你看着吧。你可以坐上去。”
孩子看上去放心些。
警官直起腰:“瞧,我们就在这儿下车。来,跟我来。”
他向他伸出手,乔治把自己的手塞进他手里,他们走进炽热的阳光里。
“它在吗,你的汽车?”孩子问道。
“我们先去我家,车在那儿。”
人们从电车里面可以看到他们远去,这时车门又关上。
现在,由于距离和来来往往的车辆人流,警官的说话声听不真切。他说:“到家后,我向你介绍我的一个朋友。你看吧,你们可以一起玩。”
他们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开罗城和密密麻麻的人群中。
玛丽咏咬紧牙关,忍住从内心深处泛起的苦涩。
她用指尖抚摸着嘴唇,仿佛在感受自己的脸庞,找回自己。在这么多生命经历中,她迷失了自己。
她看见右方一座灯塔,灯光像刷子一样扫过。
所有这些星星,自古以来人类悲剧唯一沉默的证人。
她缓缓地把照片放回日记本里,把日记捧在手中一会儿,然后递给老人。
“我想,它属于你。”
他接过去,把它放进一只口袋里。
“现在,你都知道了。”他总结道。
“除了一点。这么久以来,是什么原因让你一直留着它。”她尽量用尊敬的语气说道。
他向她露出疲倦的微笑。
“它帮助我理解。至于剩下的吗……我那时是个孩子。人们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一个孩子的行动。今天,我是个老头儿了,情况还是一样。”
“那么,在这两个年纪之间呢?”她温和地问道。
“我试着理解杰瑞米·麦特森。”
玛丽咏咽了一下唾沫,她不敢问那个到了嘴边的问题。乔治对她点头鼓励她开口。
“嗯……你理解他吗?我的意思是,超出仇恨?”
他拍打着装日记的口袋。
“有时,我为他的一生哭泣。”
玛丽咏扣紧大衣抵御寒风。
“现在,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对自己说这一切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冗长而奇怪的故事,发生在很久之前,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成了一段模糊的回忆,仅此而已。出于对我的尊敬,你还是忘了它吧。如果我是个魔术师,我会把它从你的脑中拿走。”
他的一只手搁在她的肩膀上,指给她花边楼梯的方向。
当她走去时,眼角好像瞥见他一动。
乔治正在擦拭脸颊。
尾声
玛丽咏和贝阿特利斯紧紧拥抱,然后走下格朗德街。
她们已经互相道了别。
乔治·凯奥拉兹吐露隐情后才过了两天,一辆高级轿车在圣米歇尔山脚下等着她。
她在山上只度过了两个星期。
安娜修女前一个晚上来通知她说有人来接她。她这就回巴黎。
在同一晚上,玛丽咏接到一个电话。事情有新进展,一位法官对这个案子特别关心,她将立刻被传讯。接下来……没人能回答她。她将在饭店里住几天,然后再作考虑。什么都没有解决,她的流浪生活还会很长。
她走得比预计的早,走时的情况很特殊,甚至很刺激。
玛丽咏一早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