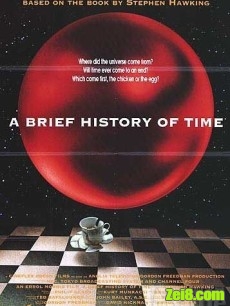时间的血-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的指甲黑乎乎的,泥土使手指的每条纹路显得更深,不时有一块块脏东西掉下来弄污白纸:
TOURGABRIEL·PIERREJAUNE
(加布里埃尔塔·黄石头)
06
一道浅蓝色的光笼罩着卧室,太阳光已经完全消失了。只有单人沙发和灯的四周有一圈琥珀色。
“加布里埃尔塔,黄石头。”玛丽咏朗读道。
她把记事本搁在膝盖上。
那人到底要她干什么?把她引出去做跟踪游戏?
她抬头向窗户看去。夜色中,公共墓地好像老了几个世纪,里面的十字架看着让人害怕。苔藓看上去肉鼓鼓的,把一块块石头连在一起。远远的上方,融成一团的修道院端坐在岩石上,守视着小屋。
玛丽咏找来安娜修女这天早晨给她的地图,把她展开在矮几上。
加布里埃尔塔的位置有些偏僻,在山的西梁上。
这是座圆塔,依海而立,有两条道通向那儿。其中一条在涨潮时就不能通行,要走这条道得从大门出镇子,绕一个圈子到法尼尔。
另外一条道对新来者说比较复杂,先要爬到镇子的高处,一直到修道院巡查道,然后从“法尼尔坡”重新下山,直到加布里埃尔塔。
有地图在手,不该有很大困难。
玛丽咏折起地图,下楼取大衣。
当然,她要去。现在,她的好奇心被唤醒。否则,做什么呢?洗个澡,胡猜一通这个游戏的理由?那也太枯燥乏味了。
枯燥乏味,还惹人生气。
她整了一下衣襟,一口气喝完一杯水,走出门,细心地用钥匙锁好门。
小街跟下水道一样黑,就像是中世纪阴暗的小巷:一边是墓地地基的外墙,另一边是一排小房子,到处是老石头,当作路灯的是一盏熄灭的锻铁灯笼,在风里发出嘎吱声。玛丽咏意识到自己没有电筒照亮脚下的路,也不能看一眼地图。可幸的是,她脑子里对要走的路径很清楚。不必想着从下面走,她下午时看见,海水已经上涨,现在,海浪该舔着城墙了。
她向左走。
地面由砖块铺成,玛丽咏什么也看不见,她走在一团漆黑之上,只听得到自己的脚步声。
一串台阶出现在她的右面,台阶沿着墓地通向山的高处。
她竖起衣领,保护脖子不着凉,双手插在衣袋里,双肘夹紧身子攀登台阶。
阶梯很窄,转了好几个弯,在石灰剥落的矮墙和老房子中间穿行。不一会儿,玛丽咏已经能俯瞰镇子,很少有光线从那里发出来。
路上空无一人。
她来到修道院的脚下。这儿是信仰的堡垒,面对海湾,威力无比,主宰着一切。玛丽咏在它的佑护下走了一程,一直来到一道很高的阶梯前,阶梯之下是条蜿蜒的山路,在树木间曲折地向下,直通到法尼尔。
风更大了。
加布里埃尔塔出现在下方,掩映在覆盖山岭西边和北边的绿色植被之中。塔比较高,特别宽,它与山上的其他建筑隔离开来,就像是个贱民。
海浪拍岸声与海风呼啸声汇集在一起。
玛丽咏终于来到一扇开着的窄门前,窄门通往塔的一侧。
一道巨浪拍在塔的另一边,撞在石头上摔成碎片。
玛丽咏嘹望了一会儿眼前景致,忽然感到不知所措:她与海面处于同一水平。她陡然失去了安全感,没有了控制一切的感觉,变得不堪一击,仿佛遭到摆布。
对,就是这个词,遭到摆布。
从高处俯瞰,围绕着她的这一大片黑色显得美丽无辜,就像是一幅画。现在,大海可以伸出任何一只凶恶的爪子把她抓住,只要它骤然动怒,就可以把她拖向大海深处。
微弱的光亮让每个声音变得更响亮、更可怖。玛丽咏把脖子深深地缩进大衣领子里。她没有害怕,在黑暗中与大海靠得那么近,这让她感到不自在,可是,她不害怕。
现在,她已经到了加布里埃尔塔,接下来,要找到一块黄石头。
山路已经消失在她身后,泥土小路坡度舒缓地伸向海岸边的陡坡。
一道闪亮的圆弧突然出现在路的尽头,它咆哮着摔成碎片,泡沫在礁石上飞溅。海水静止了一个瞬间后就向后退去,像是一根巨大的舌头,刚尝过了这块土地的味道。微微的天光反射在上面,鳞光闪动。
玛丽咏站在世界的边沿,头发被寒风吹得乱飞。
她不后悔自己下山来到这里,这样的气氛值得体验。
“一块黄石头,只要找到黄石头,看看这个游戏到底要把我引向哪里。”
她一步一步向前,搜寻地面,辨认地上仅有的几处浅色痕迹。
她很快就走过圆塔,离海越来越近。现在,她在海面之上不到一米。
海水不停波动着,摔打在岸边陡坡上,发出巨响。玛丽咏尽量离它远些,一不小心,就被喷了一身大海的唾沫星子。
不见黄石头的一点影子。
除非它只有一丁点儿大,藏在灌木丛里,她没有电筒,根本找不到。
玛丽咏走到小路尽头,前面就是敞开着的海的王国。
黄石头……黄石头……得知道它到底指什么!
她掉转头,重新朝着圆塔向上走。
有许多白乎乎的点子布满了泥地。
一块更大、颜色更深的光晕紧靠着加布里埃尔塔的石墙,那是一块礁石,很可能是黄色。
玛丽咏向后扳动礁石,很沉。
石头滚到一边,喀喳声被波涛声吞没。
玛丽咏一把抓住露出来的信封,不让它飞走。
上面没有一个字。
她把信封塞进衣袋里。
在她的上方传来呼哨声。
起初很轻,接着,越来越响。有什么东西开始拼命地吸气,好像是一头气喘吁吁的巨大怪物。
玛丽咏观察着圆塔和塔顶,喘气声好像是从那儿传来。这时,声音被淹没了。
最后几个音符被一阵水声吞没,就像有道阀门突然关住了水流。
顿时,气流发出猛烈的撞击声,比雷声更干脆,回声更大。玛丽咏惊吓地一跳。
回声在塔内回荡。看到海水退去,玛丽咏才明白,塔的脚下有许多长长的开口,很像水平的枪眼。巨大的海浪有时从这里钻进塔内,拍打着塔的内部结构。在退潮时,海水吸住空气,发出悠长的呼哨声。
玛丽咏看够了,冷气开始侵入她的身体。如果到目前为止,她还只不过是感到不自在的话,现在,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开始忐忑不安。
正当她重新走在修道院巡查道上时,第一次看到一条人影。
这条人影就在下面,在邻近的一条小巷子里,她处在高处,距离人影几米远。她才注意到有个人在那儿,那人无疑也发现了她,因为他不时停下脚步,抬头朝着她这个方向张望。可惜他离得太远,玛丽咏看不清。
玛丽咏加紧步伐,时间还不晚,但风实在太大,人们都不敢出门,暴风雨正在逼近,这已经没什么好怀疑的了。可是,出现这样个人物,让她心神不宁。
这条人影被狂风推着,前进得很快,并且继续窥视着玛丽咏。
玛丽咏不想与任何人打照面,更何况还是个陌生人。不,现在不行。
她下了第一层台阶,又飞速奔下第二层。通道狭窄,先是在两幢空房子间向右转,然后左转,接着又转了个弯,又是台阶,玛丽咏真是疾步而下。
她的耳朵里发痛,暴风雨来临前的大风一阵紧接着一阵,吹个不停。
她终于来到小街上,她的小街,风减小了。
她在阴暗的巷子里跨过最后几步。
这时她骤然止住脚步,停在一堆意外路障之前。
他在那儿。
就在她面前。
无声之中,一道光唰地亮了,直直照着玛丽咏的脸,她向后退了一步,用手臂遮住眼睛。
“嗨!”她抗议道。
对方没有反应。
玛丽咏仅仅得空看到陌生人比她高出很多,长得很魁梧。
“请你把电筒放下!”她叫道,“我的眼睛都被你刺瞎了。”
她看不见他,只听到他在移动,鞋子在砖块地上发出嘎吱声。
“嗨!我和你说话呢!”
电筒熄灭了。
“我不认识你,你是谁?”一个带着浓重北方口音的男人问道。
“对不起?你是在开我玩笑吧?是你用手电筒光照我。”
“那是我的工作,我的小夫人。我是守夜人,你呢?”
玛丽咏略微放松了些。她感觉到背部一轻,自己原来比想象的更紧张。
“我是……受修士和修女的邀请,到……”
“我猜得不错,你和兄弟会在一起。看见你的面孔陌生,我就猜想到了。加埃尔,加埃尔修士通知我,他们要接待一个夫人冬天在这里隐居。很抱歉,让你受惊了。”
玛丽咏很生气,有人竟然说她要在这儿度过整个冬天。
“算了,别再提了,”她说道,“我叫玛丽咏。”
“我是路德威格。”
他竖起电筒对着自己的脸,按亮电筒,展示了下自己。
“这样,从现在起,你就认识我了。”他咯咯地笑道。
他确实长得很高,起码有一米九十厘米,有点胖,圆脸颊,嘴边一圈大胡子。他的眼睛和他的短发一样黑。三十多岁,玛丽咏估摸道。
“你不该呆在外面,暴风雨就要来了,”他提醒她道,“马上就要砸下来了,厉害得很。”
“我正要回家,我刚去散了会儿步。”
“是吧,成,别拖拖拉拉的了,我这就结束巡夜回隐蔽所。街上就不会有人了。”
玛丽咏指指他身后的那条街:“我住在那儿……”
“哦。对不住……”
他侧身让她过去。
“好吧,如果你和我们一起过冬,我们有机会互相认识。晚安,夫人。”
她表示赞同,然后,心情不无愉快地找到自己的家门。
他嘴里的“夫人”一词让她不悦,过于强调。他自己有几岁?比她小五六岁?他称她“夫人”时,好像两人之间隔了一个世界,好像她……很老。
多疑。
就是多疑,那又怎样呢?
她反锁上门,打开门口的吸顶灯。
她怎么会就这样出去的呢?
她把手插进衣袋,取出信封。
她轻轻摇了摇头,对自己的态度感到厌烦。
她把信封放在花几上。
07
拂晓是灰色的。
喧闹的。
暴风雨在晚上第一次袭来,玛丽咏被惊醒了好几次。眼下,是这次袭击的尾声,连续不断的风吹打着墙壁,把整个海湾变成一大片煤烟色的天,没人能够分辨,哪里是海,哪里是空气。
玛丽咏渐渐睁开眼睛。
床头柜上,一张乳白色的纸展开着,很好的纸张,高雅的笔迹留下这几个字:
“衷心祝贺。
祝贺你,欢迎你。”
纸上留着揉皱的痕迹,那是昨晚,玛丽咏在一气之下揉的。睡觉前,她还是打开了信封。
她八点钟不到时起床,走下楼,身上穿着从一家漂亮的伦敦饭店里“借来”的浴衣,那是一次国际法医研讨会,她陪同巴黎法医研究所所长一起前往。有人从信箱缝里塞进一张纸条,纸条滑落在门口的地砖上。玛丽咏叹着气,捡起纸条。
既不是无聊的谜语,也不是匿名信,真是幸运。
这一次,没有令人费解的句子,安娜修女在纸上解释道,她今天一天在修道院僧院,玛丽咏可以在那儿找到她。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僧侣们都不进食,所以她得独自一人吃饭。安娜修女最后写道,希望暴风雨没有过分打扰她的睡眠。
玛丽咏扬起眉毛,纸条落到地上。
她睡眼惺忪,打开冰箱,找到一瓶橙汁。她吃着饼干,坐在沙发上,漫不经心地看着窗户外的屋顶。
今天,她没有兴致和修士修女们呆在一起,更没有兴致去听关于耶稣、上帝、教会或宗教的长篇大论。她向往的是真正的安宁,个人的安宁。
她洗了个淋浴,穿上一条牛仔裤、一件粗羊毛衫,然后给修道院僧院打电话,电话号码就在电话机旁的一张名单上。她向安娜修女解释说,她希望独自一人呆着,然后挂断了电话,一字不提昨夜的谜语,更没有说到她的外出。事情会水落石出,或者,永远不会。
结果,这一天过得比她想象的更快。
早晨,她顶着仍然剧烈的海风在镇子里的格朗德街上闲逛。
除了普拉妈妈餐馆,只有一家小店开着门。仅有的几个冬季旅游者,听到暴风雨预告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街上只有玛丽咏一人。
当她走进纪念品商店时,女老板向她绽露出世界上最美的笑容,并请求她买一张明信片,说这样她就没有白开门。很快地,两人就互相产生好感,喝着咖啡,交起朋友。女老板叫贝阿特利斯,四十四岁,和十八岁的儿子格莱格瓦一起生活在圣米歇尔山上。一个漂亮女人,玛丽咏脑中不时闪过这个念头,她有一头红色垂肩直发,鼻粱纤细,颧骨突出,被单身流放在这个世界的尽头,真是可惜。有吸引力的男人在这里不会很多,只有那几个熟面孔。如果她没有技到合脚的鞋……
贝阿特利斯没多磨蹭就向玛丽咏透露,她已经离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