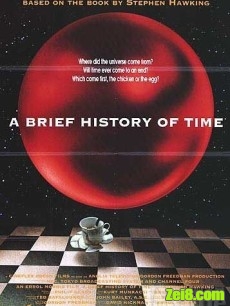时间的血-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你已经回来了!”达勉修士惊讶地说,一边把雨伞搁在门口,“好大的干劲,真是该好好表扬啊!”
玛丽咏真想反驳他,她可不是十六岁的小丫头,那是二十年前。
可是,她忍住了,况且,自己刚才还真露出了孩子样。
他们又开始了下午的工作。雨下个不停。
将近十七点时,达勉修士提醒她,他们一会儿就要回去,玛丽咏不出声地走到外语书籍的书架前。
那本黑脊书就在最上面。
确定修士看不见她,她取下书。
书消失在她的毛衣里。
“你干吗拿着它?”贝阿特利斯问道,嘴里吐出口烟。
“我也不知道。我想,是好奇吧。”
“是什么?一本旧日记?”
“好像是。1928年,是用英语记的。写的人当时住在开罗。”
“一个英国殖民者。我不明白,你手上的这本日记,它是怎么会落到阿弗朗西的?”
玛丽咏吞下一口咖啡。
“我有一个想法。”
“你还没读过呢!”
“这本日记是圣米歇尔山修道院在1945年或1946年捐赠书籍中的一本。有可能,当时的修士们在战争中接待过一名英国士兵,英国士兵或者是死了,或者留给了他们这本日记。修士们把这本日记与图书室的其他外语书放在一起’,法国解放后,或许是修道院为了腾出地方,把这些书都捐赠给了阿弗朗西市。”
“我不信。1928年,离二战发生还很遥远。我想象不出,你的英国士兵口袋里揣着本日记,晃荡了十几年!”
“这不过是一个想法而已……”
离她们几米远的地方,格莱格瓦手里捧着本杂志,躺在沙发上,这时他直起身。
“真没劲!妈,我出去逛逛,我要到蓬多松去。”
他伸了个懒腰,身上关节被拉得喀喀响,还毫不遮拦地打着哈欠。
“帅哥儿。”玛丽咏第一次看见他,心里自语。他虽然已经满十八岁,脸颊上还是婴儿般的皮肤,又红又嫩。板刷式头发没有经过整理,一丛一丛,乱七八糟地竖在头顶上。一颗钻石在耳朵上闪耀。
“别回来太晚。”
“行。”他套上件皮夹克,走出去,手里握着汽车钥匙。
沉默了一会儿,玛丽咏指着门外他消失的地方说:“生活在这里,对他来讲,该不太容易,离陆地和朋友都那么远。”
“格莱格喜欢独来独往,不过,的确,这里不是天堂。早晚他要到陆地上生活。”
“为什么这里不是天堂?你嘴里的圣米歇尔山好像是一个岛。”
“这儿就是个岛,最起码,在这儿的居民脑子里就是这么想的。
你以后感觉得到,真正的岛民心态!大家团结一致,一起忍受打击,如果有必要,大家会保守同一个秘密,一个不该离开圣米歇尔山的秘密。”
玛丽咏盯着她对面这个朋友的眼睛。
“你干吗这么说?”
贝阿特利斯耸了耸肩。
“因为,这是真的。人家说,岛民生活在陆地的边缘,生活很特别,确实就是这样。而且,这里小得只有一点点,我们一共就没几个人,又有很多旅游者。你想象一下,住在杰西岛上的人!”
“听你说起来,就好像你曾经经历过真正的岛上生活,我没猜错吧?”
贝阿特利斯作了个鬼脸。
“我出生在贝拉岛。相信我,这是种精神状态。”
贝阿特利斯从餐桌边站起身,打开吸顶灯。
“你今晚不和兄弟会的修士们一起晚餐?”她打听道。
“不,达勉修士告诉我,星期一是独处日。他是特例,出来上班,其他人都不离开他们的僧房。”
“这种生活!”
“还算好,自从我到了这儿,他们作了不少努力,尤其是就餐,他们平时吃饭时或者保持沉默,或者朗读《圣经》……”
玛丽咏啪地拍了一下黑皮书的封面。
“好了,我回去啦。”
“你不在这儿吃饭?”
“不,我已经打扰你很久,而且,我还有东西要读呢,”玛丽咏把日记举在面前,“在把它放回去以前,我还要满足一下好奇心。”
几分钟过后,玛丽咏沿着格朗德街朝小教堂攀登,手臂下夹着书,两只手插在口袋里,惬意地感受着脸上的一层潮湿水雾。
“又在散步呢?”背后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
她转过身,发现是守夜人路德威格,以他一米九十的身材从上向下地打量她。
“不,这一次,我是回家。”
“真是抱歉,上一次晚上吓着你了。”
玛丽咏摇摇头。他的北方口音很重,她觉得很有趣。他的特殊口音透露着友善。
是你自己在这么胡想,就因为他的表达方法不一样,其实不过如此……
“其实,”他接着说道,“如果,你哪一天晚上要找我的话,我就住在最下面,镇口的广场上,屋门总是开着。如果我正在巡夜,你可以打我的手机,这是手机号码。”
他递给她一张预先准备好的卡片。
“谢谢,路德威格。那么,祝你晚安,巡夜顺利。”
玛丽咏低下头走开。她没心思聊天。她回到自己的家,烧热平底锅,正准备投进去一块鸡脯肉和一点鲜奶油,有人敲门。
“真是的……”她咕哝道。
达勉修士站在门前。
“晚上好,很抱歉打扰你。我不会多耽搁。我来是为了告诉你,明天九点钟来接你。拿着,这是给你的。”
他递给她一盒夏纳克司,一种镇静剂。
“安娜修女想你有可能会需要这,当前的情况……而且,晚上风大……反正,这个能帮你入睡。”
玛丽咏一边感谢,一边接下盒子。
她注意到修士的眼神,他的目光似乎被她背后的什么东西抓住了。玛丽咏记起,自己把偷偷拿来的书放在了门口的花几上,花几就在她身后。
“我不再打搅,总之,我不该在这儿。今天是星期一,是独处日,祝你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明天早上见。”
如果他认出了书,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他却没有向她挑明。
“晚安,达勉修士。”
她关上门,把药盒扔在花几上,就在黑皮书边上。
饱餐一顿之后,她来到客厅,打开音响,放了些音乐,屋子里似乎添了些生机。然后,玛丽咏深埋在转角沙发里,舒服地坐好后,打开日记。扉页上用英语写着:
“工作日记,杰瑞米·麦特森,1928年3月——”
她翻到下一页。
“March ,11th,I decided to…”
玛丽咏眨了眨眼,她的英语很好,只要回忆起那些生疏了的词汇就行。
“3月11日。
“我决定拿起笔。我不是在靠倾诉心事来解脱灵魂,也不是在逐日记录我的存在。破天荒第一次,我要记述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这些天,我被它牢牢套住。
“如果可以把这些文字看做是练习的话,那纯粹是尝试性的。
起初,一种强烈的愿望促使我把经历的这些日子用文字记录下来,现在,我自己也还不知道它的结尾,如果真有结尾的话。我会尽量把全部事实一点不漏地记录下来,不受个人经验、情绪波动和主观解释所影响。这本日记就是我的故事。
“这个鬼气森森的故事,从此让我梦牵魂萦。”
玛丽咏抬眼一看,整个客厅里,只有她身边的那盏灯亮着,屋子的其他角落都沉浸在黑暗中。
她喜欢这种安静的气氛。又接着往下读。
“First of all, 1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作自我介绍,我叫杰瑞米·麦特森。正式地说,我是‘为尊敬的乔治五世的大英王国效力’的侦探,被派驻在大英的殖民地之一:埃及。更确切地说,开罗。我今年三十三岁……”
杰瑞米·麦特森的故事就这样开场了。只读了寥寥几句,玛丽咏已经完全投入到故事中。
想象力借助着日记的描绘,她沉浸到这个消失的世界里……
09
杰瑞米·麦特森擦去染在食指上的墨水痕迹,又接着往下写。
一盏汽油灯正在燃烧,就在写字桌的上方,吊在火车厢的一根横梁上。
房门口,地毯上布满了琥珀色的纹路,沙粒聚拢在一起,构成了闪亮的大理石状条纹。脱鞋之前,他习惯先在门口这个地方抖晃一下双脚,所以造就了这个沙洲,仿佛专门是在那儿殷勤迎客。
门边挂着支一米高的气温表,表上的华氏度指示出炎热高温,而夜色已经降临。
随着视线探进车厢的深处,光线渐渐变弱,似乎不愿透露杰瑞米·麦特森隐秘的私生活。
汽油灯的火光反射在优质材料上,忽明忽暗。涂了清漆的木器虽然陈旧,却很牢固,挂在墙上的丝绒依旧柔软。
在门的那边,比他正伏案工作的大写字桌更远些,是两张裂了缝的皮沙发椅,面对面放着,中间隔着一张木条镶嵌的矮茶几。连日来,这些家具仿佛在火盆中烤炙着。沙发椅上有两张揉皱的纸,打字机打印的字迹,开罗警察局的抬头。酷热把纸张也变得暖乎乎的。纸边,露出几张照片。
黑白照片。
第一张上面划了一道红墨水杠子,就像是遭到了否决。
照片上可以看见一堵白墙,一个穿西装套服的男子,无法辨认他的样子,因为他的头歪着,嘴角的口水一直垂到地上,就像是一张正在编织的蜘蛛网。
照片的左部,看得见墙上开出一条阴暗的小道。阴影过于浓厚,隐约可见一圈人影围着地上的一团东西。
第二张照片是个特写,一只稻草编的娃娃,做得很粗糙,部分已经磨损,仿佛拿捏不小心的话,立刻就会散架的样子。
娃娃身上笨拙地画着一条裙子。
是画,或者是污迹。
深色,潮湿。
第三张照的是穿皮鞋的脚,西方人的皮鞋,擦得油亮,尽管上面已经落了层薄薄的灰尘。穿皮鞋的脚围着地上放的一堆东西。照片上是好几个站着的男人,因为照片框架有限,只照到他们小腿的高度。
相机镜头对准的是一只胖胖的小胳膊,摊在泥地上。
手心半开。
皮肤光滑,年龄不该很大。
手腕上是与草娃娃身上一样的深色黏稠的污迹。
还有十多张照片,堆在一起,都面朝着沙发椅皮面。
汽油灯的光线只照到沙发为止,更远些的地方就全在暗处,那儿,空间狭小,是浴室的门口。右边,一条通道,通向卧室。
一面大穿衣镜反射着远处对角,给这个房间带来纵深感。梳妆台上铺满了画报;梳妆台对面,堆满衣服的扶手椅边上,是一张大床,床单皱巴巴的。床脚下,一只木雕碗被打翻在地毯上,烟蒂和烟灰洒了一地。
一张女子的照片装饰着床头柜。尽管夜色清朗,有光线从两扇圆窗透进来,女子的面容仍然看不真切。
车厢的另一头,铸铁灶头上的一把水壶呜叫起来。
杰瑞米站起身,拿了一块脏抹布,拎起茶壶,倒了一杯茶。干薄荷叶很快散发出宜人的清香,飘满了整个客厅。
杰瑞米品尝了一口滚烫的茶,仰身靠在椅子里。他破例没有脱去靴子,两只脚就像是在里面溶化了一样。
他一直穿着那件有很多口袋的衬衣,不过,前胸敞开着。胡子不曾刮过,今天早晨他没有空。这个样子很合适他,胡子遮住了过于深陷的脸颊,缓和了过于肉感的嘴唇。
杰瑞米的手掠过脸庞。
鹰勾鼻尖,窄鼻梁。
乌黑的双眉。
宽阔的前额,透出古铜色的光晕,一头黑发,整齐地向后梳理。
当女人们在俱乐部前的阳台上一边啜着阿拉伯饮料,一边聊天时,她们常说到杰瑞米·麦特森,说他“让人无比渴望”。
非洲式的野性和英国式的优雅在同一个男人身上融为一体。
有谁不知道,他既是侦探,又是出色的猎手,到过南部荒蛮地区狩猎。
有谁不知道,没有一个开罗的女人可以自吹曾经与杰瑞米·麦特森同床共衾。
人们私下里嘀咕,他是个专一的人。
人们私下里嘀咕,他很神秘。
传言很多……
玻璃杯放在桌上,发出“铛”的响声。杰瑞米·麦特森打了个响指,他的手指颀长有力,是那种让开罗城里的西方社交界夫人们青睐的手指。他打开火车厢门。
三级台阶通向一块挡雨棚下的空间,挡雨棚支在车厢壁上。一块毯子铺在沙子上,几张躺椅,一根木杆,几只装器材和食物储备的箱子,上面贴着“军用物资”的标签。
杰瑞米漫不经心地拖开一张椅子,走出来在帐篷前坐下。
暮色降临,阳光变得温和,天没那么热了。还要过一两个小时,车厢里面才会凉快下来。
眼前,铁轨编织出一幅他喜爱的图景,密密麻麻的蚯蚓在月光下向远方蠕动,仿佛象征着人生的错综复杂。
下方,在铁路博物馆的后面,在橙黄色石头的巨口之下,在中央火车站的圆顶下,蠢动着钢铁长蛇和几名乘客。
就在离杰瑞米·麦特森住的火车厢一百米远的地方,一辆有轨电车摇摇晃晃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