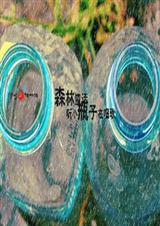白衣侠-第1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燕子翔忽然心生怯意。
他是名家之后,见过世面,知道遇上了硬手。
这青年人一字字地道:“把你刚刚吐在地上的唾沫舔起来,滚出‘瑶台’勾栏院,如果要我动手,你会更难堪!”
燕子翔拔剑攻上,这人也抽刀接招。
不到五招,燕子翔就知道今天这个脸可丢大了。
他在此处摔死了人,也打伤了很多人,万一被制住,可能被毒打一顿,如果是仇人,也可能丢掉生命。
最后就算能保住小命,只怕也要包赔损失。
十招后就落了下风,他估计接不下此人三、四十招。
这是什么人?为什么从未见过?燕子翔道:“你是什么人?”
“你还不配与闻!”
燕子翔力攻三剑,一个“鲤鱼倒穿波”就上了墙头。
再一跳,就在墙外了,逃出镇外,正在喘一口气,忽见林中走出—人,竟是刚才那个青年人。
燕子翔道:“你真以为我怕你?”
“希望不是!”
“你不敢报上名来?”
“南宫政!没听说过是不是?”
“的确,我劝你还是为自己留点余地!”
“你如果知道做事要留余地,也就不会在勾栏中杀人了!”
“你可知我的身份?”
“呸!不过是一个过气的帮主之子而已!”
“过气帮主之子,比你这无名小卒又如何?”
“我这无名小卒能在三十招之内把你摆平!”
“少吹……”燕子翔明知不是吹嘘,只是因为没听说这号人物,仍以为是自己没有全力以赴之故。
这一次他尽了全力,也用了最得意的招式,只不过在三十招内,仍被击落了兵刃,继而被制住了穴道。
燕子翔躺在干硬的地上,仍似未产生真实感。
“这小子真具有击倒我燕子翔的实力吗?”他闭上眼,内心仍恨父母,没有教他好的武功。
“说!你为什么要迫害勾栏中的—些可怜虫?”
“你说她们可怜?”
“怎么?你以为她们不可怜?”
“裤子一脱,大把的银子就来了,天下哪有这么轻松的行业!”
南宫政一愣,道:“听你的口气,颇为羡慕这一行对不?”
“倒也不是羡慕,总以为她们赚钱太容易!”
“错!她们赚钱太难了,至少在下海时曾经过人格和自尊的鞭策。好!你以为这一行赚钱容易,我就成全你。”
“你要如何处置我?”
“不会让你失望的,但你干这一行,则不需要武功……”闪电出手,连拍十余下,燕子翔满地翻滚,哀号不已。
他的武功已经失去,刚才还抱怨道,那点武功太不管用,现在他多么重视那“一点点”的武功。
口
口
口
“后庭花”相公堂子门庭若市,难然大多数人对这一行及势中这一行的人万分蔑视,似也不妨碍他们的存在。
有些人硬是喜欢这个调调儿。
其实藐视这一行的人,主要是勾栏的窑姐,她们最瞧不起这些和女人抢生意的“大丈夫”。她们如果知道某一嫖客光顾过相公堂子,她们拒绝接待。理由很简单,他们是逐臭之夫,钻过粪坑。
燕子翔人品俊逸,个子又不甚高大,打扮成女的,还真抢去了“后庭花”原有相公的光采,不久就被誉为“花魁”了。
这种侮辱男性的行业,最初由“狎优”而起,“优”就是当时的“娼、隶、优、辛”四大贱民之一的戏子。“狎优”就是玩戏子,那时唱花旦的多是面目姣好的男童,极像女人,故称之为“像
X”,以后叫白了称之为“相公”,也许另有原因,但迄无较合理解释。
现在“后庭花’也正在选“花榜”,龟奴到处张贴“花榜”,更绝的是,为了宣传以广招徕,还叫榜首的状元、榜眼、探花及传
X四名乘轿游街。燕子翔就坐在最前面的一乘彩轿中。
推动这“花榜”盛举最有力的,正是进他来此的南宫政,他出钱出力,终于办成了这件事。
南宫政为什么如此热心作这件无聊的事呢?这当然是有原因的,表面上却仅是惩罚燕子翔残害勾栏中的妓女。
四乘彩轿由一些无聊的人拥护着来到通衢大道上,人太多,轿子无法通行,只好暂时停下来。于是有人大叫,请四位“新贵”出轿一瞻丰采。
真正是一呼百诺,大家齐声赞成,盛情难却。
相公堂子方面的负责人自然愿意,难得有这机会让相公翻公开亮相。
于是在千呼万唤之下,四位相公出轿了。
最后出轿的自然是燕子翔了,一身的绫罗绸缎,浓装艳丽,花容月貌,立刻造成了轰动。
甚至有些登徒子想近前去摸他一把。
燕子翔羞怯地游目四方,突然他的目光与一位观众的两道目光一接,立刻低下头去。燕子翔一直轻视他的母亲,而现在他居然不敢正视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现在的打扮不堪入目。
只不过母子关系毕竟非同小可,况且他落到这地步,一直孤立无援,如今看到了亲人倍增亲切。
甚至他在那一瞥之间,发现母亲目蕴泪光。
于是他再次抬头望去,母亲已不在原先那位置了。
他四下打量,不见了母亲。是了,他以前对他的母亲太绝了,他的母亲寒了心,况且在这场面上,也无法援手。
燕子翔正自失望之际,耳边忽然传来了细微之声,道:“子翔,我在你身后,今夜我去救你……”
燕于翔似乎想流泪,但他忍住了。
口
口
口
晚上,他没有接客,大约三更稍过,燕雨丝就出现了。
他目前是挂头牌的红相公,—人独住一院。
燕雨丝出现时,燕子翔的心情是很难形容,他恨母亲的走调,也恨自己的不争气。
他没有说半句话,就被燕雨丝救出,来到镇外七八里外在林中放下他,燕雨丝喘着,道:“子翔,怎公会这样?”
“天生下贱……。”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你如果是来糗我的,你自管请便!”
“怎么会?”
“那就不必问!”
“我是希望知道,会不会有人强迫你?况且你的武功已废,总不会自己废了自己的武功吧!”
“是一个名叫南宫政的青年人……。”
“他为什么要废你的武功?”
“因为我在一家勾栏中闹事,杀了一个人。”
“这就是了!要不,那个南宫政绝对不会如此狠毒。”
“你是来讽刺我的?”
“子翔,人总要检讨自己的过去。”
“你的过去就光彩吗?”
燕雨丝本想拂袖而去,可是她也不能不认自己过去的走调,虽然儿子不该如此对待她。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道:“子翔,娘并没有否认自己做错了事,但作子女的,最好先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再责备父母,尽管娘并不迷信‘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那句话。”
“你救了我,我会记住这笔帐,我走了……。”
燕雨丝对这个长子真看穿了,只不过检讨自己,确有不是之处,子女为她的行为抬不起头来。
“子翔,我想试试看,还能不能为你恢复武功?”
“已经三个多月了!还行吗?”
“事在人为,试试看吧!”
燕子翔虽然仍对母亲存有芥蒂,但武功太重要了,如他未失去武功,又怎会在“后庭花”受这种罪?
在燕雨丝的居处,她为他恢复功力。
她知道,以她目前的功力,为儿子复功有点不自量力,但冒这份险是值得的。如果为了儿子而中途死亡,她以为也死得其所。
一天一夜,几乎是死去活来,她终于达到了目的。
她这么做,主要是在儿子面前赎罪。
绝对末想到,燕子翔功力恢复,打坐调息三个时辰之后,一跃而起,的确和以前一样了。大喜过望,是绝对意外的事。但是,望着一边打坐行功,—头虚汗,面无血色的母亲,却没有感激涕零的感受。他以为这是她该付出的,他对她的冷漠却仍是她罪有应得的,他居然未等母亲行功完毕就自行离去了。
燕雨丝睁眼看着儿子不辞而别,刹那间她失去了求生的欲望。
一股急气打心底升起,她的心神—松,忽然倒了下去,口鼻中大量流血。哀莫大于心死,她不想活了,就运功使“血不归府”,如果不遏止而大量失血,不须半个时辰,必然不治。
就在这时,两条人影无声无息地飘在帘内。
二人向床上看了一会,女的立刻把燕雨丝扶起。
二人都蒙了面,如果燕雨丝不昏迷,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是谁了。两人打个手势,女的在前,双手按在燕甬丝的胸前,男的在后,双手贴在她的背上。
不一会,燕雨丝浑身冒着腾腾蒸气,气色已经好转。
不一会,燕雨丝隐隐感觉四只手由她的前胸与背后收了回去,浑身有无比的舒畅之感。
睁眼一看,一男一女两个蒙面人站在床前。
她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该不该感激他们?或者是否还要继续恨他们?至少他们的表现比儿子燕子翔有人情味多了。
她又闭上眼,颊上淌下两行清泪。
稍后,她再睁眼,两个蒙面人已经走了,不由掩面而泣。儿子如此绝情,女儿失踪,迄无下落,丈夫救了她,却在别的女人身边。
家庭破碎,前途茫茫,人生乏味。
只不过想起燕雁和燕子飞,她又不想死了,她还有责任未了。
口
口
口
胡大舌头和小唐都化装易容。胡大舌头嘴角上有一撮毛,小唐留了短的胡子,眉毛甚浓,不是至亲的人,绝对认不出他们。
这大镇上突然来了百十个乞丐,其实是“逃荒”的人,附近三个县大旱,七个月没有下雨。
人们填不饱肚子,只有离乡背井了。
“唐少侠,百万人‘嗷嗷’待哺,咱们也该尽点力。”
“尽点力?有什么办法?”
“弄钱赈灾。”
“咱们不偷不抢,如何弄钱?”
胡大舌头道:“你的赌技如何?”
“牌九和骰子还凑合。”
“跟谁学的?”
“好像是马大风阿姨!”
“咱们只要合作,保证大有收获。”
“诈赌?”
胡大舌头道:“唐大少,何必说得那么难听!玩点花稍而已,再说,我选的这家赌场和‘人间天上’的江欢有点关连。”
“人间天上’?”
“怎么?连‘人间天上’也不记得了?他们以前的帮主就是谭起风,现在是江欢哪!江荪是江欢的孙女,而江荪上次要占你的便宜,不是我代你解围的?”
“是有这么回事!”
胡大舌头道:“江欢主持‘人间天上’,食指浩繁,他们要开销,当然要广开财源,就在吃喝嫖赌这些方面敛财。”
“他们开赌场?”
“当然,这镇上就有一家,他们还开了多家勾栏,那家‘后庭花’相公堂子,就是江荪的表哥南宫政开的。”
“南宫政?怎么没听过这名字?”
“以前在西北,刚来中原不久,也是江欢招兵买马,广召志同道合的心腹人才,南宫政自是适当人选了。”
“武功很高?”
“当然,听说不在谈天仪之下。”
“我们要到江欢的赌场去。”
“对,弄他们的钱,去救灾民。当然,咱们自己也需要开销……”教了些手法及花稍给小唐。
这家大发赌场已有七、八年的历史,经常门庭若市,即使在最淡的季节,也是川流不息,自有其原因在。
他们会发动部下,拉拢赌客,如不捧场,可能会有些麻烦,赌客们惹不起,反正到哪里都是赌,何不作个顺水人情。
这儿是个四合院,牌九,骰子、红黑实、麻将、十三张等样样都有。
胡大舌头事前试过,小唐的骰子和牌九这方面的技巧,比一般赌徒精练多多。就凭这份精练,以胡大舌头自己的“技术”,大概可以玩点名堂出来。他们不是一起进入赌场,也不是一起来到这一桌抬面最大的豪华赌局前的。
定桌上的赌注,毛估一下,大约有三四万两之谱。
当然,这还不能算是最大的赌局。
正好这时庄家通赌了两次,赌资不足,把位子让出,胡大舌头一屁股就坐了下去。
“天门”的中年赌徒看看这个三十左右,嘴边长了一撮毛的家伙,衣著是够光鲜,要说作庄嘛,似乎不大够份量,道:“老弟,作庄嘛!总在有三五万两的赌资吧!”
“这是当然!”
“请亮一下好吗?”
胡大舌头掏出一张银票,上面是“凭票祈付肆万九干七百两整”字样。大德通的票子全国通用,铁票。
这票子很唬人,“出门”和“末门”也看到了。
这工夫“出门”也出了局,小唐坐下来。
他的记忆失去,并不是任何事都忘了。
如果任何事都忘了,武功也会忘记的,但他的武功未忘,赌也未忘。他只是忘了一小部份,也就是被重击之前那一段短时间内的事物。
胡大舌头洗了牌,砌好,把两枚骰子字到面前,道:“下注,下注!鸡零狗碎地免上……。”
“出门”背后有个瘦子三十五、六,一看就是个内外兼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