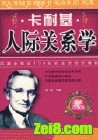亲密关系的变革-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信中反复提及。与斯托普斯通讯的许多男人谨慎地指出,他们不是弱小男人,而是“高大健壮”,“体格超过一般”,“结实,强壮,身体非常健康”,等等。
由于缺乏性知识而引起的焦虑是一个恒定主题,正如长期的自卑和困惑情感一样。不能引起对方的性反馈是常见的一种抱怨,但男人缺乏快感也同样如此。一个人曾这样说:“我们两人从来没有感到最紧密拥抱时的那种满足,本能和理性告诉我情况应该如此。”莱斯利·霍尔:《隐蔽的焦虑,男性性征,1900~1950》,第121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斯托普斯的大多数信访者所产生的性忧虑或是集中在性交失败上,或是集中在不能正常性交的担忧上。缺乏“阳刚之气”威胁到男女之间的宝贵关系,而不是抽象问题。
尽管我不想详尽讨论这些问题,但前面的分析有助于说明大众色情文学的一些特征和男性性暴力的一些重要方面。色情文学可以视作性的商品化,但这种观点是非常偏激的。当下色情读物的大爆炸基本上是指向男人的,大部分只供男人消费,而在形式上则与低调情感和高密度性活动的流行做法相并行。异性色情文学表明了对标准化场面和姿势的偏执式关注,其中,在实际的社会世界上本质上被消解了的妇女的共谋又得以明确的重申。安迪·摩耶:《色情文学》,载麦特卡尔夫和亨弗利:《男人的性征》。软色情杂志里妇女的形象——通过插入正统的广告、非色情故事和新闻而被标准化了的形象——都成为欲望的对象,但从来不是爱的对象。她们使人激动,激发性欲,但从本质上说是偶发的。
女性的共谋都被风格化了,因此,妇女通常都受到这种风格化的描写。软色情文学的“体面”是其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向人们暗示妇女是性欲望的客体,而非主体。色情杂志的视觉内容把女性性征中性化了,对?密关系的威胁被消解了。通常情况下,妇女的目光凝视着读者;在此,阴茎再次成为阳物,这是男人能够向女人施加的无上权力。有些色情杂志开辟专栏供读者商讨性问题。但这种期刊登载的大部分信件迥异于斯托普斯收集的信件。与以问题为指向的信件相对照,这些信件主要记叙勇敢的性行为;但也同样是分散的偶发的插曲。
在这些偶发插曲中有一个流行主题,即性快感,实际上不是男人的性快感,而是女人的性快感,而且往往是以特定方式表现的。这些故事讲述性交中进入极乐境界的女人,但她们总是受阳物的摆布。女人抽泣、喘气、颤抖,但男人则沉默无声,精心安排着即将过去的事件。女性快感的表达得到了细腻的描写,远远超过对男性经验的描写。女人的销魂状态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些故事的主旨并不在于理解女性性快感的源泉和性质,或产生移情作用,而恰恰在于驯服和孤立女性性快感。安迪·摩耶:《色情文学》,第68~69页;载麦特卡尔夫和亨弗利:《男人的性征》。事件是根据女性的反应来描写的,但是,这样就把女性欲望变成与男性欲望一样是偶发的了。于是,男人开始了解女人需要什么,并如何根据自己的条件应付女性欲望。
色情文学由于其替代性质是很容易使人上瘾的。女人的共谋被肯定,但色情再现无法阻止男性性征的矛盾因素。女性表现的性快感带有一个价格标签——因为能够为这种疯狂状态提供证据的人也可以认为是强行提出必须满足的许多要求的人。失败并不公开表现出来,而作为未予言表的欲望前提潜伏起来;对女人的愤怒、谴责和敬畏无疑与这些故事表露的忠诚融为一体。软色情文学的标准化效果也许说明了它之所以受大众欢迎的原因,而非这样一个事实,即更明显的色情读物在市场上并非唾手可得。至少就其某些表达方式而言,硬色情文学可能更具威胁性,尽管其公开性似乎更迎合男性的“渴求”。在此,权力不再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女人共谋的凝视——而似乎更加开放、直接和武力施行。当然,对一些人来说,这正是其吸引人的地方。然而,硬色情文学也在阳物性征的外围运作,在另一端揭示可塑性性征危险的放荡不羁。
男性性暴力
武力和暴力是所有统治秩序的组成部分。在正统的政治领域,问题在于权力达到了何种程度的霸权地步,这样,当合法秩序垮台时就只能诉诸于暴力,或从另一个角度看,暴力表现了国家权力的本性。在有关色情文学和性暴力的文献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论。有些人认为,硬色情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在暴力得到直接再现的地方,描写了作为整体的男性性征的内在真实。安德列·德沃金:《色情文学:占有女人的男人》,妇女出版社,伦敦,1981。人们进而指出,对女人施加的暴力,尤其是强奸,是男人控制女人的主要工具。苏珊·戈里芬:《强奸,泛美罪行》,载《堡垒》,卷10,1973;苏珊·布朗米勒:《与我们的意愿相悖》,企鹅丛书,伦敦,1977。强奸展现了阳物统治的现实。
似乎清楚的是,在男性施与女性的暴力与其他形式的恐吓和骚扰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而非明显的断裂。强奸、殴打甚至谋杀妇女与非暴力的异性遭遇、即对性客体的压制和征服具有相同的核心因素。里兹·凯利:《残存的性暴力》,政体出版社,剑桥,1988。那么,是否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色情文学是理论而强奸是实践呢?回答这个问题时,重要的是确定性暴力是否是男性长期压迫女性的组成部分,或是否与本书探讨的变化相关。
如前面关于男性性征的探讨所示,压制和侮辱女人的冲动也许是男性心理学的发生学方面。然而,可以商榷的是(尽管这样一种观点无疑是有争议的),在前现代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从根本上说并不依赖暴力实践。这种控制是通过男性特有的对女性的“所有权”以及不同分工的原则而得到保证的。妇女常常被男性施与暴力,尤其是在家庭场合;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她们在公共角逐场上受到保护,而男人却要相互施与暴力。在前现代的欧洲,强奸之所以“主要发生在边境、边疆、殖民地、战争状态和自然状态,在烧杀劫掠的入侵军队中”罗伊·波特:《强奸具有历史意义吗?》,载希尔瓦纳·托马塞利和罗伊·波特编《强奸》,第235页,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牛津,1986。,其原因就在于此。
这个名单长得可怕,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在这种状况下,暴力极少是施与妇女的:在这些“边界”地区,暴力公开发生,而强奸不过是其他残酷和屠杀活动之中的一种,参与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从事毁灭和被毁灭的男人。这种边界环境的一个特点是,妇女并不像正常情况下那样不介入男性领域,男人也不能保证她们的安全。
在现代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妇女空前地生活和工作在无名的工作场所,从本质上解除了过去把两性隔绝开来的“分离和不平等”的划分。假定男性性暴力已经成为性控制的基础,这在现时代要比以前更有意义。换言之,现在,大量的男性性暴力都源自不安全感和无能,而非缘自天衣无缝的连续的父权统治。暴力是对女性共谋的衰弱的一种破坏性反映。
除了战争状况外,今天,男人对待女人也许比男人相互间的对待更粗暴。男性施与女性的暴力有许多种,但是,至少有些产生了前述的影响:暴力使性征成为偶发的了。这也许是主要的——尽管当然不是惟一的——把这种暴力与色情文学联系起来的特征。如果情况属实,那么,不言而喻,色情文学,或大部分色情文学,就是霸权统治的组成部分,以性暴力作为二极支持而非作为阳物权力的例子。
当然,声称只有一种男性标准将是荒唐的,而假定所有人都不积极地欢迎变化将是虚假的。此外,性暴力并不仅仅是男人的活动。妇女在家庭场合常常向男人施与身体暴力;暴力在女同性恋关系中也并非不寻常,至少在某些环境下是如此。研究美国的女性性暴力可以表明女同性恋的强奸现象、身体的殴打和用枪、刀和其他致命武器进行的攻击。卡雷·罗贝尔:《为暴力命名》,海豹出版社,西雅图,1986。与斯托普斯通信的大多数男人都是为了增进女方的性满足而要求解决性问题的。有规律地嫖娼的许多男人都希望充当被动的而非主动的角色,不管这是否涉及实际的性受虐实践。有些男同性恋者在被动从属的状态下找到最大的快感,但许多人也能交换角色。他们比大多数异性恋者更成功地孤立出辨别力,将其局限于性欲区。一位男同性恋者说道:“有些幻想束缚我们,有些幻想释放我们。……性幻想一旦自觉地应用就能创造一种抵抗秩序,一种破坏,和我们无法逃脱的一个微小空间,尤其是当它们把主动和被动、男性和女性、统治和被统治之间鲜明而压抑性的区别搅混在一起的时候。”转引自林·塞加尔:《缓慢行动》,第262页,维拉哥出版社,伦敦,1990。
女性性征:互补性问题(1)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原则,即每一种性别都是另一种性别所不是的东西,那么,在女性性征与男性性征之间就将有一种简单的协调。事物并不是如此界限分明的,因为所有儿童在性心理发展方面都具有共性,尤其是在早期生活中。从今天的视角看弗洛伊德的思想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他都是第一个阐明这一现象的人。女孩也有类似于男孩的性史——尽管对弗洛伊德来说,其原因在于她们的早期性征“表现出彻底的男性特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性的三篇论文》标准版,霍伽斯出版社,伦敦,1953。当两性都发现小女孩缺少什么东西时,差异便介入进来;每一种性别都认为她被阉割了。
在弗洛伊德看来,从心理学上说只有一种生殖器官,即男性生殖器。尽管女孩的生殖器最初被男孩所忽视——一直到产生阉割的幻想时——但她很快就意识到她所缺少的是阳物,因此想要拥有它。甚至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女孩的经历并非与男孩的经历直接构成互补。如弗洛伊德所说,“只有在男孩中才同时发生对父母一方的爱和对作为对手的另一方的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三篇论文》标准版,霍伽斯出版社,伦敦,1953。女孩脱离母?,责怪她缺乏阳物,尽管她同样无法与父?认同,或把攻击移植到父?身上。
在对弗洛伊德的“逆转”中,肖多罗等作家从类似的观点出发,提出比之弗洛伊德原来假设的更大的一种互补性。据他们所说,女孩保持着男孩已经经历过的性心理发展的那些特征;男孩形成一些特征,形成对世界等事物的一种工具性态度,而女孩却不具备,或只有细微的表现。从一开始,母?与男孩的关系就不同于她与女孩的关系。她认为男孩相当不同于女孩,并以较“自恋”的方式去爱女孩。乔治,斯坦伯连:《男性幻想/男同性恋的现实》,第159~160页,海马出版社,纽约,1984。每一种性别都有所得,每一种又都有所失,尽管男孩失去的更多一些。女孩有较强烈的性别认同,但自治和个性感却较弱;男孩有能力从事独立活动,尽管为此而付出的情感代价是高昂的。
按照前述的命题,姑且修改并历史地追溯这种解释,试图表明何以应该避免对互补性的过分强调。母?身份的发明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母?在男孩和女孩眼里是无上的权力和无上的爱,在前几代人中情况并非如此。然而,那种权力和爱也相关于儿童的自治性,哪怕是在早期的童年生活中,人们对儿童自治性的重视也强似以前的典型强调(尽管有许多经验性例子证明这种重视大多受到了阻碍)。
男孩与母?的决裂导致这样的后果,即他对妇女的依赖被掩盖起来了,并在一种无意识和往往是自觉的层面上受到否认;在后来的生活中很难把性征融入自我的反映性叙事之中。不妨重申,男人易于压抑的不是爱的能力,而是情感的自治性,这对保持?密关系极为重要。女孩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这种自治性,这与其说取决于表达情感的禀性,毋宁说取决于交流。这种交流能力应该视作与男性易于发展的那种“工具性能力”一样重要。
在?密关系方面男人对女人的依赖不仅仅表现在性领域里,而且也可以体现为友谊。俱乐部或体育队等组织由于其全部男性的特点而提供了发展和巩固兄弟情谊的环境。然而,从纯粹关系特点的角度看,兄弟情谊——来自共同而且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