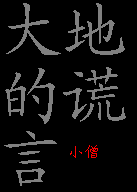大地之灯-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声音的时候,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淮在电话那边反复地询问,喂?喂?
简生终于哽出两个字,是我。
淮却像接到老朋友电话一样,笑着责怪他为什么这么久不来画画。少年在这边红着脸,安静地听着她说。聊天是时断时续的,简生的话很少。反倒是淮一直说着,语气轻松。
他们聊了很久。外面开始下雨。初秋的细雨在夜色中飞扬。除了路灯憔悴的光线之外,一片漆黑。简生顿时觉得有些冷,于是他对她说,我很冷。
淮说,你在哪里,快回家去。简生倔强地回答不想回家。淮在电话里面无可奈何地叹气,她最后说,你等等,我给你送一件衣服来。
就这样,凌晨一点的时候淮打车赶到简生面前。
只阔别了一个夏天的结尾,他却觉得很久没有见过淮了。简生看着淮从相距咫尺的对街走过来,穿过一束被憔悴路灯染成橙黄色的细雨,抱着一件风衣,整个人在色差强烈的黯然背景之中只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却仿佛一句暴露在绝望之中的誓言,撞痛了初秋雨夜的阒静,由此得以在时光中留下清晰的刻度。
淮走过来将风衣给他披上,拉了拉领子,然后轻轻地抚摸他的脑袋。靠近的瞬间简生清晰感到另一具身体散发出的温热,且有一种富含救赎意味的亲切与之共鸣。这身体没有与他游戏,只是希图温暖自己,并且告诉,人与人应当如此。他抬起头,看不清楚淮在逆光之中的黑暗面孔。
多年之后回忆起来,这情景依然有着悠长的反光,让人微感沉然。温暖是如此的浓稠,以至于简生相信他后来的人生只是在不断试图复制它,并被一再被现实否定。
毕竟,一如有人所言,对于大多数短暂而平凡的既定命运来说,人只是一堆盲目而无用的热情。爱之永恒美好与激越,只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永恒隔膜这一悲哀。
简生抬起头,看到淮的身后,一束舞台追光般的路灯照射下,夜风像是深海的洋流,裹着一股银色鱼群般的茸茸雨丝,柔软地按照风行方向散去。于是他幻想淮此刻有着玲溪的月色一样的目光,与这秋天最沉郁的夜色融合。
那个晚上,淮与简生坐在大商场前面的厅廊台阶上聊天,等待天亮。少年头一次小心翼翼地尝试表达自己的心迹,然而话到嘴边,却总是言不由衷。他简单而混乱地说起自己双亲缺席的乡下童年,以及回到城市之后和母亲在一起的令人失望的生活。谈话中断的时候,这个心思细腻的敏感少年不知所措地低下头,不知如何继续。淮就伸出手,长辈一样在简生的脑袋上轻轻摩挲。
少年鼓起莫大的勇气,颤抖着对她说,淮,我好爱你。
淮无言,只是转过头来温和地望着他。少年亦凝视淮的眼睛。四目相对。她是那么的美。
一瞬间冲动而预谋的拥抱与亲吻。他是激烈的,而淮却毫不犹豫地躲闪。她再次是推开少年,轻声却镇定地说,简生,不要这样。
良久的僵持,与无言。
沉默了半晌,淮眼里满含泪光,断断续续地说,简生,你要知道;你还是一个孩子。我只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想帮助你走过这段成长。就这样。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你。我担心我对你的关心会更加令你无法从中走出来,而我如果刻意远离你,又害怕伤害你令你失望。
简生。我不知如何是好。
简生只觉得无限难过。于一个生性敏感脆弱的寂寞少年,他从她的话语中感到切肤的疼痛。少年失望地转过头看着淮的侧面。几年前自己第一次在她办公室画画的情景竟然在记忆中急速的返回。那是简生回到城市不久的时候。一个阳光浓稠的安宁的下午。淮在美术课上让孩子们画心里最喜欢的东西。淮给他留下如此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这些年来,由此衍生出来的想念已经具备了初恋一般的力度,植入简生的人生。
少年对她说,我离不开你。淮。陪在我身边,求求你。
他再次抱着她,单薄的身体略有颤抖,竟令她于心不忍。
《大地之灯》 总是令他微感沉然
12
秋天,母亲定期寄给乡下李婆婆的汇款被退回。邮局在退件中注明,收件人不存在。于是她打电话给镇上才得知,李婆婆已经去世。母亲把李婆婆去世的事情告诉简生的时候,说,等我有空,就去乡下看看她。简生听了,激动地说,等你有空?老人家养我十年,难道她去世,还要等你有空才去?她孤寡一人,谁来料理后事?
母亲一时语塞,她说,简生,我是你的母亲,你不要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
简生说,好,母亲。我不要你跟我一起回乡。我要自己去。
母亲悲漠地苦笑,说,也罢,你去吧。我是再也不想回到那里。
简生请求淮跟他一起回乡。淮有过犹豫,但终究还是同意。
两个人坐火车,枕着车轮撞击铁轨的规则的声响,一路向北。在凌晨黑暗的车厢里,他睡不着,坐在床边久久地凝视淮的睡容。将掀开的被子轻轻给她盖上。
他又获得与淮的单独相处,觉得愉悦得无以言表。
下了火车,又搭乘客车,然后终于来到了镇上。简生见到多年前熟悉的场景。深秋的北方,天气深肃。初雪涂抹在这座荒城般的小镇上。铅灰色的矮楼房中间夹杂着一条条年代久远的陋巷。清晨被雾霜抹得毛茸茸的玻璃窗,小卖部门口挂着被风吹得刷刷作响的塑料布,街道上肮脏的雪以及静止在路边的拖拉机。去年的陈旧红色剪纸……一切都勾勒着萧索之意。
他们从这镇子上坐班车去乡下,回到靛青色的湖泊之畔。芦苇已经被秋霜染成枯黄,在风中忧郁地渐次倒伏。南归的大雁,驮着铅灰的积云,让飞翔贴满了天空。乘船缓缓穿过广阔的大湖,在处子般平静的水面划出静静扩散的波纹。简生指着对岸,对她说,看,那便是我的家。
婆婆的房子果然空了。邻居也都不再是当年的那些认识的农民。他们询问婆婆的墓地,被絮絮叨叨地告知,是村委会如何如何给她老人家办了后事,葬在后山的坟地。人们说,造孽啊,老人收养了一个儿子,一把屎一把尿带到十多岁却被人带回城里去了啊……
简生听到,如芒在背。
两个人在村子后面的坟山上去挨个找,终于找到一块新墓,草草了事的碑刻,拙劣而孤寂。隐喻着一个形销骨立的老人的身影。他不知道是该献上花束还是应该烧香献上大盘的贡品,仿佛一切都是滑稽并且不协调的。简生在墓前长跪不起,俯首磕头,埋在那里难过得发不出声音来。
黑色的鸟群在天空盘旋,忧郁而不祥。暮色四起,寒气逼人。淮在远处默默地看着他。
末了,简生直起身子来。他对她说,我们明天便走吧。这地方让我太伤心。
那个寒冷的夜晚,他们两人寄宿在一户农家。他梦见了童年时代的生活。
仲夏的月光照亮了一泊泊梦魇一般的湖,水面如镜,闪烁丝帛般的柔润光泽。唯有水蜘蛛细长的腿在点水时触动一圈圈水纹,轻轻扩散之后被深入湖水的芦苇茎杆所阻挡,波纹便紊乱地弥漫到更广的夜色中去。
黑暗中的簇簇芦苇穗子被皎洁月光照出茸茸的紫蓝色光晕,随歌谣一般的晚风窸窸窣窣摇晃,犹如婆婆的摇篮曲。偶尔一声鱼跃落水的声响便惊得草丛中原本和谐规律的虫鸣一阵激昂,亦使聚精会神捕食的狍子或者鹭鸶乱了阵脚,惊惶窜动,甚至惊扰了野鸭的梦境,让它们发出不适的呀呀叫声。然而很快,这一切又遁入无边的黑暗的夜。唯有凝着霜露的苇丛似钟表指针一般匀净摇摆。
这就是他记忆深处最宁静的童年夏日。白天在苇荡里捉鱼戏水折腾得筋疲力尽,此刻他必定是躺在那张铺在堂屋的地板上的老苇席上,在婆婆摇扇子的吱吱呀呀声音中渐渐入睡。皎洁月光漫过门槛,在堂屋地上切下一块明亮的银霜,刺眼到不得不背过身睡觉。到了后半夜,这铺在地面的苇席凉得凊骨。熏过的苦蒿挂在老屋的房檐上,驱散蚊虫的同时散发出浓烈的辛香,闻起来仿佛饮了一口井底的甘泉。夏日,子夜刚过,丑时天就开始亮了。远处的狗吠鸡鸣之声隐隐约约传来,而他还贪恋在甜美的梦境里面,直到清凉的朝阳毫不客气地将光线射入堂屋,他才被迫在黄虎那热乎乎的舌头添舐下不情愿地醒来。
到了冬天,大片的水域已经凝结成冰湖。在月色之下呈现金属般的暗蓝色泽。风夹带着纯净寒冷的空气直闯肺叶,总是能打得你一个激灵。积雪覆盖在苇丛上,像是堆堆谷垛,只剩几根白色的毛茸茸的芦苇穗子随风摇晃,像是挥别那些悲郁的岁月。偶有缺乏经验的黄羊不慎走到了冰面上并很快滑倒,狼狈地挥舞着无法从冰面上站起的蹄子。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地将其捉来,品尝一次冬日里难得的鲜味。那纯色的皑皑白雪一直要等到地底下的春天彻底迸出萌芽才会融化。在这漫长的寒冷季节里面,孩子们都会拿着钢钎到冰湖上去捉鱼:只要你的钢钎戳得准,一个窟窿下去,急于呼吸的成串鱼儿就会像泉水一样一条条接着往外直蹦。
还有那春温秋素的岁月呢……
他在半夜从梦境中醒来,只觉得心下戚然。他瑟缩着下床,像小孩子一样无助地钻进淮的被子。他说,淮,我梦见了湖。
淮将少年抱在怀里,无言地轻轻抚摸他的头。他在她的怀里,重新温暖地陷入沉沉睡眠。
这样充满母性的长辈式的关怀,给简生的一生烙下深刻的灼印。被有温度的触觉所提醒,会时时散发出经久的感怀。带有醇香。回忆起来,总是令他微感沉然。
《大地之灯》 仿佛是重归家园
13
他从乡下回到家的那天晚上,和母亲在厨房吃饭。母亲追问他,你和谁一起去的乡下?他坦然地回答,和淮。母亲又说,你怎么能够和一个这么大的女人在一起?别人知道了
会怎么说?
简生没有抬头,他说,我没有想过别人会怎么说。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母亲气愤地说,你可以不管别人怎么说,可我这个当妈的听到了我怎么能够不管?那么不堪入耳的闲话……你不可以这样!你再这样傻下去,混下去,你这辈子就玩完了!!
简生亦激动地还嘴,我怎么就傻了,混了?!就算我傻了混了,你就现在才来管我?!你管得着我么?!你管别人怎么说我,你怎么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啊?!
母亲气得发抖,你怎么这么不要脸……我怎么着也是你亲妈啊,那个女人就哪一点好了,把你迷成这样?亏我还拿钱给你让你去她那儿画画,我真是瞎了眼!
简生听得血气奔涌,再也按耐不住,他带着哭腔吼,我不配做你儿子!行了吧!我跟淮的事,轮不上你来管!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少年的脸因为冲动和愤怒而格外扭曲。母亲甩手就又是两记耳光。少年被打得趔趄后退,耳朵又是嗡嗡直响,脸上火辣辣地疼。
他知道这样的把戏又来了。
母亲转身冲进他的房间去,在那边絮絮叨叨地骂,当我傻子么,你平时在家里,装作是做作业,背地里在干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她气得手抖,直接过去就拉开抽屉,从里面抓出简生的速写本,又扯开画板,翻出他的画,啪地扔在厨房门口的地上,指着那一对纸,骂,我的血汗钱,让你读书你不读书,晚上也不做作业,给你买纸买笔,你就一天到晚拿去画这女人,你不嫌你没脸啊,这个没出息的……
母亲盛怒,越说越过分,从地上又把那些画纸抓起来撕掉。少年再也受不了这般的羞辱,眼看着他的那些画在母亲手里渐渐变成碎片,他忍无可忍地冲过去把母亲手里的那些画抢出来。他咬着牙说,你给我,你敢再撕我跟你没完……
母亲未曾想到他会说这么硬的话,扬手又要打他,被他一把抓住。她无处泄气,便转身去寻了一只铁衣架,扬过去又在他手臂上抽……
简生疼得不停地躲闪,母亲却还不住手,打红了眼。此时简生忍无可忍地跟她说,够了,妈……够了……他抱着头躲闪到边上,然后瑟缩着蹲下来蜷在墙角,留着道道清淤痕迹的双肘紧紧地抱着双肩,蜷着的双脚摩挲着地面,还在一点点地挪动并躲闪,如同受伤的小兽一样。
他胸中有激越的疼痛,止不住地哭。此番痛哭,他仿佛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呕出来一样。脑中闪现着无数片断——失去双亲的童年,回到城市之后在学校受过的孤立和委屈,什么都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时常被打骂,亲眼撞见的母亲和陌生男人做爱的场景,令人寒心的家庭关系,婆婆的去世,以及对淮的苦恋……一切都如黑暗潮水般汹涌地撞击在心上,他并非是因心智混浊而顽皮无赖的少年,可以对一切熟视无睹,被打了屁股穿上裤子转身就忘。
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