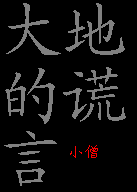大地之灯-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卫东对她说,跟我一起走,我们回到城市去。
她知道他是去逃亡,并且肯定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于是她说,那我们带上简生一齐走。他听完却皱眉,说,我们不能带走他。
这是我们的骨肉,不能弃之不顾!
你异想天开!我们把他交给李婆婆,她老人家本来就孤寡无后。
你个丧尽天良的,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不要!
争吵越来越激烈。她扯破了脸痛骂,然后又丢下脸面苦苦央求。直到最后,卫东铁青着脸,不再吭声。她带着他的默许,颤抖而卑微地抱紧了孩子。
临行前的那个夜晚,她抱着简生躺在他的身边,冷得发抖。她看着因为饥饿和寒冷而轻声哼哼的婴孩,心里格外酸楚。
事实上,她自己也并不知道,即使逃回城市,又将会有怎样艰难无着的生活。而这个孩子的存在,又将是怎样一个难题。
这最后的一夜显得格外漫长。天终于亮了。呼啸的北风仍在土房子外面肆虐。卫东呼地打开门,北风夹着湿气汹涌而进,孩子被冷风激得啼哭起来。
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早晨,蒙蒙的雾气之中,他们和另几个知青以及前来送行的李婆婆一起,前去搭林场的车子,要离开这片土地。
去乘车的路上,他对她说,我来抱简生。她欣喜地以为卫东已经下定决心带孩子走,于是满怀高兴地将孩子交给他。到了停车处,车斗里已经有很多知青和农民等在那里,周围有送行的人。卫东把她送上车子,然后把行李递上去,使唤她找个角落把行李搁好。
他迟迟在下面磨蹭,直到车子启动的前一刻,这个年轻的父亲忽然把孩子放在地上,自己独自爬上车斗。
车开走了很远,素清才发现卫东带着苍白得发青的脸色,咬着牙关坐在人堆里,怀里没有简生。她回过神来,问,生生呢?我的生生??可怜的母亲因为恐慌而声音颤抖,爬过满车斗的拥挤的人和行李,爬到尾巴上去,但是早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她甚至没有看到,简生是如何像个垃圾一样被扔在路上,然后被婆婆捡起来抱走……
车依旧往前开,素清瞬间发疯一样尖叫起来,拼命要跳下去。卫东死死拉住她的手,任凭她豁了命撒泼也不放。车斗里乱作一团。知青和农民们有的在吆喝,有的在咒骂,有的让她下去,有的拉她回来。纷乱的双手和身影,无法分辨。
卫东拉着她的手不放。她回头狠狠给了他两记耳光,破口大骂,你个狗娘养的畜牲!
卫东吼道,你给我听着!我们尚不自保,怎么养得起这个孩子?!回去了怎么跟家里交待?!我事先早就把他抱养给了李婆婆;老人会好好养他的!你他妈犯不着操这份心了!
她痛哭着,神魂颠倒地拼命摇头。不可置信地流下眼泪……
村庄渐渐完全消失,密林山野在天地相接之处破了一笔清冥浩荡。留下一笔写意的淡墨,掩映在浓浓的雾气深处。卫东镇定地看着一切。眼睛里面没有丝毫泪水。
他们在车上度过一个昼夜的时间。一路上她脸色苍白如纸,头发蓬乱,默不作声地靠在一角,干裂发白的嘴角微微翕张。他看着她陡然间苍老的形容,简直与一个疯癫庸堕的老妇无异。他回忆起初次见面的夜晚,她犹如秋林般的漆黑发辫,在烛光中闪烁着靛蓝的光泽。目光鹿一般伶俐。绯红的脸颊,像是春日山岭中的达子香。他听到姑娘在吹奏《山楂树》,于是动情地将自己写在树皮上的诗歌送给她。
《大地之灯》 淹没最后一丝日光(2)
但一切都只是过去了。生活和境遇足以轻易而彻底地改变所有。
他心中是疼痛的,隐隐不忍,便伸出手轻轻抚摸素清的头,试图理理她蓬乱的发辫。她却陡然惊恐地躲闪,抬起头,目光锥子般充满恨意。卫东无奈地缩回了手,低声说,这不是我们的错。
这不是我们的错。他说。
她回答,对,这不是我们的错。可是卫东,她幽幽地说,你心太狠了。一般人都不会有你这么狠心的。
他咬紧了牙关。沉默不语。
是用了多年混浊而悲壮的青春,去懂得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命运不可掌控,尤其是若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降生。
下车的时刻,她要继续南下,而他要向西。她对他说,我们该分开了。他拖着行李回过头来,镇定地望着她。憔悴的脸上重新上演默然的表情。他无言。转身扛起行李,兀自向前。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情景隐喻着他分裂的人格:最忧郁而浪漫的诗歌,与最自私和无情的抉择。
那便是他留给她最后的印象。那兀自离去的身影,仿佛一场仓促而混乱的落幕,宣告青春的彻底消失,在这个同样仓促而混乱的世界,和时代。
人们说,曾经见到一个年轻知青,独自深入小兴安岭的林区,在山坡上的荒冢前叩首,长跪不起。
他是简卫东。当他已经决意离开这片土地,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他终于能够鼓起勇气,去看望这座坟墓。当年自己粗心大意地添加了过多的柴火,烟囱被烤烫,衣物被点燃,引起了大火,最终导致好几个人烧伤,四个女孩子丧身火海。她们的笑容就这么被遗忘在了异乡的土地,遁入时光的隐秘角落,悄无声息。
那是在一个黑夜迫近之前的黄昏。简卫东站在她们的墓前,看到她们熟稔而陌生的笑容逐渐隐没在落日的群冈。他知道这一片年轻的生命必定已经遁入了他在现实中无法接近的理想天堂。那些萋草离离的残碑断碣,在寂静的岁月之中,美得这样辛苦与悲壮。
这片笑容在异乡的土地下沉睡。无人问津。以后还将一尘不变地沉睡下去。四周零乱丛生的蒿草和野花,迎着漫天悠扬而清亮的晚霞,随风轻轻摇摆。它们亦是沉默了又沉默的判断者。他独自一人良久地站立着,透过玄青色的苍凉墓碑,凝视这些死于自己手下的十七岁的眼睛。如同月下潮汐,时间缩影成一帧帧光感饱满的电影胶片,被岁月的齿轮带动着从眼前卷过。
第一次知青联谊活动上,他还是那个有着一双苍白颀长的手的诗人,拉一把深棕色的大提琴——雪白颀长的手持着琴弓,清晰的骨节极富韵律地突起,在夜色以及烛火的洗濯之下,像是一首节奏凌跃的诗歌。在匆忙离去之前,他拿着一盒写在桦树皮上的诗歌,对那个美丽的姑娘说,这是我写的诗,有兴趣你就看看吧。
然后是记忆中那场关于大火的噩梦。黑色的浓烟未曾散尽,被活活烧死的四个女孩子,手挽着手蜷缩成一堆。她们的身体已经成为漆黑的焦炭,裹尸布不断地浸出黑浓的人油。
那些仲夏之夜前去幽会情人的迢迢路途,那些清晨在浓雾弥漫的白桦林里匆忙的吻别,那些年轻身影被茫茫青纱帐所遮掩并最终消失的青春岁月,都已经彻底消失。不复追回。
简卫东在坟墓前持久的伫立,远处便是辽阔的遗忘的水域,遍布浓浓雾气和丛丛芦苇。山岗上夜已经浓了。面对星月凊辉,他深知自己已经不能再对命运有任何怨悔与贪婪。因了相对于这片沉睡的笑容,他还拥有万能的生。只有自己知青岁月,能陪伴这坟墓下的生命与山冈日夜私语。
他与她们都是共和国理想的效死者。同时代本身一样,是无知而无辜的效死者。
《大地之灯》 逃离插队农村之后(1)
5
童素清逃离插队农村之后,已经备受斗争迫害的父母再次因为她的逃亡而蒙受耻辱的追究,她自己亦根本无法求学求职,家里又没有分给她的粮票布票,生活很难。已经逼迫到绝路。于是她横了心跟着几个抱负不凡的知青一起偷渡南洋,漂洋过海去谋生创业。一去多年。
在南洋的生活亦是艰难无比,在彼地她很快与一名华裔商人结婚,开始跟着他投资做生意,惨淡经营,十分艰辛。有了经济保障之后,她急不可待地开始上大学,弥补青春年华失学的遗憾。几年之后那商人意外去世,她继承遗产,自己做起了老板,生意越来越大。她终于经过这些艰辛的打拼而立足。十年之后,她才第一次回国。
十多年的岁月里,她像是用战争的残暴来洗濯伤痛的顽强士兵,在每一个抉择的关头都毫不犹豫地向着风险最大的目标前进。一同创业的老三届们,也都纷纷出人头地。有时候她深刻地觉得,在离开插队农村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苦难能够比得上那几年艰难并且毫无指望的劳作和生存。而当一个人熬过了苦难的底线,对于世间的冷暖毫无知觉,并且韶华已逝逼迫她不能再在无用的事情上浪费哪怕一分钟时间的时候,就真的只剩下所为成功了。因为其中的代价,已经早早透支在青年时代,并且其庞大的伤害与遗憾,并非一句貌似豪迈而动情的青春无悔便可以弥补——即使于一个时代而言。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面,生活的目的仿佛只是一场正义的并且迫不及待的报复,本质上,她仍然是无知无辜的效死者。连回忆那段遥远的青春,那些深深埋藏在田塍褶皱中的岁月,都已成为奢侈的伤春悲秋。尽管无论如何,回忆总是以它无可替代的华丽堪与今日和未来相媲美。
多年来,她已经渐渐忘记了简卫东。忘记了这个她交与了全部青春的情人。她后来渐渐明白,简卫东当初扔下孩子并且与自己分道扬镳,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抉择。只是在十年之后的某个夜晚,她忽然又梦见了简卫东,梦见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还梦见了那个不满一岁就送给老人收养的无辜的孩子。简卫东洁白颀长的双手在梦境中清晰如昨,而双手的主人却被赋予了狰狞的面孔——那双手攫着一个婴孩,无声地朝她逼近,婴孩的啼哭却格外的响亮而单薄,她被渐渐逼近的狰狞面孔惊醒,恐惧像是包围自己的大火……
她在半夜被这恶梦惊醒。从床上坐起来,感觉虚脱而疲倦,伴随着无边无际的伤感。
就在第二天,怀着莫名歉疚的心情,她便准备返回当年插队的乡下,去接走简生。
像是一趟迟到了多年的旅行,茫然地向记忆深处的岛屿前进。旅途的尽头就是那片广阔的遗忘中的水域。
这是一路怀旧的旅途。素清去林区探望。
她始终都记得当年那场大火之后,自己亲眼目睹几个女孩子烧焦的尸体时候那种激荡内心的震骇。她受内心记忆的指引,去看望她们。
下午快要结束了。日光已经浓得非常粘稠。再次是一个大好春日。晴朗的天色以及烂漫的春光丝毫未变,一切如同多年前那个模样。
埋葬着那四个女孩子的简陋荒冢已经被疯长的草木所掩埋,只在层层绿色的深处隐现出歪斜的一角玄青色石碑。拨开狗尾草毛茸茸的穗子以及苦艾的茎叶,看到石碑上刻的那些朴素而悲凉的名字,已经被厚厚的茂盛青苔所模糊。面无表情的阳光依然是把一道道光辉刻在这被遗忘的坟墓上。不知道在这十多年的漫漫岁月之中,坟墓之下那片年轻的笑容经历了怎样的清冷寂寞,才能盼来今日一个蓄谋却又不经意的探望。
山风抚过辛香浓郁的土地和树林,给她的脸带来久远而安宁的摩挲。她带着空白的记忆和念想,就这么安静地站在僻静的山岗,与簇簇沉默的狗尾草和苦艾相伴,如同年幼贪顽的孩童一般,贪恋着跨越时光的快感。她仿佛重新回到了十多年之前的自己。越过了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的那些坎坷的年岁,仍然是那个穿着肥大的棉衣穿梭在树林深处的女孩,留恋着林中的白桦,冬青和映山红。或者是后来那个穿着军上衣的姑娘,腆着肚子,忍着燥热背了装满玉米棒子的背篓,辫子纠结发腻,沾着叶絮,蹬着一双磨烂了的军胶鞋,穿越茫茫的青纱帐。
然而光阴这么的不动声色。这些,已经成为往事。
《大地之灯》 逃离插队农村之后(2)
横躺在生命中接受回忆的检阅,浑身有着经过时光的酝酿而散发出的美好光彩。竟仿佛变成了自己不曾获得过的梦想一般,连理性都因之陶醉得晕头转向。殊不知,在经历往事之时,是那样一般辛苦。
落日像是风滚草一样被风吹下了地平线。她望着这片沉默的笑容已经只是淡然的心情。是离开的时候了。她伸手摸摸冰凉的石碑,默默告别。或许这一生一世都再也不会再来探望了罢。毕竟没有什么凭吊能够回报生命之中那些无人知晓的坚忍岁月。因生命本身不过就是一树沉默的碑,上面刻下的字早已被尘世忘却。
离开林区,她辗转回到县城。刚下车,就碰见一个在茶水摊闲坐的老头。是原来那个生产队的指导员。他已经老了那么多,亦是认不出她。她不打算前去攀谈,因为她而今已经不需要再凄凉地拿着一纸招工返城的申请奔走在这些人的脚下。
物事人非。她心里忽然想起儿时的唐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