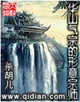华山论贱-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个歹徒咧着嘴,得意地笑了。其中有个黑皮无赖毫不知耻地说:“哥们把她玩恣了!”另外两个歹徒也胡言乱语:“她是我对象,关你屁事!”一场争吵,直到那男子的行李从车窗扔出,他随后被推搡而下。汽车又平稳地行驶在山路上,女司机掠了一下头发,按响了录音机。
车快到山顶,拐过弯去就要下山了,车左侧是劈山开的路,右侧是百丈悬崖。汽车悄悄地加速了,女司机脸上十分平静,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眼睛里淌出晶莹的泪水。
第二天,当地报纸报导:伏虎山区昨日发生惨祸,一中巴摔下山崖。车上司机和十三名乘客无一生还。
半路被赶下车的中年人看到报纸哭了。谁也不知道他哭什么,为什么哭……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阿Q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是和阿Q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
“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鲁迅《阿Q正传》
如果说,阿Q是贱人的精神领袖,恐怕没有人会反对。这个并不存在的人物和客观存在的“精神胜利法”,确实给广大贱人提供了行动的榜样和指路的明灯。伟大的“精神胜利法”告诉我们,在你挨打的时候,在你失败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难过,不要伤心,不要悲哀,要高兴,要快乐,要有希望。正如契诃夫所言: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里燃起来了,那你应该高兴,而且感谢上苍:多亏你的衣袋不是火药库。要是有穷亲戚到你家里来找你,那你不要脸色发白,而要喜洋洋地叫道:“挺好,幸亏来的不是警察!”要是你的手指头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挺好,多亏这根刺不是扎在眼睛里!”如果你的妻子或小姨练钢琴,那你不要发脾气,而要感激这份福气:你是在听音乐,而不是在听狼嗥或猫的音乐会,你该高兴,因为你不是拉长途马车的马,不是细菌学家做实验的细菌,不是旋毛虫,不是猪,不是驴,不是茨冈人牵的熊,不是臭虫。。。。。。。你要高兴,因为眼下你没有坐在被告席上,也没有看见债主在你面前逼债。如果你不是住在十分边远的地区,那你一想到命运总算没有把你送到边远地方去,岂不觉得幸福?要是你有一颗牙痛起来,那你就该高兴:幸亏不是满口牙痛。要是你给送到警察局去了,那就该乐得跳起来,因为多亏没有把你送到地狱和大火里去。要是你挨了一顿桦木棍子的打,那就该蹦蹦跳跳,叫道:“我多运气,人家总算没有拿带刺的木棍打我!”要是你妻子对你变了心,那就该你高兴,多亏她背叛的是你,不是国家。
如果这本书没人买,没人看,我该庆幸,还好没有造成不良影响而被禁。如果得了病,该庆幸,还没有死。如果死了,该庆幸什么呢?
大二的时候,考英语,是分AB卷的,全是选择题。一兄弟在最后10分钟终于拿到答案,突然发现答案是A卷的,而自己的卷子是B卷。再拿答案已来不及。低头想了1分钟,开始抄。抄完了后,将答题纸角上那个“B”一把撕了,写了个“A”,就交了。分数出来,60分……全班对他五体投地。
大二的时候,上法律课,我们法律老师有个癖好,喜欢提问,提问之前必高声重复一遍问题。有一次正在上《民法通则》,突然老师又提高声音开始提问,所有同学都恐惧地盯着老师,惟恐被喊到,因为老师以提问来代替点名,所以是看着点名册提问的,所以大家都不必低下头。
“一班25号!”老师点道。
一片沉默(张三正在发呆)……
“25号——张三!来了没有?”老师重复道,刷!整个教室的人都看着张三。
“没来!”张三大叫。全班人都愣了!不过很快又开始佩服张三的勇气了。
“怎么没来的?”老师又问。
“他病了!”张三无奈,只得撒谎,全班一阵哄堂大笑。
“你是他宿舍的吗?”对于莫名其妙的大笑,老师也被搞糊涂了。
“是的。”面对老师的盘问,张三脸都绿了。
“太不像话了,回去告诉他,让他下午到办公室来找我!”全班同学又是一场大笑。
“啊?!好。”张三头皮都开始发麻了,下午找谁替我去挨骂呢?就李四吧,唉,又得请那小子吃一顿了。
张三正在为逃过一个问题而庆幸,老师又补充道:“那这个问题你替他回答吧?”
“啊!?”张三极不情愿地站起来,郁闷之情可想而知,教室里已经有人笑痛肚子了。
“老师,能不能重复一下您问的问题?”
“啊!!这个问题我已经重复了三遍了,你怎么上课的?”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张三额头上已经有汗珠了。
“那好,我再重复一遍……”
“我,报告老师,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张三想反正是一死,何必死得那么窝囊呢,于是理直气壮起来。
“那好,下午2:00和张三一起到我办公室来!”所有同学都笑到喷血。
从此,法律课无一人敢说某某没来。
——《网络笑话选编》
有的人就是够贱。可能是觉得生活太舒服了,可能是觉得没有什么能够征服他们,可能是觉得生活太平淡而缺少刺激吧。就像电影《甲方乙方》里面的大款,非得自己找点儿罪受,有了罪受的时候又受不了,又盼着早日脱离苦海。
而像张三这样的人自讨苦吃完全是为了哗众取宠,这也是自虐者其中一部分的心理。说到底,一时的想受虐和有目的的想受虐还是其中层次比较浅的,真正的贱人,把受虐当作一种快乐。这群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群体,虐恋群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SM。
对虐恋的研究,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女士是专家。她在自己的著作《虐恋亚文化》中谈到:“虐恋”这个词英文为sadomasochism;有时又简写为SM、S…M、S/M或S&M,最早于1836年出现于法国的字典,到19世纪80年代才传播到德国的。虐恋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所谓痛感有两个内涵,其一是肉体痛苦(如鞭打导致的痛感);其二是精神的痛苦(如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的羞辱所导致的痛苦感觉)。如果对他人施加痛苦可以导致自身的性兴奋,那就属于施虐倾向范畴;如果接受痛苦可以导致自身的性兴奋,那就属于受虐倾向范畴。虐恋关系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统治与屈从关系和导致心理与肉体痛苦的行为。虐恋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形式是鞭打和捆绑。因此有人又将虐恋活动概括为D&B(displineandbondage)或简写为DBSM。
瑞克(TheodorReik)为虐恋下过一个形象的定义:“一位威尼斯智者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只要女人既能令他快乐又能令他不快乐,他就是个年轻人;如果女人只能令他快乐,他就是一个中年人;如果女人既不能令他快乐又不能令他不快乐,他就是一个老年人。现在我们不论年龄,有受虐倾向的人属于哪一类?他是一个只有令他不快乐才能令他快乐的人。”(Reik,339)高度概括地说,虐恋倾向是快感与痛感的结合。
痛感和快感本来就很难统一,但是没有痛感就没有快感让人感到就有点特别了。这类贱人贱的程度也超乎常人的想像,很多人对自己身体和灵魂的摧残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因为越贱的事情,越给他们带来快感。这可谓是见过贱的,没见过这么贱的。当然,你不能说他们变态,只能说,他们很特别,特别的贱。
“我希望有人在我的屁股上用藤条痛加抽打,直到我痛得求饶。我还想弯下腰,脱下裤子,让一个强壮的男人不断地鞭打。这就是我的愿望。”
——某名校厕所的墙壁
汤姆走进一座图书馆,他问图书管理员介绍如何自杀的书籍放在何处。
“第三排书架的左上方。”图书管理员回答道。
汤姆在那个书架上边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又回到柜台前对图书管理员说没有见到那些书。
图书管理员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登记簿,说:“恐怕你是无法找到了,因为迄今为止借这些书的人没有一个来还书的。”
——《网络笑话选编》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古人的话虽然未必完全可取,但起码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生命是崇高而伟大的。父母赋予你的生命,应该好好珍惜。生活是美好的,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都应该勇敢地活下去。
而对于贱人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受到压力,感觉到无法承受的时候,无数的人选择了自杀。我们先来历数一下自杀的名人和他们选择的方式吧。
借助药物型的,有李立三、严凤英、杨朔、阮玲玉、希特勒、隆美尔等;上吊型的,有三毛等;跳楼型的,有张国荣、谢津、伊丹十三、罗广斌等;割腕型的,有玛丽亚·凯莉(未遂)、宫泽理惠(未遂)、德鲁·芭莉摩尔(未遂)等;刎颈型的,有项羽、关天培等;切腹型的,有三岛由纪夫、南云忠一等;触电型的,有贾平凹(未遂)等;投水型的,有屈原、戈麦、陈天华等;自焚型的,有商纣王、公孙瓒、明惠帝朱允火文、古巴比伦王等;绝食型的,有伯夷、叔齐、朱自清(变相绝食致死)等;死亡装置型的,有贾耐特·阿德金斯(本不是名人,因志愿使用杰克·盖博坎博士开发独特的自杀装置成功自杀而在死后成为名人)等;卧轨型的,有海子等;吞枪型的,有海明威、柯特科本、尼泊尔王储迪彭德拉、王宝森、凡·高、茨威格等;爆炸型的,有“9·11”恐怖分子等;煤气型的,有翁美玲、闻捷、川端康成等;撞死型的,有杨继业、王累、商容等。
这些名人,有为了正义事业慷慨赴死的,有兵败垂城被逼自尽的,有为了表明自己的气节以死明志的,但也有很多因为精神抑郁,对生活失去希望而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最后一类人,就不能不算是贱了。而且,是顶级的贱。
可怕的是,这种贱正在世界各地悄悄风行。美国、日本、英国,都出版过《自杀指南》。很多青少年受不了生活的打击,选择了自杀。而《自杀指南》往往不惜花费笔墨介绍自杀的实例,刊登自杀方法排行榜,评说吞枪的“最佳”角度、服用多少药物剂量才能确保“死得干净”和怎样跳楼才能“直达黄泉”……还有怎样准备遗嘱,以及在自杀的时候听Pinkfloyd的歌曲《告别残酷的世界》和看Yeats《爱尔兰机师预见他的死亡》的诗行等骇人听闻的内容。互联网上也出现了匿名的荷兰语网页指导人们如何自杀。
自杀是当一个人的烦恼和苦闷发展到极端,对“破局”的事态产生恐惧,对生活失去信心,对现实感到绝望而采取的惟一的、最后的“保护”的手段。自杀一般始于心理挫折,发生在摆脱抑郁的心理冲突的过程中。有关数据表明,青少年自杀率,目前全世界呈增长趋势。这引起了全社会及家庭的普遍关注。在我国,这种情况也较严重,自杀,成为了青少年,特别是年轻人(18…30岁)的主要死因。
在这里,我们要说:贱可以,但是不要这样贱。毕竟,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崇高的。
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的一夜。现在他结实的身体像一块岩石一般矗立在水面上,左肩上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圣者克利斯朵夫倚在一株拔起的松树上;松树屈曲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