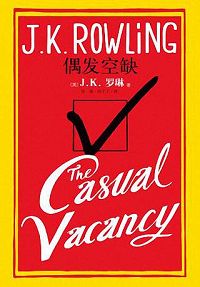偶发空缺-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到奥伯了吗?”特莉朝五十码外奥伯的邻居喊道,“他回来了吗?”
“不知道。”那女人说着扭过头去。
(不打特莉时,迈克就做别的事,令她无法启齿的事。凯斯奶奶再也不来了。十三岁时,特莉逃跑了,但没有去凯斯奶奶家,因为她不想让父亲找到她。但人们还是抓住了她,把她送进了收容中心。)
特莉用力拍打奥伯的门,等了等,又开始敲,但还是没人开门。她跌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浑身发抖,哭了起来。
两个翘课的温特登女生从旁边走过,看了她一眼。
“是克里斯塔尔的妈妈。”其中一个大声说。
“那只鸡?”另一个扯高了嗓门回答。
特莉无法打起精神来骂她们,因为她哭得太厉害了。那两个女孩嗤笑着大步走出了她的视线。
“表子!”走到街角时,一个女孩回头喊道。
3
加文本可以邀请玛丽来他的办公室,讨论最近和保险公司的往来信函,但最后还是决定去她家里拜访。她厨艺了得,所以他预留出下午较晚的整段时间,怀抱着她能请他留下来共进晚餐的些微希望。
出于本能的羞怯,他无法直面她的悲痛,而这种羞怯近日已因定期的联系而消弭。他一直对玛丽心存好感,但有巴里在场的时候,玛丽的存在总是变得模糊。她倒从没有显出不喜欢贤内助角色的样子,相反,她对自己能起美化背景的作用似乎很是满意,知足地为巴里的笑话捧场,知足地只是待在巴里身边。
加文觉得凯恐怕这辈子都不会甘当这样的角色。把车开上教堂街时,加文想,若是建议凯为了男友的愉悦、快乐和自尊调整自己的言行或压制自己的观点,她准会勃然大怒。
他认为自己的过往情史没有哪一段比现在更不快乐。哪怕是跟丽莎之间的感情垂死挣扎时,也会有休战,有笑声,有往日甜蜜突然涌上心头的时刻。和凯在一起却像是持续的战争。有时,他会忘记他们应该是喜欢彼此的。话说她到底喜欢他吗?
去迈尔斯和萨曼莎家吃晚饭的次日上午,他们之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争吵以凯摔下听筒、挂断加文的电话而告终。之后的整整二十四小时,加文都相信他们的关系算是完了。不过,尽管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心里感到的却是忧虑多过轻松。在他的幻想中,凯最好消失回伦敦,然而事实是,她已经通过一份工作和一个在温特登上学的女儿把自己和帕格镇拴在了一起。在这个芝麻大的小镇上,恐怕会跟她低头不见抬头见。也许,她已经开始在流言之井里下毒对付他了。他想象着她把在电话里对他说的话又讲给萨曼莎或是那个让他起鸡皮疙瘩的熟食店大嘴老太婆听。
我为了你让女儿转学,我自己辞职又搬家,你对待我却像是对一个不用付钱的妓女。
人们会说他为人很不地道。或许他这件事做得真的不地道。在这段恋情的进程中,一定有某个他应该抽身而退的决断时刻,但他没有看到。
整个周末,加文都在阴郁地思考自己被人们看做负心汉时会有何感受。他从来没有担纲此等角色。丽莎甩了他之后,所有的人都同情他,对他很客气,特别是菲尔布拉泽夫妇。负罪感和恐慌像疯狗一样纠缠着他,直到星期天晚上,他终于崩溃,通过电话向凯道歉。现在,他又回到了自己不想待的位置,为此他对凯心生怨恨。
加文把车停在菲尔布拉泽家的车道上,就像巴里活着时他经常做的那样。他朝前门走去,注意到自他上次拜访后,有人修剪了草坪。按了门铃后,玛丽几乎是立刻就把门打开了。
“嗨,下午——玛丽,怎么了?”
她的整张脸都是湿的,晶亮的眼泪马上就要从眼眶里落下来。她深吸了一两口气,摇了摇头。接下来,在意识到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之前,加文发现自己在门阶上和她抱在了一起。
“玛丽,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感觉到她点了点头。他深知两人无遮无挡地抱在一起多么引人注目,也知道身后就是一条开阔的马路,于是引着她进了屋。在他的怀里,她是那么娇小而脆弱,手指紧紧抓住他,脸贴在他的风衣上。他尽可能轻地松开手提包,但包落到地上的声音还是让她猛地退后,倒吸一口气,双手捂住了嘴。
“对不起……对不起……哦上帝,加文……”
“到底怎么了?”
他的声音与平日不同:更强势,更有力,更像迈尔斯在工作中处理危机时的语气。
“有人把……我不……有人把巴里的……”
她示意他到家里的办公间里去。那是一个杂乱、简陋却又舒适的房间,巴里以前的划艇奖杯放在架子上,墙上挂着一个相框,照片上八个女孩脖子上挂着奖牌,握拳击向天空。玛丽伸出一根颤抖的手指指向电脑屏幕。加文风衣也没脱便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瞪着帕格镇教区议会网页上的留言板。
“今天上午我去了熟食店,莫琳·洛伊告诉我有许多人在网站上贴了慰问信息……所以我登录上去,想留言谢谢大家。结果——看……”
她说话间加文就已经看到了。西蒙·普莱斯不适合参选议会,发帖人巴里·菲尔布拉泽的鬼魂。
“耶稣基督。”加文厌恶地说。
玛丽又哭了起来。加文想重新抱住她,却又不敢,特别是在这么一个处处能看到巴里痕迹的地方。于是,他转而握住她纤细的手腕,带着她穿过客厅走进厨房。
“你需要喝一杯,”他用自己所不熟悉的强势命令语气说道,“奥古蛋白①饮料。东西在哪里?”
①奥古蛋白,即SOD(Superoxide dismutase),学名超氧化物歧化酶,是一种源于生命体的活性物质,能消除生物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
没等她回答,他就想起来了。他曾好多次见巴里从橱柜里拿出那几个瓶子,于是轻车熟路地为她调了一杯杜松子酒和奎宁的混合饮料。就他所知,她在饭前只喝这个。
“加文,现在才下午四点。”
“谁在乎?”换上新嗓音的加文说,“喝下去。”
尽管还在啜泣,玛丽仍然忍不住笑了一声。她接过杯子,小口地喝了起来。加文拿起纸巾为她擦掉脸上和眼里的泪。
“你太好了,加文。你不想喝点什么吗?咖啡或……或啤酒?”她问,又忍不住轻笑一下。
他从冰箱里给自己拿了一瓶啤酒,脱掉风衣,挨着厨房中间的餐台坐在她的对面。过了一会儿,喝完大半杜松子酒后,玛丽再次平静下来,恢复了加文熟悉的样子。
“你认为是谁干的?”她问。
“某个混蛋。”加文说。
“现在他们都在抢他在议会里的位子。像往常一样为了丛地的事情争论不休。而他还在那里,还在发表他的看法。巴里·菲尔布拉泽的鬼魂。也许真的是他,在留言板上发帖?”
加文不知道她这句话是不是开玩笑,只好微微一笑,避免评论。
“要知道,我愿意认为他在担心我们,不管他在哪里,担心我和孩子们。但我怀疑这一点。我敢打赌,他更担心的是克里斯塔尔·威登。如果他真的在那儿,你知道他最有可能对我说什么吗?”
她将杯中剩下的饮料一饮而尽。加文觉得自己调制的时候并没有放太多酒,但玛丽的两颊已经出现了绯红。
“不知道。”他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他会告诉我,我不是孤单一人,”玛丽说。令加文意外的是,在他一贯认为温柔的嗓音里,竟然听到了愤怒。“是的,他很有可能会说:‘你有所有的家人和我们的朋友,还有孩子们来安慰你,但是克里斯塔尔,’”玛丽提高了嗓门,“‘克里斯塔尔却没有任何能照顾她的人。’你知道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天他在忙什么吗?”
()
“不知道。”加文只好再次这样回答。
“他在为地方报纸写一篇关于克里斯塔尔的文章。克里斯塔尔和丛地。该死的丛地。要是能永远不听到这两个名字,我绝不会嫌那一天来得太早。我想再来一杯杜松子酒。我还没喝够。”
加文机械地拿起她的杯子,惊讶万分地走到放酒的橱柜边。他一直以为玛丽和巴里是完美婚姻的楷模。他从来没想过,玛丽并不是百分百支持她那大忙人丈夫的每个冒险和每次远征。
“傍晚进行划艇训练,周末开车送她们去比赛。”她说,伴着加文往她杯里加的冰块发出的叮当声。“大多数晚上,他都坐在电脑前面,试图劝说人们支持他帮助丛地,要么就是为议会议程添点儿料。所有的人都在说,‘巴里真棒啊,为大家做了这么多事,热心地做志愿者工作,为社区尽心尽力。’”她喝了一大口掺了奎宁的杜松子酒,“啊哈,真棒,棒极了。直到他送了命。结婚纪念日那天,一整天,他都在拼命地写,生怕误了那愚蠢的稿约。而他们现在还没把那篇文章发出来!”
加文无法把眼睛从她脸上挪开。愤怒和酒精让她的脸恢复了血色。她坐得笔直,而不是最近常有的躬身驼背的样子。
“他就是那样才送命的,”她清楚地说,声音在厨房里略微回响。“他把自己的一切给了所有的人。只除了我。”
巴里的葬礼过后,加文一直带着深深的心虚在想,若是自己死了,在社区里留下的空洞肯定相对小得多。此刻,看着玛丽,他开始觉得一个人的死亡在另一个人心中留下巨大的空缺是不是更糟呢?巴里知道玛丽的感受吗?他没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吗?
前门很响地打开,加文听到四个孩子进来了:谈话声、脚步声,然后是鞋和书包扔在地上的声音。
“嗨,加文。”十八岁的弗格斯跟他打了个招呼,一边吻吻妈妈的额头。“你喝酒了吗,妈妈?”
“是我的错,”加文说,“要怪就怪我吧。”
菲尔布拉泽家的孩子是那么乖巧。加文喜欢他们跟妈妈讲话、拥抱她、彼此交谈和与他聊天的方式。他们开朗、礼貌又有趣。于是他不由又想起了盖亚,想起她刻薄的插嘴、如碎玻璃般锋利的沉默和冲着他的大嚷大叫。
孩子们拥进厨房翻找饮料和点心时,玛丽说:“我们还没谈保险的事儿呢。”
“没关系,”加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又匆忙纠正自己,“我是说,我们可以去客厅或……”
“好。”
从厨房的高脚凳上下来时,她踉跄了一下,加文赶紧扶住她的胳膊。
“留下来吃晚饭吗,加文?”弗格斯问。
“请赏光,如果你愿意的话。”玛丽说。
加文心中涌过一股暖流。
“荣幸之至,”他说,“谢谢。”
4
“令人悲伤,”霍华德·莫里森坐在壁炉前,轻轻摇晃着身体,“十分令人悲伤。”
莫琳刚刚讲完凯瑟琳·威登的死讯。当晚早些时候,她从她在医院当接待员的朋友凯伦那里得知了事情始末,包括凯斯·威登的孙女对医院的不满。一种高兴而又鄙夷的表情堆积在她脸上,在心情极度不好的萨曼莎看来,她的脸看上去活像一颗落花生。迈尔斯按传统表达出惊讶和同情,雪莉却面无表情地盯着天花板,她最恨莫琳抢风头,站在舞台中央向大家公布本该她第一个得知的消息。
“我妈妈是那家人的老相识。”霍华德告诉萨曼莎,虽然后者早就知道了。“那些霍普街上的邻居。凯斯算是个体面人。她的房子总是一尘不染,而她自己一直工作到六十多岁。是的,不管她的家里人最后变成了什么德行,凯斯·威登倒是个靠自己汗水吃饭的人。”
霍华德喜欢在适当的时候赞美一下别人。
“钢厂关闭后,凯斯的丈夫失了业,整天喝酒,她的日子可不好过。”
萨曼莎几乎再也装不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样子,幸亏此时莫琳插话了。
“《公报》已经盯上贾瓦德医生了!”她沙哑的大嗓门突然响起,“想想连报纸都扯进来了,她该是什么心情!那家人不会善罢甘休,不过,也不能怪他们,是不是,毕竟人单独留在屋里三天才被发现。你认识她吗,霍华德?哪个是丹尼埃尔·福勒?”
雪莉站起身,腰里系着围裙,大步走出了房间。萨曼莎喝了一口酒,脸上露出了微笑。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霍华德说。他一向以几乎认识帕格镇的每个人为傲,但威登家的年轻人们按理说更属于亚维尔。“不可能是女儿,凯斯只有四个儿子。我猜应该是孙女。”
“她想要官方介入调查,”莫琳接着说,“这样的纠纷总会走到这一步。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若说有什么意外,我只是有点吃惊会花这么长时间。有一次,贾瓦德医生不肯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