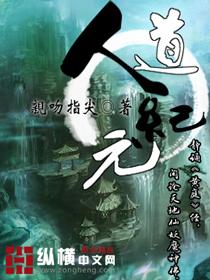嫌疑人-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她穿过道前去寻找她前夫时,李荣出现在她身边,他把手放在了她的右肩膀上,那时候,他的手显得像一块石头,很沉重在想把她抓住,当他说:“你的前夫已经跟你没有关系时,”她笑了,她说道:“你又嫉妒了,看到你为此嫉妒的模样,我真高兴,这正是游戏……”当他抓住她的手臂问她这场游戏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结束时,她诡秘地一笑,轻轻地挣脱了他的手说道:“快了,游戏开始以后总是会结束的。”
他松开了手,然而,他并没有离开,陷入她魔法中去的男人在那一刻正像她所言称的一样,被嫉妒笼罩着。嫉妒是一种从我们的肉身上产生的与他人和事物密切相连的情绪,这种情绪如果附在我们体内,就会每天吞噬着我们的血液,同时吞噬着他人的世界。然而,嫉妒一旦附体,我们被置在其中,我们就不会设置一座个人和他人的密切相连的监狱。
她往前走,他也往前走,因为他们已经陷在监狱中,他们已经无法在这一刻彻底地抽身出去。不知道为什么,当女人走到音乐家客房门口时,手却没有伸出去,李荣好像是头一次看到他情人的迟疑。
其实她并没有迟疑,她不过是在倾听而已,想倾听到客房中细微的声音的那种神态,在那一刹那间突然把她笼罩了。她忘掉了一切,忘记了在不远处的李荣,她的脸,已经反复地被专业美容师修整的脸,显现出了线条的美丽。那些美使她贴近了屋内的声音,如果屋内确实有声音的话。
就在这时,她的前夫从走廊上走来了,就他单独一个走过来了。站在门口的女人突然愣了一下朝着相反的方向:那是通往电梯的走廊,那是通往楼梯的走廊。这完全出乎李荣的意料,按照女人的禀性,她应该迎面而去,事实却恰好相反,她朝着相反的走廊处消失了。
《嫌疑人》第二十六章(2)
接下来,李荣面对面地质问女人为什么面对她前夫却逃避时,女人回到了客房。门铃一响,女人奔过来开门,她突然投进李荣的怀抱,浑身颤抖地说:“我怎么也没有勇气朝着他迎面走去,我怎么也无法单独前去面对他一个人。”女人之所如此地脆弱,是因为她已经对自己没有了信心,当她被饭店中的与前夫有关的热烈的、喧哗的的气氛所包围时,她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失去了这种信心。于是,她不得不改变技法这是她的天性,她可以利用窥视术走近前夫,这样一来,李荣也就丧失了与她前夫的面对面的所谓竞技和决斗。
其实,他感觉到无聊极了,因为女人的技法改变之后,女人在暗处窥视着她的前夫,而他呢,却不得不也在暗处窥视着他的情人。这种恶作剧让他感到无聊,也许他感到羞辱和快失去了尊严。正当他再一次感到无法忍受无聊而准备离开时,他在窥视中看见了这样的场景。
场景发生在音乐会散场的时候,因为游戏规则,李荣和情人的座位都隔开了,这是有意识地隔开,因为惟其如此,他们才会毫不妥协地由窥视到观望,尽管如此,他们隔得很近,女人坐在前排,他坐在后排,在叉开的位置中,女人并没有回过头看见他的存在,在这里,女人正在全神贯注地等待着音乐会的开始,女人出发的时候带了那架德国照相机,她是不可能错过这场音乐会的,为了这场间乐会,她似乎已经等待了太长的时间。在整座音乐会的过程中,女人的身体不时地随同音乐的变幻而晃动,女人已经在她前夫的音乐中寻找到了根深蒂固的,不可从她身体中剥离而去的名誉和激情。而当音乐家会散场的那一刹那间,让李荣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她突然站了起来,天知道从何处冒出来一束百合花,那种艳红的香味即使隔得很远也能够熏倒一批听众,事情就是这样,音乐家的前妻不顾一切地怀抱着花在掌声中站在了舞台。在再次涌起起来的掌声之中贴近了让她灵魂失散的前夫的面前。她是最后一个献花者,随即幕布合拢,舞台消失了。
《嫌疑人》第二十七章(1)
那天晚上,李荣再也无法见到他的情人,他本以为女人上台献花后很快就会从舞台上撤退,哪知道幕布却在那一刹那间合拢了。难道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吗?为什么幕布会在那一刹那间准确无误地合拢呢?这真是一个无法解开之谜,也是他不愿意解开的谜。那天晚上,当他回到饭店里,他到外面寻找着女人,他找遍了饭店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未见到情人,他的手放在了另一道门上,那是音乐家住的客房,那是一道让他体内蓄满嫉妒之花随时随地都会在燃烧的门,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没有人前来开门,而且他判断这房间里昨夜根本就没住上任何人。
这就更加令人费解了,他的情人和音乐家都彻夜不归,难道他们真的已经在幕布合拢之后消失了吗?正当他准备驱车出去寻找时,一男一女从大厅外的旋转玻璃门内走出进来,玻璃门一前一后地旋转着他们的身体,女人站在大厅中央沮丧地盯着音乐家的脸说道:“难道你真的对我失去了信心了?”音乐家冷静地站着,不时地摇了摇头,听不清楚他在嘀咕些什么。他不时地摆摆手,女人就这样站在大厅中央的聚光灯下凝视着音乐家的脸,直到音乐家进了电梯。
很显然,音乐家已经拒绝了他的前妻,这种现象让生活在嫉妒中的李荣多少获得了一种心理的满足感。这个时刻,他出现在大厅中央,出现在已经被弄得万念俱灰的女人面前时,女人抬起头来对他说:“你都已经看到了,你都已经在暗处看到了什么?”尽管如此,她还是跟他走了,他们似乎都不想继续住饭店了,他们想在黎明即将到来时驱车离开这里。
女人没有倾诉,幕布合拢之后她和音乐家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坐在车厢,开始闭上双眼假寐,其实,他的灵魂一直清醒着,他们重又回到老地方,女人期待中的男人之间的决斗没有发生,女人所期待的幻想也没有实现。有很长的时间,房间里也听不到那音乐的声音,女人迷恋上了看影碟。她盘着纤长的腿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开始白天黑夜地看影碟,这正是李荣所期待中的事情,他希望他的女人,就像一只受伤的蝉一样不发出蝉音,也不发出游走的信号,在属于蝉的一个小世界中开始悄无声息地疗伤。因为他对这个受伤的女人依然充满了爱意和同情,他已经习惯了每天回来时呼吸到从她体内散发出来的那种疗伤气息。一个女人,每天都在家里盯着影碟翻转。不停息地睁大眼睛感慨,沉溺于别人的世界和命运之中去,李荣忽视了一个问题:人他情人被控制了,被别人的命运所控制了。
终于,他的情人开始在影碟中获得了人生的灵感,她的整个身心都在反复地演绎着那些平庸的、艺术的碟片中关于男人、女人;关于阴谋和告密的镜头,当她停止看影碟片的时刻,也正是她的命运仿效别人的时刻。她不可能变成蝉,她把那些影碟推开的时机已到,她又一次地消失了,但没有留下短简,因为忙碌,因为疲惫,这一次他没有出发去寻找。
现在,又到了该告别的时刻了,李荣说他明天将离开,他已经实现了看母亲的愿望,他说:“你母亲还在医院,有你在她身边,我看起来可以离开了。我知道你和我母亲的故事是没有结局的,那些风一样呼啸般的故事已经弄得我很疲惫,我已经决定放弃你母亲了。很多故事,你去问你母亲吧,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你的嫌疑人。然而有一点是可能肯定的,没有一个女人像母亲一样想疯狂地想占有你父亲。”
然后,他离开了。看来,他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在故事中他并没有决斗,但却因为母亲参与了一系列活动。范晓琼回到母亲身边,母亲的眩晕症已经缓解了。当她们离开医院时,范晓琼加紧了跟随嫌疑人的步伐,一个女人,虽然是她的母亲,在理性的意义上却是嫌疑人,为此,当她们以一种缓慢的姿态开始乘火车的时,母亲严肃地告诉她说:“我知道你想听什么,我知道你想从我身上搜寻到什么,我会把什么都告诉你,我喜欢乘火车,当你父亲活着时,我喜欢乘飞机,翅膀是多么快啊!只要飞机的翅翼在空中一震动,我就会到达你父亲的身边……而现在,让我们乘火车去看你父亲吧!”
这正是范晓琼之愿望,她们上了火车,她们坐在一包箱中,之前,母亲就让她订下了火车包箱,母亲暗示她说:“包箱很重要,因为它隐蔽,就像我跟你父亲从前的关系一样很隐蔽,因为只有在一个很隐蔽的环境中你父亲才会见到我,我也因此才会见到你父亲……”母亲的声音中仿佛隐藏着范晓琼已经在质疑中触摸到的一种杀机。她跟着母亲上了火车,当母亲知道李荣已经在之前离开时,她沮丧的脸终于转向了另一边,那也许正是父亲的墓地。
火车的包厢使她们拥有了一个私秘的空间。母亲似乎又恢复了体力和味觉,语感和回忆的力量。在这里,私秘的空间显得很贴切,这正是范晓琼触手可及的一种光线,幽暗而朝前晃动,这是火车厢中的惯性力量使她们朝着这晃动的身体,这也是火车厢中忽明忽明的光线。其次,她们置身在旅途,旅途应该就是这样:仿佛被叠起的帆布帐房矗立起来了,随即她们可以随着风的呼啸而去,也可以被云托在雾中。
满世界涌来的雾,扑进了包厢。
在这包厢中需要三种东西:第一是香烟,为此,在火车即将开出的三分钟前,范晓琼下了车买了几包地道的女式香烟,因为从李荣描述中,她看到了一个吸女式香烟的女人,这是一个在阴霾中伸出手指夹住香烟的女人,一旦她喷吐香烟雾团的时候,也正是她沉濡于妄想的时候,她的妄想症笔直地沿着父亲的轨迹前行,有了香烟雾幔的笼罩,这个女人就会变幻出她演驿过的魔法;第二是红酒,女人都会在红酒衬托中变得灿烂起来,母亲当然也不例外,她在餐厢中租借了两只高脚杯,范晓琼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女人,她知道用纸杯喝红酒的感觉是错位的;第三,是磁带,那些纤巧的磁带就放在她包里,这是她惟一可以选择的地方。
《嫌疑人》第二十七章(2)
母亲一钻进包厢就从坐在窗口,她拉开车窗。母亲说:“我知道你怀疑上我了,所以,在这火车上我会把什么都告诉你,因为我已经别无选择了。”母亲微垂下头,她的发质因染发、烫发而变得有些零乱,其实,当女人的头发开始乱了时,并不是因为外在的原因,而是心灵的零乱使发丝相互缭绕,互相纠结。
包厢的距离很近地使母亲和范晓琼身不由己在站在一块,两人仿佛在大海中漂泊了很长时间,他们开始回到岸上。人之所以需要彼岸,就像海潮回到了大海又涌向了岸,我们无法确信潮汐延续的力量到底有多持久,然而,在它们到达彼岸的一刹那,它们带着询问的神色四处张望。母亲掐灭了手中的烟蒂,这是第三支香烟了;范晓琼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看上去,让一个嫌疑人开口并不艰难。
艰难的是陷在真相中的实景:如果母亲就是那片实景镜头中的女主角,那么现在她应该回忆还是缄默,面对范晓琼紧追不舍的步履,面对着自己已经开始变乱的发质,母亲的嘴唇终于开始了嚅动。火车厢沉重的轰鸣声一阵又一阵地敲击着车窗和耳朵,每轰鸣一声,母亲的叙述便会出现一阵高潮,对于这个女人来说,缺乏人生中的高潮,生命似乎就会变成僵尸,所以,她绝不妥协,绝不松手。
她虽然失去了舞台,却具有表演的欲望,那么,她必须寻找到舞台,父亲的存在让她又一次望见了舞台,然而,她需要作出一种姿态,因为她只想跟父亲站在他们舞台上表演内在的一切戏剧,就这样,越贴近父亲的影子,她越加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
对母亲这样的女人来说,越是贴近了父亲的时刻,她越加充满了仇恨和欲望。所以,范晓琼一刻也不放松地盯着母亲:这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谜团,她怎么也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找来找去,母亲竟然变成了嫌疑人,然而,当母亲开口说话时,范晓琼不再盯着母亲了,她仿佛看母亲在表演。
《嫌疑人》第二十八章(1)
为此,在这个世界上,范晓琼得出了一种结论:母亲就是这个世间表演一切欲念的女人。镜头应该倒转,回到母亲所揭开的与父亲之间的秘密战争中去,两性之间的战争通常是私秘的,它只发生在属于两性自己合伙而演出的舞台,在这舞台上没有观众,因为无观众,使他们可以放纵地表演。一放纵,就面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