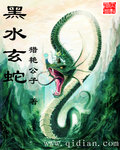蓝色响尾蛇-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四
当余恢和缪小姐在进行谈话时,另外一个座位上有一个人,正在用心地窃听着他们的对白。这个人的位子,距离他们并不很远。地位是在缪小姐的背后而面对着余恢。这个坐在他们背后的人,走进这所看台,是在他们之前,抑或是在他们之后,这却并没有人知道,所可知的,这人对这谈话的一对,显着十分的注意,一种非偶然而近于鬼祟的注意。
此人也穿着白色的夏季西装,叠起了一个德国式的啤酒大肚子;那件衬衫,包在他的肚子上面,像是一张包水果的包皮纸。他有一个近五十岁的秃顶,圆圆的脸,眼睛像是两条缝。他的全身的线条,完全像是漫画上的线条。
此人不时撑起他的狭缝般的眼皮,在向余恢凝视。这里余恢每次被他看着,便来不及地把视线避开,而脸上也格外增加了不安的样子。
缪小姐正把眼光送到那片水波上,她忽旋转脸来重新再向余恢问:
“你说今天有个特别节目呀?”
“奇怪,看这样子,不像有什么特别节目。而且,我的朋友也没有来。”他把眼光停留在身旁的纸包上,想了想,他又说:“如果你肯走下池子,那么,全场的人,将有一个临时的特别节目可看了。怎么样?英!”
缪小姐微笑摇头。她的水波那样的眼珠,重新融化在那片水波上。
这里问答的时候,那个圆脸的家伙,正从一只三炮台的纸烟壳上,撕下一点纸来,取出一支铅笔,写了几个什么字。写好之后,他向一个侍者招招手,等那侍者走到他的身前时,他把纸片交给他而轻轻向他说了几句话。
这家伙的狭缝似的眼睛,随着这侍者的身子移动到余恢的桌子上——神情愈弄愈可异。
那个侍者把一杯冷饮托在一个盘子里,送到了余恢的座位上。余恢因为并没有唤这冷饮,正感到惊异而想发问,一眼看到这盘子里面,放着一块碎纸片,纸片上有几个铅笔写的字。他猛然抬起头来,向那个圆脸的家伙看了一看,立刻他的脸上泛出了一种死灰似的颜色。
可是凭栏外望的那位缪小姐,却并没有注意这个短镜头中的变化。
这时池子边上又有年轻的女子,用一个鲤鱼打挺的姿势,轻捷地滑进水内;——“控通”——水面开了一朵花。四周的掌声与水响交织成了混合的一片,对方池边有三个学童挤坐在一处,他们的身子虽已被水浸软,可是狎水的兴趣还没有尽。看见有人下水,他们不及拍手,六条腿在这大盆子里——“轻控”,“轻控”,——像幼孩洗脚似的乱踢着这水波,而让水花飞溅起来。只见那一大摊闪耀于阳光下的蓝色碎玻璃,也让这些池子里的鱼儿越弄越碎。
栏以外的水之音乐与图画,在这女游泳家的脸上引逗起一种兴奋的薄红。她在太阳光中,闪动着她的长睫毛。看样子,像一个被阻弄水的幼孩在眼看别的孩子自由弄水。她几乎要向池子里扣一阵手,以显示她的羡慕。余恢乘机向她说道:
“看你这样高兴,何不也去试一试?”语声把水面上的灵魂唤回。她的脸色又变为沉郁。但对方不等她摇头,马上又恳切地说:“从今以后,我们恐怕很不容易再见面。也许,我将永远没有机会,再看到你像从前一样的游泳,你能不能答应这个末次的请求,让你的朋友,得到一些快慰?”
说话的时候,他的眼角,显然已装满了伤感的情调。最后他又补充:
“我想,这难得的一次未必就会发生问题吧?”
缪小姐向他看看,双方眼珠在经过一个短而难堪的接触之后,于是她说:
“但是我没有游泳衣,你知道我的脾气,从来不喜欢使用租借来的东西。”她这口气,较之最初的严词拒绝,显然已经活动了许多。
“游泳衣么?有,有——我这里有!”余恢慌忙指指那个身旁的纸包:“而且这是新的,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和你的身材,大约也很相配。”
“你带着女式的游泳衣?”缪小姐显然有点惊异了。
“我告诉过你,我在这里等一个朋友。——一个女朋友。”余恢低低地说。他的眼光看着桌子。
这个情形,假使发生于五年之前,也许这故事中的对白,决不能如此简单。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因之,虽然缪小姐的心里,或许有点怀疑,或许竟有点不快。可是她也不再追问,实在她已无法追问。她自管自打开纸包,取出了这纸包中的一件紫色毛织品的游泳衣,在她身上比了一比。这表示她的心坎里,已被对方的话所打动,因之,她对余恢的请求,已在无言中表示接受。但,她是一个五年前的女游泳家,对于这里的情形,似乎已不很熟悉。于是,她向一个侍者招招手,把他唤过来,问了几句话。
当缪小姐向侍者说话的时候,那个圆脸而带漫画线条的家伙,却用一种狞恶的神气看着余恢。他像在发怒,像在冷笑,又像在期待着什么。
这里缪小姐向余恢问:“你呢?”意思问他是否下池?
“我,我吗?——”余恢伸手抚着头,皱皱眉。
缪小姐不知想到了什么,她没有再问。
那边的圆脸家伙在轻轻地咳嗽。
余恢尽力地躲闪这胖人的注视,一面心神不安似地向缪小姐说:
“你可以把你的衣服,锁在衣帽间里。还有——”他的眼光落在对方的皮包上。
“我把这皮包交给你吧。”她从皮包里面随手取些钱,交给那个侍者,让他代她去补购游泳券。想了想,她从袒开着的衣领之中,把悬挂在颈项里的一根外国金链取下来。——这链子比一根棉线粗不了许多,上面绾着一个心形的照相盒。
她把皮包重新打开,放入了这一根链子。她苦笑着说:“我还不能把这个东西随便失落哩!”
说完,余恢目送着她的背影。跟着那个侍者从这看台的入口处兜向外边去。
五
不多片刻,那个换上了紫色游泳衣的影子,已从水淋浴室那边兜绕过来,让水边的骄阳直射着她。她用一方紫色的薄绸帕裹住她的秀发。她的赤裸的腿臂,像用乳色透明的石质所雕刻,线条充分健美,虽还没有踏进水内,已让许多条视线在这蓝澄澄的一片水上结起一片网来。
缪小姐站在池子边上,仿佛一个久未登台的角色,一旦重新踏上舞台,有点怯场的样子。她并没有走上那个高高的跳水台,表演她在昔得意的跳水,她只在池边伸直了洁白的手臂,一钻身就进了碧波深处。“控通!”一条紫痕划开了蓝玻璃。刚入水的时候,她的姿态并不活泼,这并不能使人相信她就是五年前与杨秀琼齐名的女游泳家。但是不久,这一条紫色的小鱼,已狎习了这弹性水波而充分显示她的活跃。不多一会儿,她让全场那些游泳健将,获得了一个不平凡的印象。许多目光从不同的角度里集中到一个旋转着的水晕上。有的在议论她的姿势美,有的在向同伴悄悄打听:她是什么人?木板上面坐着几个人,本来已经游泳得够了。看这紫白的浪花推过来时,他们又重新跳进了水内。
先前的那位烛式游泳者,在池的那一端,在张望着这太深的水。
那片经过滤水器滤过的蓝色水波,假使没有人造的浪花加以激动,简直连最深处也清可见底。这时,在这大半个较深的池子里面,完全显示了“桃乐姗拉摩”所摄制的一个最动人的镜头,她有时把全身完全做成一支箭,泼刺地前进,像一枚鱼雷在攻击一艘兵舰。有时她把身子变成一张弓,在水内绕出一个竖直的环子。她稍感疲乏的时候,却沿着池边透出半个身子,让池边上的细瀑似的喷水,淋着她的臂背。同时她也时时抬头,举起得意的眼光,飘送到看台边上,她似乎在向她的同伴发问:“喂,你看,我还没有完全落伍哩!是吗?”
当缪小姐在注视余恢的时候,当然,余恢也在全神贯注看这一道紫色的水花。但是,池子里的缪小姐,在游泳了片晌之后,她在余恢的脸上,忽然发现了一种可异的神情。
这一次,她看到余恢的脸色有点惨白,两眼有点失神,样子好像就要睡下来。——但是,她以为这是错觉。她没有在意。
在另一次兜到池边上时,她发见余恢的两眼,已成为半开半闭;好像他的眼皮上正有什么有分量的东西在压下来,使他无法睁开。缪小姐一面用手臂缓缓拨开水面,一面心里在感到奇怪。她想:他为什么要露出这种疲倦的样子呢?由于她的同伴的态度并不兴奋,这使她的游泳也减低了活跃的姿态。但是她在这个难得获到的机会中,还不愿在兴致未尽的时候就辞别这片心爱的水波,因而她还没有从池子里走出来。
这时,池子四周的观众,包括着那个坐得很高的救护员,都在热烈地注望着她,似乎在给她一种无声的鼓励。——让她多逗留一会儿。
可是在她第三次把眼光送到她这同伴的脸上时,他竟看到一个完全出乎意外的情形;那个凭栏下望的余恢,坐着的样子改变了原状,而完全呈现出一种不习见的姿势。他的两眼完全紧闭,分明已经踏进了睡乡的深处。他的嘴张得很大,远远看过去,还看到他的口角间,像有一些口沫在流下来。
这一个奇怪的画像实在太奇怪了!缪小组的心头有点怦怦然,她情知这里面已发生了什么不很妙的事情。她慌忙跨出池子,就在池子边上把身子轻轻跳跃了几下,让湿淋淋的水淌掉一点。一面她不再假道于先前所经过的更衣室,却就在木板上面拾级而上,慌慌张张走上那座看台。
池子四周的观众,不知道她这慌张的态度是为什么理由?好多条视线都被她的湿淋淋的身子带上了看台。同时看台上的座客,也把眼光集中到了一处。
许多人都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平凡的喜剧;但是,他们不会知道,在这平凡的喜剧幕后,隐藏着一个不很平凡的剧情。
缪小姐走到余恢的身前,她发觉她这可异的同伴,已入于深睡眠的状态,甚至推了他几下也并不醒觉。最后她简直费了一点相当的气力,方始把他弄醒。可是,正当余恢努力抹拭着他的朦胧的睡眼之际,缪小姐忽然发现她的那只皮包,已跌落在余恢的脚边,而那皮包口上的拉链,却已拉开了一半。
这使缪小姐的游泳方毕的肺叶,格外加紧了不规则的扇动。在这瞬间,她好像预感到一种不幸的事件,将要降临到她的头上。果然,在她打开这皮包,匆匆忙忙加以检点时,她发现这皮包中的东西,钱、手表、墨水笔以及其他的一切零星物件,一件也没有少,却单单缺少了一件最重要的东西。——那个藏有她丈夫的照片的心型照相盒不见了!
一颗心在水边不见了;另一颗心也沉入到了冰冷的水底。
在缪小姐不见她这重要物件的时候,这游泳池的看台上,那个带有漫画线条的圆脸家伙也不见了。
但是着急中的缪小姐,却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并且,她根本也不知道,这里曾经来过这样一个行迹极诡秘的人。
六
这小小的事变,当时并不曾在这游泳场的群众之前,引起什么纠纷。缪小姐虽因失落了这一件相当重要的东西而感到相当着急,但是,她尽力阻止余恢把这事情声张出来。因为,假使当众查究这件事,那会使全场的群众,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中,全都知道她的名姓;如果因之而传进那位家庭独裁者的耳内,却是一个不得了的问题。为此,当时她悄悄而来,也悄悄而去。她并没有让这游泳场中的任何一人,知道她就是五年前活跃于水波中的缪英小姐;她也没有让任何一人,知道她在这个蓝澄澄的水边,已遇到了一个相当离奇而又麻烦的事件。
一顶小伞抹上夏季斜阳的余晖遮着她的苗条的身影,踏上了焦灼归途。
一路上,她不但拖着灌铅一样沉重的步子,同时她也拖着灌铅一样沉重的心。切实地说来,她失落这个心形的饰物,较之失落了她的腔子里的血肉的心,还要难堪。因为,这里面是有些问题的。
第一:这颗心,是他留给她的唯一的纪念,论理,她是万万不能遗失的,而现在,她竟把它遗失了。——至少,这是心坎间的一种遗憾。
第二:她的独裁的婆婆,三天两天,常要查看这个东西。——如果查问起来,怎么办?
第三:假如说明这个东西已经失落,那么,问的人当然要说,一件藏放在贴肉的东西,怎会无端地失落呢?——她能把游泳场中的情形,照实说出来吗?
第四:一个被束缚于旧式家庭中的女子,在一种无法说明的情形之下,失落了一件藏在贴肉的东西,这事情钻进了戚友们的十八世纪的耳内,将会产生如何后果?
第五……
失落了那么小的一件东西,引起的问题,竟有这么多!
紊混的思想,像暴风一样在她脑内打着转。
而且,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