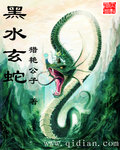蓝色响尾蛇-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五……
失落了那么小的一件东西,引起的问题,竟有这么多!
紊混的思想,像暴风一样在她脑内打着转。
而且,想起这东西的失落的情形,的确非常奇怪。据余恢说:在她走进池子未久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一种异样的气味,从身后飘拂过来,一阵阵送进他的鼻子。——那是一种类似劣质纸烟夹杂着香水里面一样的气味。当时他也曾回过头去,寻找这气味的来源。因为不很经意,他并没有发现身后有什么可异的事物。但,从这时起,就觉得眼皮渐渐沉重,全身异常疲乏,简直无法再作一分钟的支持。他不明白自己在霎时之间,为什么会这样疲倦?虽然心里也曾觉得可异,但是,在他努力振作精神而准备驱走睡魔时,接着他就觉得脑子里面开始剧烈的晃荡,比之晕船还要厉害。他还清楚记得这个时候,眼看池子里的那片水波,像一大片海水在反倒过来。以后,他就完全入于睡眠状态而绝无所知,直等到她把他唤醒为止。——依据余恢这种说法,可见那颗心的失落,非但并不偶然;显见这事情的背后,还藏有一个暧昧的内幕,一定是有什么人,用了有计划的手段,劫夺去了那颗心。但是,谁要劫夺这颗心呢?虽然这是一种从异国带回来的式样新奇的饰物,而实际却并不能值多大的钱。如果劫掠的目的是在于钱,那么在包中的现钞和其他较易换钱的东西,为什么客气地留下?如果劫掠这颗心,目的并不在钱,那么,其他的目的又何在呢?因为事情太离奇,使她不得不从较深的地方推想下去……假定掠夺这颗心的目的,真的并不在钱,那么,除非有什么人,要借这个东西陷害自己吧?但是,有什么人要陷害自己呢?
当时她心头上的一片暗影,曾轻轻落到那位家庭独裁者的身上。但是,这并不可能。因为自己踏进那家游泳场,是由于一种偶然的机会,那个独裁者,如何会在这种偶然的机会中,设下预定机关来陷害自己呢?
接着,她脑子里的黑影,又曾一度恍恍惚惚笼罩到了余恢的身子。但是,想起她和余恢的过去情感,再想起余恢的悠柔的性情,他会做出这种事来吗?他凭什么理由,要拿走这颗心呢?
她立刻阻止自己,赶快不要再从这一方面想。
可是不从这方面想,事情也就越想越不可解释。
正为事情不可解释,她越想越感觉这事情万不能使她放心。虽然余恢在临别的时候,曾以非常焦急而又抱歉的态度,向她担保:在最短时日之内,他将倾其全力代她找回这个东西。但是,他这担保是否可以信任呢?
整个的归途消逝于脑细胞的纷乱的活动上,直到她的身子接近家门,依旧没有在乱丝之中抽出一丝头绪。尤其进门的时候,她的失去了一颗心的心中里面,感到一种空洞的重压。由于这意外事变,她在外面逗留,不知不觉已超过了被许可的时间,她惴惴然,简直不敢正视她婆婆冷酷的脸。
还好,那位家庭中的独裁者,并没有向她提起时间早晚的话。
但是,她偷眼看到那位婆婆的脸上,露着一种奇怪的冷笑,她好像在说:嘿!我已经知道了游泳场内的事情啦!
她是不是真的已经知道了那件事情呢?
七
一种惴栗的心情使她感到坐立不安。这种坐立不安的惴栗,整整延续了两天之久。在第三天上,她的心头略感到了一点轻畅。因为,当时余恢曾肯定地答应,他在三四天内,一定给她一个较可满意的消息。因而她正伸长颈项在盼望这个满意消息之来临。不料,余恢方面的消息没有来,出乎意外地,她竟接受到了一个破空而来的晴天霹雳。那是一封出于意外的信件,信上的措词,蛮横而又无理,文字似通非通,一望而知这是出于一个抹白了鼻子而穿上破靴子的角色的大手笔。并且这信后的具名,觉得脑筋里面,全无一点印象。总之,这完全是一个不相识者所寄来的信。
缪小姐细细展读这封信。她在没有看完这封信时,已经气得手足冰冷,在看完这封信后,她的眼前发黑,差一点就要昏晕过去!毕竟这封信上写着什么东西,让缪小姐看着这样生气?其实,这不但使她无法忍受,就让任何一人看了,也要感到不能忍受。
以下照录原信所有全部的抄文:
郭少奶奶妆次:
风闻女士近来颇多艳闻。最近曾辟室某大旅社四二四号,与电影明星某君会晤,竟以随身佩戴不离之鸡心形照片盒一枚,私相投赠,作为恋爱纪念。此刻物已落于本埠某巨公之手。某巨公以事关礼教风化,勃然大怒!为整饬社会计,拟将此中全部黑幕,在大小各报公开发表,以儆效尤!唯鄙人为顾及尊府名誉,兼为息事宁人计,业已婉劝某巨公暂时息怒,勿为己甚。兹由鄙人函告女士,限女士于十日之中,筹集现款三十万元,交由鄙人代捐慈善机关,以示女士真心忏悔。一面当由鄙人将女士所遗鸡心,连同照片金链,一并奉还,银货两交,决不有误。并代女士严守秘密,决不宣扬于外,倘过期不来接洽,则鄙人等唯有如法办理,完全将此事登报,以凭大众公论。以后女士身败名裂,咎由自取,切莫后悔可也。金钱与名誉孰重?务请三思,幸勿自误!
仆程立本敬上
信后很大胆地留着详细的接洽地址和电话,这地址就是发信人的家,他自称为“程公馆”。
这一封似通非通的吓诈信,充满着一大把好看与难看的字样,也充满着一大把纷乱的人物与事件。最初的几秒钟内,使这位目定口呆的缪小姐,简直弄不明白,这张纸上是在放着什么烟火?她定定神,把震颤不停的手指,努力捉住这意外飞来的信笺,一连看了几遍之后,她方始全部明白纸面上的鬼戏,同时她也渐渐恍然于那天在游泳场中所遭遇到的事件的真相。据她推想:这个写信的坏蛋,就是那天劫夺她那颗心的角色。至于这个角色,怎么会攫获这个偶然的机会,完成他的计划?关于这,她始终无法揣想。总而言之,这个写信的坏蛋,劫夺了她的东西,准备借此敲诈她的金钱,这还不算,另外却要装一些堂堂乎的理由,以掩护他的敲诈的面目。哼!这是一个现代化的策略;从最大的国际人物,到这最下等的小流氓,都是很擅长这一套的!
暗幕揭开以后,有一股青年人的怒火,凡乎焚烧了她的全身!——她觉得假使能把这个侮辱忍受下去,那么,世间将没有一件不能忍受的事情!——难道,自己真的就把这种不可忍受的侮辱,默默然地忍受下去吗?
假使不愿默忍这种侮辱,那么,除非依着地址去找这个坏蛋,向他提出严重的交涉。但是照这样办,那天游泳场中的事件,也势必致于连带宣扬出来。这事件的宣扬,将会得到如何的后果?
她不敢再往下想。
这事情尤其不了的是:自己即使努力默忍下这个侮辱,而这写信的坏蛋,当然不肯让自己默忍下去就算了事。对方费掉许多心力,实行这个恶毒的计划,目的只在于钱,对方不拿到钱,他肯默默然完事吗?
缪小姐看着这信的前半,结果她是愤怒。而想到这信的后半,结果她由愤怒变成了着急。
总而言之,她觉得她在这件事里,已踏进了一个龌龊而又讨厌的泥潭。假使没有钱,那就休想脱身于事外!
但是,钱呢?
郭家虽是出名有钱的人——也就为郭家出名有钱,自己才会遇到这种龌龊的事——然而经济大权,全部操之于那位家庭独裁者之手,自己按月最低度的一些零用,也须在别人手里讨针线。三十万元的巨数,从哪里筹划?何况限期又是那么短。
她越想越觉得这事情的后果的可畏。
在这十万分焦灼之中,她觉得只有一个人可以商量,这人就是余恢。可是余恢方面,却像石沉大海,丝毫没有音讯。而自己在种种阻碍之下,又没有方法可以去找他。
更坏的是,她的那位婆婆,在这两天之中,时时向她透露恶毒可怕的冷笑。她好像有什么话要对她说,而一时还没有出口。她疑心她婆婆已经知道游泳场中的那件事情。她甚至疑心她婆婆在这个陷害她的机关里面,也是参加预谋的一个。她时时提防她婆婆会突然开口,向她查问那颗失去的心。
还有讨厌的事哩!在接到吓诈信的后一天,她又连着接到那个姓程的人的电话。电话里的对白,除了对她加紧压迫,当然,不会有什么使她愉快的句子。
但虽如此,她依然束手无策。——她根本无法筹划那笔钱,她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助她的人。——她,只能伸长颈子,听凭命运的宰割!
可怜!她的一颗心,被捉住在魔鬼的掌握中,而另一颗心,却在冰箱里面打转!
八
在接到吓诈信的第四天,这是一个寂寞而又烦躁的下午。那位寸半本的独裁者,外出去探望一个亲戚,家里只剩下了缪小姐。有一阵电话铃声来自隔空,直刺进这默坐发愁的缪小姐的耳朵。最近,她很怕听电话铃声,每次听到这声音,使她疑惑电线上面,已带来了什么最不好的消息。因之,一听到铃声就让她的心头会狂跳。但是这一次,她在听到铃声以后,并没有看见女侍们进来请她接电话。
停了好一会儿,她看见那扇夏季的纱门轻轻推开,有一个穿短衣的高大的影子,站在门口里面,这是那个新来的汽车夫。
这一个汽车夫,进这里郭宅门里,一共还不到半个月。缪小姐对于这个新汽车夫,颇有一点特异的印象。照规矩,一个汽车夫,总有汽车夫的惯见态度,会在无意之中自然流露;而这个人竟完全没有。他有一双聪明而带冷静的眼睛,鼻子生得很端正。他那薄薄的带点棱角的嘴唇,样子好像很会说话;可是一天到晚,却又并不听到他说什么话。从一般的印象而说,这人简直不像是汽车夫,倒有点像是一位学者。在某些地方,他还带着几分中国绅士的气度。总之,她不很喜欢这个人。她只知道这个人是原有汽车夫的替工。他在这里,仅有二十天或一个月短期的服务。他的名字,叫做阿达。
这时,阿达站在门口里面,目光灼灼地看着缪小姐,缪小姐也呆呆地看着他。她不知道他无端走进来有什么事。
“少奶奶,有人打电话给你,那个家伙自称姓程,——禾旁程。”汽车夫阿达,用恭敬的语声,向她报告。她被这个讨厌的“程”字吓了一跳,就在心跳的时候她听阿达静悄悄说下去:“我已回报他说:‘少奶奶不在家。’”她心里立刻感到一宽。可是她也有点发怒,她想:一个下人,会有这么大的主张,竟敢代主人回报电话。当时,她还没有把这意思表示到脸上,——事实上是阿达不等她有表示这种意思的机会,而已经接连在说:“对不起!我把这家伙痛骂了一顿。因为他对少奶奶的口气非常无理。”
缪小姐脸上满露惊慌。她情知这个挨骂的东西,就是写信来的坏蛋程立本。她不知道这个汽车夫是怎样的得罪了他?尤其担心这坏蛋在受到得罪之后,不知对于自己将会发生怎样的反响?她一时说不出话来。可是,她看看这个擅作其主的汽车夫,见他满面严肃,冷静的目光,一点没有表情;尤其他的口气,显得十分自然,这不像下人和主人在说话,倒像和一个最稔熟的朋友,毫无拘束地在闲谈。
这态度引起了缪小姐的显然的惊异。
阿达在报告完了上述事件以后,他似乎在等候这女主人的发落。但是缪小姐却被阻于她的心事而依旧没有马上就发言。
在这沉吟思虑的片刻之间,阿达想了想,忽然冷静地发问:“我猜,少奶奶一定怕见这个姓程的人,是不是?”
他这句越轨而又轻率的话,却将缪小姐的蕴藏未发的怒气,飞速地提了起来。她锐声说道:“咦!你……”她本来要说:“你敢干涉我的事情!”但是,不知如何她在这个汽车夫的严冷的可怕的态度之下,竟把原句改变成了如下的方式:“咦!你怎么知道我怕见这个人?”
“大概如此吧!”阿达的口气,坚凝得像一块铁,他并不曾为他主人的怒声而摇动。
“这并不是你所该问的事。”她的怒火添上了火舌。她疑惑这新来的汽车夫,已从电话里面,发现了她的秘事。她又疑惑这汽车夫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而来窥探她的隐情的。因之,她说话时,变了脸色,语声也增加了更重的分量。
可是,这汽车夫阿达,绝不会因主人变色而影响到他的一丝一毫的镇静,他自顾自很执拗地在说:“我知道,少奶奶非但怕这姓程的人,还知道你最近正有一件很重大的心事。”——他把对方简称作“你”,有时简直遗失了“少奶奶”三个字的称呼。
“赶快出去!”缪小姐觉得这汽车夫的口气,越来越不成话。她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