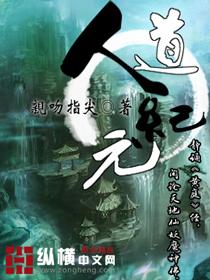无罪的罪人-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想出什么理由,不让我坚持这一不在场证词,但后来我放心了,斯特恩显然也已经意识到,现在再改变立场已经太困难了。我们还必须想出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解释我在那个黑色星期三的失常表现——我为什么会撒谎,我为什么对我的老板、我的朋友,还有两个新上任的检察官大发雷霆。
斯特恩把纸箱拖过去,开始整理里面的文件,他从最上面的物证资料开始。
“我们先来看看最关键的。”斯特恩说,“就是那只玻璃杯。”肯普找来了指纹验证报告的复印件,我们三个一起看着,计算机房的人是在选举的前一天得出指纹比对报告的。当时,波尔卡罗正和尼可暗中勾结,莫拉诺和他们也是一伙,这份报告一定是直接被送到了莫拉诺那里,然后尼可也知道了。所以,那个星期三在雷蒙德的办公室,尼可说他在选举期间就已经掌握了重要的证据,但并没有公开。我猜,他是想最后关头再制造轰动。
报告中简要地说,从杯子上验出了我的右手大拇指和中指的指纹,还有一枚指纹则不知道是谁的。不是我的,也不是卡洛琳的,很有可能是最先到达犯罪现场的某个人的:比如,接到报警后首先到卡洛琳家的巡警,他们总是喜欢在凶杀案警察到达之前碰碰这个,摸摸那个,也有可能是首先发现尸体的公寓管理员,或者是医疗急救人员,甚至可能是个记者。但不管怎样,尼可如果真要解释清楚这个细节,也不会那么容易。
“我想看看那只玻璃杯。”我说,“说不定能想起些什么。”
斯特恩指了指肯普,让他列一张要求查看物证的法庭申请。
“还有。”我说,“我们还得看看所有的指纹鉴定报告,他们在卡洛琳公寓的每个角落里都采集了指纹。”
斯特恩让我自己写这份申请,他递给我一个便笺本说:“申请查看所有鉴定化验的结果,包括所有尚未公开的报告、照片、表格、化学分析鉴定结果,等等,你应该比我清楚。”
我作了记录,斯特恩提出一个问题,“你以前去卡洛琳家的时候,肯定也曾经喝过酒吧?”
“当然喝过。”我说,“她虽然不是很爱打扫卫生,但不至于一只杯子六个月都没洗吧。”
“那倒是。”斯特恩说。
我们都沉默了。
肯普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我认为我们应该找来卡洛琳家所有物品的清单。那个润滑剂是放在哪里的?还有,这个化学鉴定报告里说的那些东西都是在哪里找到的?难道不是应该都放在她柜子里吗?”他看着我,希望我能支持他的想法,但我只是摇摇头。
“我都不记得我曾经和卡洛琳讨论过什么避孕的问题了。你可以说我很大男子主义,但我从来不会问她到底是用什么方法避孕。”
斯特恩又开始思考,空气中飘着雪茄烟的烟雾。
“我们得注意了。”他说,“这些想法都很好,但我们不能让尼可发现他之前可能遗漏了的地方,所以,无论我们提出的申请是什么,都必须隐晦一些。你要记住,检方如果发现了任何有利于我们的证据,按照规定,他们都必须告知我们。而如果我们发现了任何可能对他们有利的证据,我们可以只字不提。”斯特恩斜着眼看了我一下,有点顽皮的样子。他显然很喜欢这种昔日敌人变战友的感觉。又或许,他是想到了他以前从来没有让我发现的某个证据吧。“我们最好自己去调查,而且不能透露出我们真实的意图。”他指了指肯普,这次轮到他写申请报告了,“再写一份申请,要求查看死者房间里所有物品的清单,并请求让我们去看一看死者的房间,那个房间应该封起来了吧?”他问我。
“应该是。”
“还有。”斯特恩说,“你说到卡洛琳的习惯,让我想到一件事。我们应该传讯她的医生。如果她的医生已经去世了,那么医患保密的协议就应该不存在了吧?说不定我们能发现什么呢,说不定发现她一直在用什么药物呢?”
斯特恩还是和往常一样礼貌地问我听没听说过卡洛琳某个医生的名字。我说没有听说过,但所有区政府的职员都是有医保记录的。我建议,对所有的医生都进行传唤,一定能发现不少信息。斯特恩也表示赞同。
我们接下来又开始分析电话记录,都是从卡洛琳家和我家打出的电话,有两三厘米厚的一沓复印纸,全是十四位的号码。我把纸一张一张递给斯特恩。在三月五号、十号和二十号,都有一通一分钟长的电话是从我家打到卡洛琳家的。看到四月一号的记录时,我看了很久很久,我把手指放到晚上七点三十二分打出的那通电话记录上,那通电话有两分钟长。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斯特恩思考着的样子就像在追着一缕烟雾,或是在观察慢慢被拉长的影子。他的口音让他把“一定”两个字强调得恰到好处,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他抽了口烟。
“你在家照顾小孩的时候,一般都干什么?”他问。
“工作啊,看看起诉书、案件资料什么的。”
“那你一定会经常给其他检察官打电话,商量商量案情了?”
“有时会。”
斯特恩说:“你有时会需要问他们一些问题,或是约一个开会的时间。在这么多电话记录中。”斯特恩拍了拍文件,“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电话,是你打给除卡洛琳之外的其他检察官的。”
我不断点着头。
“还有很多种可能。”我说,“那个月,我记得卡洛琳在办一个大案子,我打给她是想了解一下她的工作进度。”
“很好。”斯特恩说。他又看了看谋杀案当晚我的电话记录。他咬紧嘴唇,看上去有点烦恼。
“七点三十二分之后就没有任何电话了。”最后,他指着那条记录,终于开口了。
换句话说,电话记录不能证明我在那之后还在家里。
“不妙吧?”我说。
“确实不妙。”斯特恩终于大声说,“那天晚上有人给你打电话了吗?”
我摇摇头,我记得应该没有,我知道我目前的处境了。
“我会好好想一想。”我说。我把四月一号的电话记录拿过来,又研究了很久。
“这些东西能不能做手脚?”肯普问,“就是这些电话记录?”
我点点头。
“我也在想这个。”我说,“检察院拿到了电话公司送来的电话记录复印件,某个检察官或是其他什么人,想做点手脚,完全可以把某条记录剪掉,再贴上去,重新复印一份,没有人能看出问题来。”我又点点头,看着肯普,“这些东西确实是可以伪造的。”
“那我们应不应该继续查一下?”斯特恩问。他的语气中是不是带有一点点指责的味道?他看着自己衬衫袖子上的一截线头,但当他的眼神从我身上一扫而过时,我却感觉就像镭射激光一样犀利。
“可以考虑一下。”最后,我说道。
“嗯,嗯。”斯特恩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他的表情非常严肃,他指着肯普,让他作一下记录,“我觉得,在州检察院那边的证据尚未定论之前,我们暂时不应该往这个方面查。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我们对这些文件记录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而最后又发现这种怀疑是错误的。”他这番话虽然是对着肯普说的,但显然,是要让我明白其重要性。
斯特恩又伸出手,拿来了一沓文件。他看了看表,那是一块超薄的瑞士金表。我的传讯四十五分钟后就要开始了,斯特恩要提前到达法庭。他建议,我们抓紧时间把证人的情况简要说一说,我大致说了我看完证人名单后的想法。我说,莫尔托和尼可暂时还没有提供任何证词,但另外两个证人,也就是我的秘书尤金妮亚和雷蒙德已经给出了证词。斯特恩心不在焉地让肯普再起草一个申请,他已经把他龟壳的半框眼镜戴上了,认真看着证人的名单。
“你的秘书。”他说,“我倒是不担心,原因我过一会儿再告诉你。老实说,我担心的是雷蒙德。”
斯特恩说到这里,我倒是很吃惊。
“有些证人。”斯特恩解释道,“尼可是一定会让他们上庭的,无论他们对他多么不利。拉斯迪,你当然也清楚这一点,比我更清楚。利普兰泽警官就是一个例子,在选举结束后的那一天,莫尔托找他问话时,他就非常坦诚地说,是你让他不要去查你家的电话记录的。这一点对检方很有利,所以,无论利普兰泽上庭后说你多少好话,尼可也一定会让他上庭。而另一方面,雷蒙德作为证人,我认为,应该不是那种检方会很喜欢的证人。所有的陪审员都认识他,大家都很信任他,让他出庭作证检方冒着很大的风险,除非……”斯特恩停了下来,又拿起了自己的雪茄烟。
“除非什么?”我问,“除非他的证词是对我不利的?我不相信雷蒙德会对我落井下石。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十二年。再说,他能说些什么呢?”
“说什么倒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说。我猜,他是要去证明选举后那一天你在他办公室里说的那些话。我原本以为,如果尼可非要挑一个证人的话,他会去找梅可,至少她过去这十二年来还不算是尽人皆知的大人物。但另一方面,如果雷蒙德作为尼可政治上的对手、作为你十几年来的好朋友和好上司,都站在了检方那边,那结果真是非常不乐观。你和我都知道,就是这种细微之处,才往往改变了一个案子的走向。”
我直直地盯着他,“我不这么认为。”
“我明白。”他说,“有可能你是对的。或许我们遗漏了什么地方,如果能知道雷蒙德会说出什么样的证词,那这些遗漏的地方可能就清楚了。不过。”斯特恩想了想,“雷蒙德会愿意见你吗?”
“为什么会不愿意?”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看看吧!他现在在哪里?”肯普想到了雷蒙德现在可能在的地方,包括六家律师事务所、全国律师联盟,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化团体,这六家事务所是欧葛来迪事务所、斯坦伯格事务所、马可尼事务所、斯里波维奇事务所、杰克森事务所,还有琼斯事务所,“我们应该尽快和雷蒙德见一面。”
很奇怪,这是斯特恩第一次说到一件事让我既完全出乎意料,又无法不去思前想后。确实,自从四月的那一天我从雷蒙德的办公室走出来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但他应该有很多自己的事情需要操心:找新的工作,换新的办公室。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他知道,如果我们联系了,那么,我们之间的对话必须要非常谨慎小心。他的沉默,在我看来,是出于一种职业上的安全考虑。直到现在,连我都在怀疑这一切是不是新检察官用来陷害我的一场阴谋,因为这确实很像莫尔托的作风。
“如果他已经打算让莫尔托上庭作证,那为什么还要叫雷蒙德呢?”我问。
斯特恩说,从原则上来看,莫尔托很有可能不会出庭。尼可已经多次暗示过,会让莫尔托负责审理这个案子。在同一个案子中,律师不能在辩护的同时又担任证人的角色。但无论如何,斯特恩还是提醒了肯普,说我们应该提出申请,如果莫尔托要出庭作证,那么法庭方面应该撤销他律师的身份。如果无意外,这将会给检方一个措手不及,而我曾经对莫尔托说过的那句话也就不能作为证据了。斯特恩和我都觉得尼可不太可能会把那句话真的搬上法庭,但它确实对我很有杀伤力,所以,我们最好先发制人,免得到时候被动。
斯特恩往前探过身。“这个,我就不明白了。”他说,他举起那个女佣的证词,她在证词中说,她曾经在卡洛琳被杀之前没多久的那个晚上,看到我坐在从尼尔林开往市区的公交车上,“尼可让她来说这些话,到底是想证明什么?”
“我们家里只有一辆车。”我解释说,“我敢肯定,莫尔托查过了。那天晚上,巴巴拉开车出去了,所以,我必须以别的方法去卡洛琳家,那就是乘坐公交车了。我敢打赌,他们至少让警察在尼尔林的公交车站蹲点了一个星期,才找到这个认出了我照片的人。”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斯特恩说,“他们显然承认了巴巴拉当天晚上确实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我也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相信是她开走了你们家的车,她们大学附近发生了好几起深夜抢劫案,女人一般都不会深夜自己一个人乘坐公交车的。但他们为什么会相信的呢?检方应该不愿意承认被告居然是坐公交车去杀人的,听起来怎么都不像那么回事。他们一定查了出租车公司和租车公司的记录,什么都没有找到。我猜,他们也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