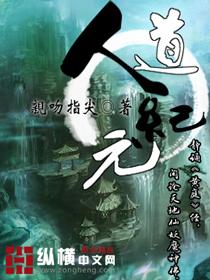无罪的罪人-第5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解释不清楚。她就是有那种力量,而我又是那么软弱。但我很明白,只要她还在我身边出现,我大概很多年都会对她无法释怀,也许永远都无法释怀。我这么说不是要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我也不想假装这其中有什么理由或借口,但至少,我们都应该承认这个事实。”
“我一直都觉得,谈这件事对任何人都没什么好处。我猜,你也是这样想的。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但我总是想,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猜,每一个检察官最后都会发现,我们和罪恶之间的距离比想象的要近得多。幻想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你产生了一个念头,一个精心设计的计策,你每次想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兴奋、很刺激,你不断去想,甚至还迈出了实施的第一步。你觉得更兴奋、更刺激了,所以,你继续下去。最后,你深陷其中,你对自己说,这又没有造成什么实际的伤害。最后,当你感觉到最兴奋的时候,感觉到一种飞翔般的自由的时候,这一切就真的发生了。”
我把目光从墙壁上收回来。巴巴拉已经站了起来,站在椅子的后面。她的表情很警觉,她显然没有料到我会说出这番话。
我还在继续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说出这些话,但我现在说了,因为我想,这些话是应该一次说清楚的。我不是要威胁你,一点儿要威胁你的意思也没有,我只是想把话都说出来。只有上帝才知道你当时是怎样想的,巴巴拉。我不想我们俩继续猜来猜去,猜对方到底知道什么,又在想什么。我不想让这种猜测影响到我们以后的生活。你大概听到我说这些话,也会觉得惊讶吧?但我觉得,这些话必须说出来。原因很多,首先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奈特,我想把这件事给我们生活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除此之外,我还希望你能从那次疯狂的举动中得到一些教训。而最重要的,我想给自己一个解释,卡洛琳到底是怎么被杀的,又是为什么被杀的,是怎样一种缺乏理智的冲动导致了她那样的结局,这太难解释了。我一直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她的被杀是因为我们俩,主要还是因为我。我想说清楚,是想看看这些话对你有意义吗?能让你有所改变吗?”
我终于说完了,我感到一种奇怪的满足,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说出这些话。巴巴拉,我的妻子,在哭,哭得很厉害,哭得很安静。她低着头,泪珠不断地滚落。
她喘着气,“拉斯迪,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只能说一句抱歉,我希望你有一天能够相信我。”
“我明白。”我告诉她,“我现在就相信你。”
“我已经准备好说出真相了,一直都准备好了,从最开始到最后。如果我被传唤为证人出庭,我会说出发生的一切。”
“我知道,但我不希望那样的情况发生。老实说,巴巴拉,你说出真相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你的这番说辞听起来就像是借口,就像是你故意撒谎来救我,没有人会相信你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这些话又让她开始流泪,最后,她终于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她似乎释然了,她用手背擦着泪眼,做了下深呼吸。她低着头,看着餐桌,开口说话了。
“你知道那种发疯的感觉吗,拉斯迪?完全疯掉的感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我觉得我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我觉得我随时会倒下去,我不能再继续这样。如果我和你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我永远都没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知道这些想法很可怕,不管我怎么想,在经过了这件事以后,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拉斯迪,我只能说,这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直到案子开庭,直到我坐在法庭里,直到我看着你所经历的一切,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是真的发生了,我才终于发觉,我一点儿也不想这件事发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的感受。我已经没有正常的生活了,我只感觉到害怕。当然,还有……用‘羞愧’好像也不恰当,应该是‘内疚’吧?”她慢慢地摇着头,低头看着餐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
“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的,你知道吗?”我说。但这话听起来有点虚伪。巴巴拉抽泣了几下。她突然咬紧嘴唇,把头偏到一边,又哭了起来。
她一再摇着头,“我觉得这样不对。”她说,“就这么结束吧,拉斯迪。”
这就是她说的全部的话了。我以为她还有更多话要说,但没有了。她起身准备离开,但又停了下来。我抱住她,抱了很久,最后,她还是挣脱了,我听到她上楼的脚步声。我太了解她了,她会躺在我们的床上,继续哭泣,然后,她会站起来,开始收拾、打包,准备离开。
第三十九节
在感恩节过后的一天,我到市区采购,为圣诞节作准备,我看见尼可在大街上走路。他紧紧拉着外套的领子,皱着眉头,显得忧心忡忡。他似乎在左右看着路上的车辆,他朝我这边的方向走来,但我敢肯定,他没有看到我。我想躲进旁边的大楼,倒不是因为害怕,只是觉得我们两个大概都不想见到对方。但这时他看见我了,径直朝我走来。他没有对我微笑,但向我先伸出了手,我握住他的手。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涌上一种可怕的情绪,痛苦、难受,好在这种情绪很快就消失了。我站在那里,友善地看着这个曾经想毁掉我的人。有一个戴帽子的男人显然认出了我们,他转过身看着我们,但并没有停下脚步,很快,他就消失在街上的行人中。
尼可问起我的近况。他的语气很真诚,就像是大家最近对我说话的语气一样,所以,我猜他已经知道了,但我还是告诉了他。
“巴巴拉和我分开了。”我说。
“我听说了。”他说,“我很抱歉,真的。离婚很难熬,你也知道。我曾经在你面前为这事哭过,我的孩子最后也没有归我,你们俩说不定可以商量商量。”
“我觉得已经没什么商量的余地了。奈特现在跟我住,等巴巴拉在底特律安定下来以后,他就会去那边了。”
“没办法。”他说,“真的,没办法。”我想,尼可还是老样子,什么话都要说两遍。
我转过身让他先走。这一次,我先伸出了我的手。当他握住我的手时,他朝我靠近过来,脸上的表情很凝重,我知道,他接下来想说的话让他觉得很痛苦。
“我并没有陷害你。”他说,“我知道大家都这么想。但我真的没有派人去伪造证据,没有派莫尔托,也没有派熊谷。”一想到熊谷,我又差点退缩了。他现在已经从警局辞职了,他没有退路,要么承认伪造证据,要么承认渎职失误,他选择了比较轻的那项罪名,他的选择是对的。他当然没有伪造精液样本,但如果当时他能多看几眼自己的验尸报告,我大概从一开始就不会被起诉,但没有人能预知未来。也许莫尔托也是有过错的,他太过于急进,案子证据不足,还贸然提起诉讼。我猜,他认为只有我的倒霉才能抚平他的痛苦或者说嫉妒,因为他对卡洛琳也有感觉。
尼可还在继续说,仍然是那么真诚。“我真的没有陷害你。”他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要告诉你,我没有这样做过。”
“我知道你没有,拖拉王。”我说,然后,我告诉了他我认为是怎么一回事,“你只是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做自己的工作,你只是所托非人。”
他盯着我。
“我这份工作大概也不会长了,你听说他们要对我撤职的事了吗?”他问。他又左右看着街上的人群,“你肯定听说了,大家都听说了。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们都在对我说,我的职业生涯算是结束了。”
他不是在恳求我的同情。他只是想让我知道,他也是受害者。卡洛琳把我们俩都拽入了她死后留下的黑洞,我突然很想鼓励他一下。
“说不好,拖拉王,你永远也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
他摇摇头。
“不,不。”他说,“不,你才是英雄,我是狗熊,这挺好的。”尼可突然笑了,我知道,他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奇怪、很可笑,“一年前,你完全可以在竞选中打败我,你现在更加可以。这不好吗?”尼可·德拉·戈迪亚在大声笑着,是对自己的嘲笑,他站在大街中央,伸开双臂,他说,“一切都没有改变。”
第四十节
在这幢我住了八年多的房子里,现在是一片混乱。到处都是纸箱,有的敞开着,有的装了一半,四周都是从书架上、抽屉里拿下来的东西。家具已经都搬走了。我一直就不喜欢那些沙发和双人椅,但巴巴拉希望把它们摆在她底特律的新公寓里。我会在一月二号搬到市区的一处新家,地方不错。房产中介说,我能租到那房子很幸运。我决定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要慢慢来。
奈特已经去了底特律,这些收拾打包的任务简直没完没了。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每一样东西都勾起我的回忆,每一个角落似乎都充满痛苦和忧伤。当我在某一个地方无法承受的时候,我会换一个地方。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也想起了马蒂·波尔希莫斯当初在搬家时的情形。在我母亲去世后的那一周,我发现父亲在收拾整理家里的东西,而这个家是他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抛弃了的。他当时穿着一件无袖的背心,大大咧咧地把自己过往生活的见证装进一个又一个箱子。他在房子里到处走动,遇到堆在路中间的纸箱,会一脚踢开。
我上周接到了马蒂的消息,他给我寄来一张圣诞卡,“很高兴听到你一切顺利的消息。”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大声笑了出来。唉,这个孩子确实很奇怪。我把卡片扔到一边,但随之而来的孤独感却比我想象的还要强烈。几个小时后,我开始在客厅翻箱倒柜,想找到写有他地址的信封,我想给他写封回信。
我从来没有给我父亲写过信。在他离开家去亚利桑那州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偶尔给他打个电话,那是因为巴巴拉拨通了号码,把话筒塞给了我。他根本不想同我说话,也不愿意跟我说他的生活状况,其实也没有必要。我知道他当时在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生活,在一家当地的面包店工作,每周工作三天。他觉得亚利桑那州很热。
那个女人叫旺达,后来,是她给我打来电话,通知了我父亲的死讯。那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但它带给我的震惊却让我一天都无法忘记。父亲曾经是那么强壮,我一直觉得他能活到一百岁。旺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父亲的遗体已经火化了,她是在收拾遗物的时候发现我的电话号码的,她坚持让我去她那里,处理父亲余下的一些东西。当时,巴巴拉已经怀孕八个月了,但我们都认为,这是我能为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于是,我们便去了亚利桑那州。旺达是纽约人,快六十岁了,个子很高,长得并不难看。她说起父亲的时候并没有“口下留情”,我一到,她就告诉我,实际上她在六个月前就已经搬出去了。父亲的死讯是面包店的人打电话告诉她的,他死于冠心病,他们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亲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他找到你。真的,我跟你说。”她喝过了几杯酒后说,“他就是个浑蛋。”
我开玩笑说,这句话应该刻在父亲的墓碑上,但她并没有觉得好笑。
她留下我一个人整理父亲的东西。父亲的床上有几双红袜子,衣柜里有六七十条男士的紧身裤,红黄相间的、条纹的,圆点的,菱形花纹的。看来,在父亲生命中最后的几年,他终于找到了一种嗜好。
门铃响了,我突然感觉一种隐隐约约的期待,我觉得应该是邮递员,我很想和他聊两句。
“利普兰泽,是你啊!”我站在门口和他打着招呼。他走进门,跺掉鞋子上的雪。
“家里不错啊!”利普兰泽一边看着狼藉的客厅,一边说。他站在门口的脚垫上,递给我一个小包,上面还系着一个绸缎的蝴蝶结,包裹本身比那个结子大不了多少。
“圣诞礼物。”他说。
“你太客气了。”我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互送过什么礼物。
“我觉得你应该开心一下,奈特已经走了?”
我点点头。我昨天把奈特送到了机场,他们让他提前登记。我想陪他一起上飞机,但奈特不让。我站在登机口,看着他穿着深蓝色的球衣,一个人孤单单地走着,好像已经迷失在了自己的梦境里。他到底是我的儿子,他没有转过身朝我挥手。我心里是多么希望,多么希望我的生活能够回到从前的样子啊!
利普兰泽和我对视片刻。我愣在那里,忘了接过他脱下的外套。太尴尬了,我最近和谁在一起都是这样,无论是在大街上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