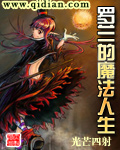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有这些企业中,我们都做小股东。这些企业的管理层常邀请我们去为他们输出管理经理。比如上海光明的王佳芬总经理是在我们到上海后认识的,一谈之后,她对希望的管理经验非常看好。在光明乳业有机会股份化时,她坚决选择让东方希望来参股。而每次董事会上她做决策时都会问问东方希望的看法,也会打电话与我个人进行交流。在光明乳业有一次要进行大规模技改的时候,我们给光明乳业提供了建议,希望他们不要急于采用进口设备而多在国产设备中做一些选择,然后自己动手改造国产设备。
他们听取了这个建议,改变了原来的策略,结果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在上海我有更多的机会来进行资本运作。但出于我自己的原则,我拒绝了许多这样的机会。有无数的经纪人来找我做股票和期货的投资,但我认为社会大众对企业的期望是以实业取胜,企业去做这样的投资多少有点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面,所以一般都拒绝了。
当然,东方希望的资金大量回流的时候我也不完全排斥股票市场,但基本上只限于打新股。因为打新股在2005年之前都是安全的。
对于政商关系,东方希望集团的策略是划一个等距离圆。东方希望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公司之后,政府给了我们很多荣誉,对于这种荣誉,我们不拒绝但很少去争取。因为我们认为只要企业做得好,地方政府会非常欢迎你去投资,政府官员同样需要好的企业效益给他们带来的政绩。因此企业的业绩是企业核心的标志。
在迁到上海之后,我与同事们对东方希望集团进行了精细化管理的改造。事实上,在希望集团早期的管理之中,我已经摸索出很多经验。但在向全国发展的过程中,我有意在一定程度上对管理进行一定的放任,我清楚地知道九十年代中国的养殖业有一个大发展的过程,此时抓住了机会就是抓住了发展的机会。但是到了上海之后,管理精细化是东方希望取得下一步进展的关键,因为此时的东方希望集团已经是一个大公司。大公司在与小企业竞争的时候有一定的劣势,小企业管理层级少,管理成本低,而大企业的管理层级太多,管理成本也上升,决策过程也慢,因此只有管理精细化才能保证其生存。
◆我看三十年
从内心最深处,这三十年来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充满了尊敬,可以说我个人人生中的每一次转折,都与他推行的政策有关。
1977年,正当我觉得自己将会在四川新津县城作为一个电器修理工平凡地度过一生的时候,高考恢复了,给了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以人生最大的机会。高考让我走出了新津县城,从书里看到了世界,埋下了我以后创业的种子。
我们的创业企业“育新良种场”的出现,是因为农村改革开始了,专业户的大量出现使得我们这几个大学生可以到农村创业。而国家放松对农民的管制使得农民可以自由交易也给了我们这个企业生存的机会。
当然,更为重要的关键点在于1992年,其时“育新良种场”正处于从经营企业到企业经营的思路转变过程中。而我们并不知道,当时的政治环境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成都当时的一位市委领导到新津看了我们上交的税收情况,对我们的税收数额很不满意,要求县委查我们的税。一令之下,令我们的企业发生巨大的震动,企业内部人心惶惶。我们几个兄弟也是十分害怕,几乎想把工厂交给政府。是县委的几个领导认为“育新良种场”离不开我们,才让我们保留了工厂,但企业内部员工还是非常不安。而此时,邓公南巡的讲话通过报纸转发,我们看到了这份报纸,并从其中嗅出了味道。所以开始放手大干,有了希望集团在四川范围内,后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张。
我清楚地知道,民营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过程中,走过的是一条非常崎岖不平的道路。它一开始只是社会经济的补充,后来成为有机组成部分,到现在已经成为社会解决就业、构筑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核心力量。在构成中国经济的三大力量中,民营企业出身不好,集中社会力量能力最低,但同样可以做大事,关键是取决于民营企业主的事业心有多大。作为千千万万民营企业主中的一个,我从来不敢期望有多少阳光雨露会洒在我头上,只要石头有一条缝,我就会和我的同事一起拼命往上生长,自己去争取阳光雨露。实际上,社会和政府已经给了我很多机会和荣誉,对于这些,我看得很淡。中国人普遍都信命,而我相信的是,一个努力为自己的使命奋斗的人,上帝都会为他让路。
第03章 步鑫生:第一个“砸”工人饭碗的厂长
【步鑫生小传】
步鑫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企业界最著名的改革典型人物之一。1983年秋,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步鑫生成为当年度最耀眼的企业英雄。
步鑫生本是浙江省海盐县里一个不太讨上级喜欢的人。他从三年前当上海盐衬衫总厂厂长后,就开始在厂里按自己的想法搞改革,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克扣工资,有两个人甚至被开除。他在厂里搞奖金制度,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提出“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很是让一些老工人不满意,时不时的总是有一些告状信写到县里和省里,让他日子很不好过。不过,由于他管理抓得紧,工厂效益不错,生产出的衬衫在上海、杭州一些城市很受欢迎。
步鑫生的命运被一个叫童宝根的新华社记者改变。童在采访了步鑫生和他的厂以后,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内参。谁也没有想到,11月6日,总书记胡耀邦会从成堆的“内参”中挑出这篇报道,写下了一段批示,认为步鑫生的经验可以使广大企业领导干部从中受到教益。随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议、考察,步鑫生的事迹得到最高领导层的进一步肯定,很快,全国各大新闻单位闻风而动,“步鑫生热”平地而起。
步鑫生被选中为典型,有很偶然的戏剧性因素,却也似乎有必然性。当时国内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力量,经济过热现象已被控制,治理整顿接近尾声,重新启动发展的列车,恢复人们的改革热精又成了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情况下,规模不大的衬衫厂及其有小缺点的经营者便“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地脱颖而出成了“学习榜样”。
在一些新闻记者的帮助下,步鑫生很快发明了一些朗朗上口的“改革顺口溜”:分配原则是“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生产方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管理思想是“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经营思路是“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等等。这些朴素而容易背诵的改革格言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许多企业挂在厂内的标语口号和崇尚的企业精神。步鑫生的这些观念对于无数白手起步的民营企业主算得上是一堂最最生动的启蒙课,日后,很多在那个时期创业的企业家都回忆说,正是步鑫生的这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受了市场化商业文化的洗礼。
“步鑫生神话”渐渐生成,他成了一个管理专家、经营大师。通往海盐武原镇的沙石路上车水马龙挤满了前去“参观学习”的人们,当时的步厂长炙手可热,据称,连厅局级干部要见一下他都很难。
在八十年代初的政治生活氛围中,当一个人被中央指定为典型之后,他就很容易“偶像化”。本来就桀骜不驯、缺乏政治训练的步鑫生很快在热浪中迷失了自己,他像英雄一样地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做巡回演讲,在鲜花和掌声中,他开始说一些连自己也听不太懂的话。而在领导和专家们的谋划下,类似“步鑫生服装生产托拉斯”之类的创意不断产生,很多项目没有经过可行性论证就得到了批准并得以实施,步鑫生在看似获得别人难以企及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事实上却踏入了一连串的经营失误。海盐衬衫总厂到1985年就难以为继,而到了1987年11月,海盐衬衫总厂负债1014。 48万元,亏损268。 84万元,而这个厂的资产总额仅1007。 03万元。资不抵债,实际上已经破产。1988年1月,浙江省一个调查组在职工中做民意测验,96%的职工认为步鑫生不能胜任,1月15日,他被免去厂长职务。
被免职后的步鑫生,如敝屣被弃。他出走浙江,到北京办厂三月,不成,再北漂辽宁盘锦,后来,甚至还去过俄罗斯。很快,他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九十年代以后,在一些新朋旧友的帮助下,他一度有复出迹象,但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必须承认的是,“步鑫生热”在1983年年底到1984年年初的出现,让国内沉闷多时的改革氛围为之一振。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等改革理念一时又成了主旋律。
◆大刀阔斧搞改革
大家一说起我,就会想到海盐县衬衫总厂。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前身,是1956年组织起来的缝纫合作社。直至1975年的二十年间,全厂只有固定资产两万多元,年利润只有五千多元,职工连退休金也领不到。1977年我当上了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那时,我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进行改革,使工厂恢复生机;要么就是倒闭。我自然选择了前者。也许是性格使然,我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待事业,反对循规蹈矩和墨守成规,喜欢敢闯敢干和创新进取。我勇于挑重担,不怕闲言碎语。
我确立了“信誉至上,质量第一”的企业宗旨,制订了“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的业务方针。我砍掉了三分之一的行政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鲜明地提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对奖金分配坚决打破平均主义,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在产品经营上,我们坚持创名牌战略,反复强调“靠名牌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企业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我们将上海作为我们抢占“制高点”的首选城市,作为第一家打进上海市场的制衣企业。我们生产的“双燕牌”名牌衬衣于1980年冲进上海市场,并通过上海这个“制高点”辐射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我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产品看样订货会,视客户为上帝,特地从上海租用了几辆轿车,去上海和杭州等地的机场、车站、码头专程接送客户。要晓得当时海盐县委县政府才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车,而我们企业用来接送客户的小轿车有五辆。这五辆小轿车在小小的县城招摇过市,十分显眼。
同样,我们企业也会应邀去外地参加这样的订货会。有一次新疆有关企业邀请我专门参加看样订货,按常规安全得坐火车,来回半个月时间耗不起,我就改乘飞机,来回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所有这些,现在看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在当时却属于“大逆不道”。有些人侧目而视议论纷纷,有些人更是公开指责发难。对此,我做了具体分析,搞这些改革,谁高兴谁不高兴,谁赞成谁反对。我心里清楚。我扪心自问,推行改革对国家对集体对职工三方面都有利,而我自己还是原来的步鑫生.我问心无愧,因而不为众多议论指责所动,他人的非议反而更坚定了我改革的决心。我们企业自办了专业消防队,还千方百计办起了上水平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确保职工生产无后顾之忧。我们还别出心裁地实施了一些看似与生产无关的举措。如设计厂标、制作厂徽、统一厂服、谱写厂歌、举办一年一度的厂庆,组织全国服装企业的第一家具有专业水平的时装表演队。我们去北京举行产品展销期间,时装表演队随展销团同去,并应邀在北京饭店、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专场表演,引起轰动,对企业的服装展销产生了较好的良性作用。
在进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我亮出了自己的决心:大刀阔斧搞改革,呕心沥血抓发展,冒着风险排干扰,不创一流誓不休。“冒着风险排干扰”这一句,不是自己信口拈来,更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在当时政治大环境下上述改革措施哪项不是违规的“犯上”行为?改革,不冒这个风险行吗?不排除干扰行吗?
我们的改革引起了上级的关注。《浙江日报》第二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企业家之歌》为题对我进行报道,这篇报道在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共浙江省委派出调查组来我厂进行调研,给予充分肯定,并写出调研报告上报中央。新华社反映我的“内参”报道后来惊动了中央。
◆“全国最知名工厂厂长”
1983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