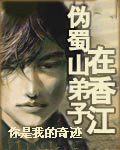香江边上的思考-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够的,而必须具有一些日常性的监督管理权。可中央不掌握香港的财政、税收和司法主权,无法对香港行使日常的治理。基本法赋予中央两项间接的监督权,即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和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任命权。可基本法的解释权本身不能用于日常治理,而行政长官的任命权又由于行政长官的普选目标而受到冲击。
面对这种宪政体制设计本身所带来的困境,行政长官就成为巩固中央与特区关系最重要的纽带,中央不得不牢牢把握住对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命权,而且确保特区的行政主导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否则香港就基本上变成一个“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然而,正是在涉及中央与特区关心的中枢纽带上,基本法的规定本身充满了张力:一方面规定行政长官最终由普选产生;另一方面规定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的任命。可在香港未完成“去殖民化”的前提下,在香港对中央权威的政治认同不足的情况下,激进的普选很容易出现试图在政治上挑战中央权威的行政长官候任人,对此中央政府要不要拒绝任命?如果中央拒绝任命又如何处理由此产生的“宪政危机”?如果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采取“去中国化”的施政措施或采取公投等行动推动修改基本法,削弱中央的主权,甚至推动香港实行自治或更极端的独立,怎么办?这样的担忧绝非空穴来风。人们不会忘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二○○四年四月做出决定否决香港特区二○○七年行政长官和二○○八年立法会“双普选”的决定之后,香港“民主派”竟然学习和模仿台湾,公然推动“全民公投普选”计划,试图以所谓“香港民意”来推翻国家主权者的决定。这不仅很容易被理解为“台湾公投制宪”的香港版,而且手法类似彭定康推行政改方案一样,以“普选”的名义挟持香港市民与中央对抗。人们更不会忘记,二○○七年,“民主派”推出的行政长官候选人梁家杰在竞选政纲中明确宣布,要修改基本法,将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改为议会内阁制并取消中央对主要官员的任命权。当然,人们都相信,即使出现这种局面,也不可能取得成功,但这意味着中央不得不再次直接介入,进行一场没完没了的政治斗争。这意味着中央对香港难以采取常规政治下的有效治理,时刻处于对应危机状态的局面。因此,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采取循序渐进、审慎理性的态度,恰恰是着眼于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防止急速的民主化引发香港的“台湾化”,避免香港陷入政治上的紧急状态而迫使中央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宣布中止基本法,直接将内地的法律适用于香港,这无疑会危及“一国两制”本身。
正是面对香港历史上形成的国家认同不足和基本法中国家主权建构的不足,香港的政制发展就必须在“一国”与“民主”之间达到适度的平衡点。为此,小平在设计“一国两制”时,早就定下两个大的政治原则,来弥补上述两个不足。其一就是积极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政治功能,用政治手段来弥补法律手段的不足,使得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转化为香港爱国者对香港的治理;其二就是要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发展,用时间来弥补政治认同的不足,使得香港市民的政治认同随时间推移和代际更替而不断加强。
二○○三年以来,中央治理香港采取新机制,采用新思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效,其间,香港经历了一系列接连不断的选举。然而,面对未来普选的政治挑战,不仅要增强爱国爱港阵营在选举中的政治实力,更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文化战略,发挥软实力,逐步改变香港民情,争取人心回归,尤其是争取香港中产专业精英的人心回归,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让人陷入难以释怀的忧郁之中。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曾经以何等的政治自信,将香港作为通向西方世界的跳板,并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正当性发起了意识形态的挑战。然而,几十年之后,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被迫采取守势。这种攻守异势既有国际局势的转变,也有国家实力的转变,更有文化领导权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这一代领导人的自信,不是来源于国家的经济实力,而是来源于政治正当性的正义原则,即共产主义信念所支撑的“民主”原则和“平等”原则,由此不仅能凝聚人心,而且始终掌握着话语主导权。可以说,整个“冷战”话语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原则与资本主义阵营的自由原则之间的较量。
起初,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原则占据了上风,第三世界尤其是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这种“民主”和“平等”原则下展开的,美国因为种族隔离、英国因为殖民统治而丧失了政治正当性。为此,英国步入非殖民化时代,美国为了打赢这场冷战而被迫取消种族隔离,由此六十年代美国兴起的人权运动被称之为“冷战人权”(cold war rights)。在这场“民主”与“自由”对抗的冷战背景下,西方思想家一方面在政治哲学上极力诋毁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民主原则,将民主等同于“多数人暴政”和“极权专制”,从而把所谓英美自由主义推向了神坛;另一方面也对民主原则进行技术化处理,将民主原则等同于代议制选举,并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将“民主”概念变成所谓的“宪政民主”,从而重新夺得了民主话语上的主导权。
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世界努力争夺“民主”话语的主导权不同,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首先采取了“硬着路”,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并拱手让出了“文化领导权”,丧失了对“民主”概念的解释权;接着又以“不争论”的方式处理政治正当性问题,致使中国政治丧失了政治正当性原则的是非辩论,窒息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活力,陷入了庸俗的市侩主义;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传统所树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团结友爱和无私奉献的伦理思想,受到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的冲击。我们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新兴精英阶层在全球化的经济生活中享受短暂的和平和私人的快乐,以一种非政治化的天真在全球化的空洞许诺中丧失了政治意志、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主,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界定权和对生活方式的辩护权,只能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认。
从一九八二年香港回归谈判到二○○三年大游行这二十多年,香港在政治上和地缘上处在大陆的边缘,可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却处于西方世界主导的中心地带;随着内地经济的崛起,香港在经济上开始出现边缘化倾向,但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占据了民主、自由和法治话语的中心地带。这样一种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错位与反差恰恰是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忧郁所在。中国人即使在最为困顿的时代,内心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明中心的高贵追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天下的思考,可在近代以来的实际政治环境中却不得不沦为被支配的边缘地带,难以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辩护,由此产生难以释怀的忧郁。这样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容易因为过分自尊而产生孤立主义的民粹倾向,也很容易因为过分自卑而产生普适主义的投降倾向,这两种倾向又往往以极左和极右的方式展现出来,二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张力不断拷问着中国人的心灵,使得近代以来的整个中国史不断经历着“成长中的阵痛”。与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一样,香港历史上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回归道路以及回归以来的一幕幕悲喜剧,不过是这阵痛的一部分而已。
“要使一个事件有伟大之处,必须汇合两个东西:完成它的人的伟大意识和经历它的人的伟大意识。”尼采认为这些“不合时宜的沉思”是写给未来的。
从康熙皇帝驳回了重修万里长城的一刻起,他并不在意自己着手奠基的“一国多制”的宪政模式已经超越了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但他触及到这样一种伟大的意识,即政制必须建立在人心之上,且将人心导向高贵境界可能有多种途径,因此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政制或文明必须能够容纳不同文化形态所蕴藏的将人心导向高贵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对各种可能性的尊重和包容,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天下大同”。因此,真正的天下大同不是罗马帝国的同一性扩张形成的“永久和平”或“普遍的均质性全球国家”,而是儒家主张的“和而不同”(参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九”)。当毛泽东晚年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时,他的意识早已超越了万里长城,触及到“共产主义”这个天下大同之境。然而,这个境地究竟是同一性的均质状态,还是“和而不同”?当年毛泽东关于“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或“合二而一”的哲学论辩绝非形而上学的概念游戏,而是触及探求至善真理的伟大意识。正是在郡县与封建、一与多的伟大意识中,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背后的“和平共处”思想回归到了中国古典传统之中。
如果说在中西文化领导权的较量中,我们之所以在民主乃至整个文明的正当性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还没有能力去发掘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改革背后的伟大意识,缺乏这种伟大意识的引导,使得经济改革的成就可能被金钱的贪婪、物欲的膨胀和暴发的炫耀所牵引,导致人心的败坏和伟大意识的沦丧。由此,如何收拾人心,凝聚人心,将政制奠基在人心之上,奠基在伟大的政治意识之上,这本来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胡温新政以来,我们不仅在社会政策层面,而且在文化价值层面,不断恢复社会主义传统中的人民主权思想及其背后的平等价值,也开始恢复儒家传统文明中的政治伦理原则、民本思想和和谐价值。中央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和文化软实力的积累也给予了高度关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既是爱民如子的儒家政治传统,也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传统,更包含了约束政府权力的西方民治传统。中国文明正是在古典儒家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西方自由法治传统之上,孕育着新的未来。面对这个光明的未来,依然需要全球的中国人以更大的耐心和更强的自信心,共同探寻中国的道路。
香港曾经是中国从大陆迈向海洋的政治跳板,那是继郑和下西洋后又一次富有政治意义的、而最后失败的远跳。而如今我们在香港正经历着静悄悄的第二次远航。香港不仅是我们展现给台湾的“一国两制”样板,也是我们巩固东盟的基础,更是我们透过东盟与伊斯兰世界建立合作、互惠和互信关系的纽带。若能善用香港,善用香港发达的商业、市民社会和文化这些“社会性力量”,善用香港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善用在香港积累起来的治理经验,则香港依然是撬动西方世界的支点。在这样的历史大变局中,中国香港又将经历怎样的历史命运?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