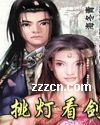挑灯看剑-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惟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
勾龙如渊笑看秦桧:“适才学生摇头,实在非是因为秦相之字,而是因苏大学士此句,而想起了昔日王荆公,无端生出了些许感慨。”
秦喜不由得一愕,秦桧却是稍稍注目,轻轻地说了一声:“哦?”
荆国公王安石,在本朝神宗年前的那一场大变法,非但是自本朝开国以来从未曾有过变革,甚至是自三皇五帝以来,亦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有宋一代,以科考取士,打破了以往下品无士族的状况,对于商贾的限制远较前朝为少,是以商业之繁荣,远逾汉唐。而历代天子官家对于文人士子参政意识的有意识培养,更使得文人士子对于家国天下有着远超于前代的担当。也是直至大宋立国,才会有臣子敢于当面跟天子提起君王应当“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又能获得天子的认可,甚至这句话还成为了有宋一代延革至今的君臣之间一种共识。
而这一朝一野的两大变化,也使得原本承袭隋唐而来的社会制度再难以满足现实之中种种互动,是以神宗年间,王安石应运而生,振臂而呼,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革。
只是一人之力终难尽善尽美,王安石变革初衷再好,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亦难免有许多难以预想的暇疵,一时朝中大臣,分成支持变法与反对变法的两派,也便是新旧二党。
苏轼苏子美苏大学士,正是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代表。
是以由苏轼之章句,竟能联系到王安石的变法,实在是有点跳跃过大。
更何况,自王安石变法之后,新旧二党在争辩之中益演演烈,逐渐由公正持平的国是之争,演变为一味相互攻讦的意气之争。
这等党争之祸,由王安石变法之际以来,哪怕直至金人纵马南下,宋室南渡而来,亦未曾有一日片刻的停息。
于是如今王安石王荆公这个本应无法回避的名字,有意无意间却依稀成为了一个大家不愿提及的话题。
如今这位深夜之间,不请自来的勾龙如渊,有意无意借苏轼之词赋而提起了这个话题,恐怕不会是偶发感慨这么简单。
秦喜蓦然间想起了那一日秦桧与自己讲解这一句时的那番神情,已是不由得略为色变。
秦桧却是神情自若,饶有兴味地问道:“哦?如渊果然眼界开阔,不拘一格,竟能由苏学士之词赋联系上王荆公,老夫实是愿闻其详。”
勾龙如渊微笑道:“苏学士满腹的诗文风月,是以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便是苏学士眼中最值得珍惜的无尽宝藏;王荆公却是满心满眼的百姓疾苦,是以他毕生所追求的,却是一个可供天下万民,衣食无虞,各得其养的无尽之藏。”
秦桧的眼里依稀露出一分恍然的神色,却是嘴角弯出了一丝笑:“如渊被龟山先生称许为承袭洛学门风之大宗,却没想到,对于王荆公竟也能作此等之论,若王荆公泉下有知,亦当含笑无憾矣!”
昔日洛学创始人明道、伊川二位先生,与王安石的变革前后,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明道先生程颐,认为王安石与神宗皇帝的一场遇合,实为古往今来君臣相遇之最佳范例,可惜王安石其道不正,白白浪费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是以行文传记,字里行间,不免对于王安石王荆公颇有些略显偏激的评判,由此承传而下,历来洛学门人对于王安石的评价都倾向于反面,却没想到勾龙如渊这个洛学传人会有这般与其师门完全不同的见解。
勾龙如渊抬头,轻轻叹了口气:“世人皆言王荆公不应一心求财、与民争利,却不知国不富则民不养、则兵不强、则为政不安,王荆公毕生所作所为,只为天下万家生民营造出一个再无穷匮的无尽之藏,并无一丝一毫的私心,学生此说,不过是持平凭心而论。”
“所以”,他转过头,看着秦桧,轻轻一笑:“学生此次冒昧而来,却是为了这些天来起居舍人包大仁会同户部、礼部、临安府有司诸官,所拟定出来的那个加征两项捐赋的条陈。”
秦喜眼中闪过的恍然之色,不由得微微皱眉,明白今天晚上的戏肉终于来了。
勾龙如渊从苏轼到王安石那处兜了个大圈,却原来所为的还是这件事情。
王安石变法以收天下之利归入国家,而为世人长期以来之所诟病,与包大仁所鼓捣出来的那两项捐赋,虽然方式方法不同,但最终目标,却是一样的。
观方才勾龙如渊所说,这位洛学门人,对于这等做法,居然却是颇持赞赏的态度。
只是自己与义父方才一袭谈话未完,自己却是完全摸不着眼前这位义父到底是在想些什么。
还好不管怎么说,这位义父的本意,本来也就是准备让岳飞与包大仁,放手去推行这两项条款,否则单是如何来说服眼前这位勾龙如渊,便是一件颇为让人头疼的事情。
虽然勾龙如渊只是个二十余岁的年青小子,但在学界之中,声名之盛,可谓一时无两。
在他身的站着的,可谓是大宋朝廷大半根本的天下读书士子之心。
秦桧神色不动,微微捻须,悠然开口问道:“如渊所说的,可是那份提议在临安城内试行经营获利捐与丁口收入捐的折子?”
勾龙如渊微微一愕,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道:“秦相果然明察秋毫,学生只知包大仁拟推行这两项捐赋,便自匆匆赶来,却不知原来只是准备在临安城内试行。”
秦喜凑上了前来,拊掌笑道:“说起来适才下官与义父谈及包大仁的这份折子,亦是想起了当年王荆公的那场变法。勾龙大人所见,果与下官父子不谋而合。”
勾龙如渊轻轻一笑:“如此说来,秦相对于此议想必早有定见,却不知……”
秦桧尚未及答话,秦喜已然先行笑道:“勾龙大人掌洛学正宗,对于此议尚无成见,我义父又岂是食古不化之人,事急从权,临机决断,本来便是国之常例,所以……”
“不”,勾龙如渊缓缓摇首:“秦相误会学生的意思了!”
秦喜微一错愕,秦桧的嘴角却是弯出了一丝笑:“如渊的意思是……”
勾龙如渊长身,向秦桧肃容一鞠:“学生此来,是恳求秦相,为天下苍生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个条陈真正通过颁行!”
秦喜忍不住唤出了声来:“什么?”
…………
瓢泼的雨,也浇不开笼罩在金兵临时大营头上那深浓的黑。
呼喊号叫之声,响遍了这片天地。
往往是两个人已然举刀挥出,才从对方的传来叫唤声里分辨出站在自己对面依稀是自己的同袍,但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方略一犹豫收刀,却便会在那错愕的瞬间被对手的刀贯穿了身躯,然后在躺倒在地上的时候,用最污秽不甘的声音叫骂着,却又在那片刻间沉寂了下去。
更何况这种攻击,不止是来自对面,更可能是来自于那完全看不清东西的任何一个方向。
在这个漫长得如同永远没有尽头的黑暗里,所有人都只能剩下了人心深处最野蛮的一面,恐惧、杀戮、嗜血,在这种时候,还残存着任何温情与不忍,都无异于自寻死路。
这,就是战争。
赵匡胤隐在事先选择好的战场死角处,信手打发了两个偶尔撞到这里的金兵。
若没有事先选择好的有利地形藏身,在如此不可预测的混乱厮杀里,哪怕个人的武学修为高深到何等地步,也绝无一丝保全自身安全的可能。
这次的劫营,他们胜在人数之少,少得不论敌我双方都难以想象的地步。
区区五十人,无论是如何的精挑细选、武艺高强,要袭杀一万五千精兵,都是绝无半分胜算的事情。
但偏偏在这漆黑如墨的暗夜里,越少的人数,反而能发挥出越强大的战力。
当那群“铁浮屠”军在黑暗中盲目乱砍乱杀的时候,他们便躺在事先挑好的隐蔽死角处,将自己所可能遇到的混乱砍杀的接触面减少到最低。
而每次电闪之时,当那群金军有可能借着那刹那间的光亮,发现自己人正在互相残杀的时候,他们便以哨声为号,飞身而出,制造尽可能多的厮杀与混乱,让尽可能多的金军,都感到死亡的威胁便尤如蹲在无边黑暗中的一头看不见的怪兽,无时无刻不在等着择人而噬。
身上大大小小七、八处伤口正在流淌着鲜血的押付边鲁,手中大柄砍刀晃动间,将临近身前的数名军士一一拍开,口中不断大声喝止着周围军士的混乱,却只能无奈地又自旋身躲开不断向自已身上招呼过来的砍刀。
他仰头,如注的雨浇得他满身满脸,却浇不灭他心里的那份焦灼。
他已然隐隐明白了在这种天气里,居然还敢前来袭营的这支神秘部队的战略所在。
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杀伤了多少对手,只在于尽可能多地在在场的所有“铁浮屠”军队心中,播撒下最深的恐惧。
这种恐惧一旦蔓延开来,哪怕这里已然有几名如同自己一般头脑较为清醒的“铁浮屠”各队大小头领,散落各处大声呼喝指挥,但战场的局势,却是根本没有可能得到任何的控制。
而唯一对整只军队具备真正控制力的平赤达鲁花,却是自开战以来,连一丝声音也没有发出来。
押付边鲁一念及此,不由得心头更是有如火烧。
一丝淡淡的凉意,便如暗夜中的一点雨丝,从押付边鲁的身后飘来。
押付边鲁却是如斯响应,一声大吼,向前飞窜而出。
电光闪动,又是尤如来自九幽地狱的哨声催命般地响起在他耳边。
左右两边风声闪动,生死交关之际,押付边鲁再不留情,手中刀飘摇交剪,将两侧三名军士尽皆扫得口喷鲜血,生死不知,继而迅捷转身,横刀当前。
却就在那电光尤自闪亮的刹那,一点淡淡的剑光,已然越过了他手中刀,轻轻刺入了他的咽喉。
虽然只是浅浅刺入一分半,但森冷的剑气,却已在那瞬间断绝了押付边鲁所有的生机。
押付边鲁抬起眼,不甘地在电光将熄未熄前,记取了辛弃疾那散发着凌厉杀意的双眼,就这么颓然倒到了地上。
不绝于耳的奔走呼号中,不知有几双脚就这么从押付边鲁的身上践踩了过去。
在临死前那一刻的清明里,押付边鲁清清楚楚地听到战场上所有呼喝指挥的声响已经全然消失,只余下连天的惨叫。
“完了!”这是押付边鲁心中涌起的最后一个念头。
第25章 黎明
风吹着雨,呼卷过园林,相府书房里的气氛,却依稀有了些凝固。
秦喜望着勾龙如渊,一时心中波澜不定。
他方才那话,是临时灵光乍现,故意正话反说的,隐含试探这位勾龙如渊之意。却没想到,这位新上任的御史中丞,果然真的丝毫没有观瞻顾及自己这位权倾朝野的义父的意思,就这么毫无顾忌地说出了自己要阻止条陈实施的真实意图。
自南渡以来,自己这位义父立主和议,与当今那位一意只求保全江南半壁天下的天子官家一拍即合,从此原本主战、主守的张浚、赵鼎两位宰相都被赶出了朝堂,形成自己这位义父一人独大十余载的局面。
也正因此,原本的朝堂中长久以来习惯于分成两派的读书士子,在十余年来朝廷内再无任何一股势力可与自己这位义父相颉抗的实际形势下,朝堂中的读书士子,都已经渐渐熟悉了唯自己这位义父的意思马首是瞻,而随着和议之局成为大宋朝的国是,自己这位义父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天下读书士子的典范与代表。
大宋朝以科考取士,读书人是朝廷百官之根苗,自己与义父手上,对于那些在读书士子间享有盛誉的学界大家的举动,素有关注。
据他们掌握的线索,眼前这位勾龙如渊,深为认可大宋开国以来崇文抑武的政策,从而在自己义父同以岳飞为代表的武将系统间的斗争中,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站在自己义父这一方。
更何况,这位勾龙如渊还历来以维护读书人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国是为己任,甚至为此提出了大肆伸张相权的“虚君实相”之说,在读书人之间影响颇大,甚合自己这位义父的脾胃。
也正因此,自己这位义父才会运用种种关系,让他补上了因万俟卨获罪而空下来的御史中丞之位。
却没想到,这位初履新职的勾龙如渊,甫一见面,其意见便与自己与义父背道而弛。
看来这个人是用错了!
御史中丞,主掌天下台谏清流,其所持的意见,对于朝议走向,一直起着极大的影响。
所以历来宰相可以荐任百官,却独独对于御史中丞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