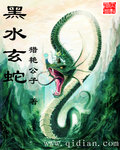青山接流水-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三人急急逼上,那首领却于踉跄后身形一个疾翻,手中长剑在空中绞了数个剑圈,鲜血在空中一路洒下,对手中的两人仰面倒落。
最后一人见情势不妙,发声喊便欲转身逃走,那首领捂着胸口急急追上,手中长剑如流星逐月,清远绝尘,射向逃走之人,一蓬血雾腾空而起,又洒洒落下,微弱的火光中,那首领手抚胸口,抽出长剑,在倒地的六人身上又各补了一剑,咳嗽着转过身来。
蓝徽容直愣愣地望着他步步走近,他胸前黑色衣襟被鲜血染得如一朵墨梅,面上头罩下的眼神让她手脚一阵阵发凉。
黑衣人首领在蓝徽容面前默立片刻,蹲落下来,微眯的眸子似有些不敢直视她愣愣的眼神,正静默间,蓝徽容一声惊呼:“小心!”
诡异的刀光自他身后摇晃袭来,那首领在蓝徽容惊呼声发出一瞬便已剑横身后,架住这必杀的一招,借力转身,只见那先前离去的黑衣人老万目光阴沉,森然道:“仇大人传信要我们提防于你,果然不差,你这小子,是活腻了吧。”
那首领也不答话,剑光霍霍,全力而击,他知这老万是所有黑衣人中武功最为高强的,虽不及自己,但如果和另几人联手,自己便胜少负多,所以先前才借口将他支走,不料他却中途返回,自己先前与那六人激战已受了剑伤,触动旧创,功力大减,现在实是到了危急关头。缠斗数十招后,他一声轻啸,口中喷出一口鲜血,随着那鲜血喷出,他手中长剑发出的杀气隐然成形,令黑夜空气都为之一凝。
老万见势不妙,知他正用咬舌之术,不惜巨损真气,使内力激至最强点,急急避开,无奈慢了一着,手中兵刃仅架住他第一波袭击,却在第二波剑浪中被绞得粉碎,千百道寒芒射入老万体内,老万倒地前睁大双眼,奋力将手中断刃递出,狠狠地插入那首领的左肋。
那首领捂住左肋,力竭倒地,身形几个扭曲,再也不曾动弹。
蓝徽容看着这惊心动魄的一番激斗,目瞪口呆,心头的惊疑如飓风般越卷越大,无奈手脚无力,纵是想爬至那首领身边,扯下他的头罩,也无法移动一步。
江边一片死亡般的沉寂,仅听到江水轻轻拍打着岸边岩石的声音。不知过了多久,那首领蠕动了几下,撑着站起身来。
他似伤得很重,踉跄走至蓝徽容身边,隐见他前胸及左肋鲜血淋淋而下,蓝徽容颤声道:“你,你的伤———”
那首领默不作声,忽然伸出手来,将蓝徽容的衣襟解开,将她的外衫外裙缓缓除下,蓝徽容的心一时下沉,一时飘浮,她脑中一片迷乱,眼见自己被他脱得仅着单薄的亵衣躺于地上,却怎么也发不出声来。
那首领又踉跄着步向江边一处高大的灌木丛,钻了进去,不一会儿,从那灌木丛中拖出一具尸体。
那是一具女尸,蓝徽容看得清楚,女尸脸上已被爆得血肉模糊,她终忍不住一声轻呼,只见那首领摸索着除下女尸身上的衣裙,将从蓝徽容身上除下的衣物穿到那女尸身上,又转过身来,抱起蓝徽容的上身,替她穿上从女尸身上除下的衣物。
蓝徽容眼中渐渐落下泪来,颤抖着道:“你———”那首领身躯一硬,猛然伸手轻轻点上她的哑穴,也不望向她悲伤的面容,静静地替她将衣裙穿好,将她抱至那艘小木船上。小木船在江水的推动下轻轻摇摆,那首领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瓶,倒出一粒药丸塞入蓝徽容口中,迟疑片刻,闷声道:“一会儿你手脚就可以动弹,你速速划船离开,一刻钟后你的内力便会恢复,你逃得远远的,再也不要回来。”
他又从怀中掏出数锭银两放入蓝徽容怀中,再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蓝徽容泪水汹涌而出,不停地摇头,无奈说不出话,眼见他奋力将木船推离岸边,眼见木船被他一推之势直入江心,随着江水向下游飘浮,眼见岸边火光下那身影跪落于地,隔自己越来越远,她觉得如在炼狱中煎熬打滚,心被生生的撕成千条血丝,疼痛至无法呼吸。
夜色下,木船沿耒江向下游急速飘去,蓝徽容渐感四肢可以动弹,但依然无法提起内力,只是可以如一个普通人般划动船浆,她忍住泪水,奋力将船调头,向先前入水的方向划去。无奈这晚江风甚急,又是逆水而行,眼见无法迅速赶回岸边,蓝徽容心一横,想起莫爷爷以前所授,咬上自己舌尖,鲜血自她口角缓缓流下,她血流速度加快,药效发作,不一会,便感恢复了两成内力,她提起内力,急冲向大椎穴,真气在那处回旋数圈,激起体内全部生气,终将解药效力瞬间提至最高,双臂运力,浆橹如飞,迎风破浪,向来路划去。
只是这种强提真气之法颇伤身体,她渐感胸口一阵闷痛,但再痛,她觉得都没有心中那股绞痛令她窒息,惊疑、震悚、恐惧、痛苦、彷徨、不舍齐齐攫紧着她的心,她恨不得插翅飞回先前所在岸边,揪起那人,扯下他的头罩,问个明明白白。
静谧的黑暗中,蓝徽容隐见岸边那一点火光还在微弱跳动,心头稍松,奋力划了过去,船未完全靠岸,她便扑入水中,衣裙湿漉着爬将上岸。
只见先前躺身的地方,那具女尸手执长剑,横于土堆之前,身前几名黑衣人的尸体横乱杂陈,一名黑衣人手中还握着似‘暴雨梨花针’的暗器。乍一望去,仿如自己奋力搏杀,与那些黑衣人同归于尽,却被黑衣人临死前射出的暗器爆糊了面容。
蓝徽容的眼泪如珍珠断线般掉落下来,是他,一定是他。
他利用西狄人救出自己,又不顾性命将这些西狄人杀了灭口;他早已准备好这具女尸,造成自己与西狄人同归于尽的假象,这样既能够让自己远走高飞,又不连累到慕王爷,更能让仇天行和简南英等人不再追捕自己。
可他,为何会是西狄人的首领?他,为何先前那般不顾性命搏杀?更重要的是,他,为何不与自己一起逃走?
他受了那么重的伤,送走自己,安排好这一切,他还有力气逃吗?他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为什么不和自己一起走?!
蓝徽容深深呼吸,冷静下来,执起火把,迅速在周围寻找一番,却未见那人身影,耳听得远处似有大队马蹄声疾驰,知可能是宁王派人搜寻而来,她心急如焚,却又无法出声,听得马蹄声越来越近,忽然灵机一动,直扑先前那藏着女尸的灌木丛,灌木丛又深又高,黑暗中她向前走了十余步,脚下终踢上一人冰冷的身躯。
她泪水直流,弯下腰将他紧紧的抱在怀里,迅速拖出灌木丛,抱至船上,此时,马蹄声就在数十丈外,她运起十成内力将船推向江心,纵身而上,迅速划动船浆,黑暗中,船在江风和波浪的推动下,如出弦的利箭一般向下游而去。
身后的岸边,人声喧哗,上百人接踵而来,惊呼声不断响起。
“不好了,蓝小姐身亡了!”
“快快回禀王爷!”
江边黑影浓重,星月皆躲于乌云之后,蓝徽容在黑暗中奋力将船划出十余里,知已脱险境,此时又是顺流而下,她平定心神,松开双浆,缓缓转过身来。
那黑色夜行衣下的身躯僵硬如冰,那黑色头罩下的双眼紧紧而闭,他仿如已经死去,已好象正在沉睡,他胸前肋下的伤口仍在渗着鲜血,蓝徽容只要伸手,就可以拉下他的头罩,看清他的面目,可此时的她,却鼓不起一丝勇气。
静默一阵,蓝徽容点上他伤口处穴道,鲜血渐渐止住,又从他怀中掏出数个药瓶,一一拔开闻了一下,知其中一瓶是伤药,就着江水泛出的一点微光,替他将药粉敷于伤口,撕下自己的裙裾包扎妥当,又伸手按上他胸前大穴,源源不断地往他体内输入着真气。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有了一丝反应,呻吟着动弹了一下,慢慢睁开眼来,蓝徽容一喜,他正好望上她如寒星般的眼眸,意识逐渐恢复,他伸手摸上自己的面颊,见头罩还在,猛然用力挣脱蓝徽容,‘卟嗵’一声翻入江中。
蓝徽容本能的身躯一拧,电光火石之间随后扑入江中,右手一捞,刚好来得及拽住他的衣襟,她用力将他拖回,波浪推涌间,游回船边,眼见他还要挣脱,情急下‘啊’了一声,这才发现自己哑穴已被冲开,她长叹一声,贴到他耳边轻声道:“孔瑄,你若死了,我也不会独活。”
岸边,数百支火把映得天空一片通红,简璟辰呆立于那具面目模糊的女尸身前,双手不停的互绞,是她吗?真的是她与敌同归于尽了吗?
那身形,那衣裙,恍如就是她躺于自己面前,让自己如割心般的疼痛。可那血肉模糊的面目,却让自己感觉到还有一丝生机,到底是不是她?
江风越刮越大,火把腾腾而闪,数百人静然而立,无一人敢发出半点声息。良久,简璟辰冷冷道:“唐文,传附近最好的忤作,将这几具尸体从头到脚,每一根毛发都不放过,给我仔细的验。”一名手下应了一声,转身而去,简璟辰又道:“尚力,你带人马沿耒江展开搜寻,记住,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容儿给我找出来。”
他负手望向耒江上空无垠的黑暗,心中渐涌狠决之意:容儿,如果你没死,我就是踏平西狄,翻遍东朝,也要将你给找回来!
三八、命运
九月二十,澄阳城外五十余里处,卫明山脚,杨家村。
村子北面靠近卫明山有一户人家,家中仅余一个六十多岁的残疾老头,其数个儿女皆于青壮年时患病离世,而他,双耳已近全聋,仅靠在山后种着几块蕃薯田得以生存。
这日下起了大雨,杨老头见雨势甚强,恐雨水和着山泥流入屋后那口地窖,那里面收着的可都是自己今冬和来春的救命蕃薯,一旦发霉,只怕这把老骨头将熬不过这个冬季。他披上破旧的蓑衣,在地窖口撑起一块大木板,推开地窖木门,沿木梯下到窖底。地窖并不深,里面堆着数堆蕃薯,杨老头在窖底看了一圈,见干燥如昔,满意地点了点头,正待出窖,忽见一堆蕃薯后似露出一片衣角,他想起自己眼力不太好,是不是花了眼,走过去正待细看,一石粒凌空飞来,正中他背后穴道,他眼前一黑倒于地上。
蓝徽容从地窖口下来,将昏迷不醒的孔瑄从蕃薯堆后抱出,凝望着他憔悴的面容,悠悠叹了口气:“又得换地方了,孔瑄,你得快些醒过来才行,我怕我撑不下去了。”
那夜,蓝徽容将孔瑄从江水中捞出,爬回船上,沿耒江放船而下,行不多远,便听到岸上疾驰的马蹄声,她知是简璟辰疑心自己并未身亡,派人追来,她只得抱着早已昏迷的孔瑄跳入江中,游至江边,也不上岸,躲于岸边的芦苇丛中,听着那些人马追着那艘木船而去,四周恢复平静,方悄悄上岸。
她心忧孔瑄伤情,急于找到一个大一点的村镇替他抓些药,无奈静夜中行来,到处可闻急促的马蹄声,可见映天的火把,她知简璟辰在这附近展开了细密的搜寻,好不容易避开一拨又一拨的官兵,一路向西逃匿。
孔瑄自被她捞上来之后便一直昏迷不醒,他的伤口在江水中浸泡多时,血倒是止住了,却开始有些肿烂,数日来,蓝徽容负着他白日寻地方藏匿,只有夜间才敢出去寻些食物和草药,又不停替他运气疗伤,累得疲惫不堪,若不是孔瑄还有一丝气息,支撑着她,她恐怕早已倒下了。一路行来,到处可见自己的画像,也到处可见成群的官兵,对每一个人进行着详细的盘查,她不敢在人前露面,生怕留下蛛丝马迹,她更不敢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两日,唯恐暴露行迹。前日逃到这杨家村,寻到这处地窖,倒是颇为理想的一处藏身之所,她又于卫明山上寻得一些疗伤效果极好的草药,孔瑄伤势渐渐有所好转,虽仍处昏迷之中,但呼吸已恢复正常,伤口处红肿消去,开始结痂。
不料今日被这杨老爹撞见,蓝徽容不忍伤他性命,只得再次负起孔瑄,等雨势停歇后,于夜色深深中离开了杨家村。
她负着孔瑄行走在泥泞的山路上,秋末的夜风寒凉入骨,孤寂、伤心、痛楚,种种感觉袭上心头,她就着一点星光缓缓向前而行,感受着孔瑄胸前存留的那团温热,眼眶慢慢湿润:“孔瑄,你快些醒过来,是个男子汉的话,你就不要这样赖着不醒,老是要我一个女子来背你,象什么话?!”“我知道你有很多事瞒着我,你说话也总是真真假假,但我知道你的心,不管你是什么人,我看得到你的心,你若心中无我,你不会这样舍命来救我,替我安排好一切。”
“你与仇天行是何关系,我等着你和我说清楚,所以你要快快醒来,把一切说清楚,然后兑现你的诺言,你说过的,要和我一起去苍山,孔瑄,我现在背着你去苍山好不好?”泪水滑入她的嘴角,咸咸的,仿如在她心口一刀又一刀地割着:“孔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