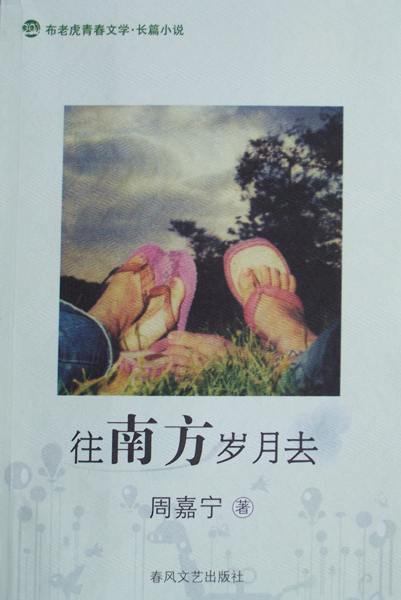南方有令秧-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房里异常地静。令她想起曾经的绣楼。自从嫁到唐家来,似乎就从没有自己一个人待在一间屋里过——这便是大家子的难处。她在自己的床沿上坐下来,贪婪地深深呼吸着只有独处才能带来的静谧。
有一条手臂揽住了她的肩,在她刚想惊叫的时候,她闻出了他的气味。
“你好大的胆子。”她满心的惊恐化作了怒气,却只敢用耳语一样的声音。“放心。”川少爷带着酒味的气息吹着她的脖颈,“我从我屋里独自来的,人都去吃酒斗牌了,你屋里也是——除了鬼,没人看见我。”
她不敢挣扎出动静来,只能听凭他解开了自己的裙子,再褪去了裙子底下的中衣。绝望和羞耻让她咬紧了牙关,她的身体却依旧记得他。男人们从来都不会遵守他们答应过的事情么?他又一次地杀了进来,他的渴望像是号角响彻了天空。带着血腥气。她恨不能像厉鬼那样咬断他的脖子,可是她不敢,她不能在他身上留下任何伤痕——天总归是要亮的,天亮了,她就必须装作什么都未曾发生。他压在她身上的脊背突然凌厉了起来,像匹受了惊的马。她就在这个瞬间用力地撑起自己的身体,像是拉弓一样,把二人的身子扯得分开来。黑暗中,她对准了床柱,重重地将额头撞了过去。情急之下,他扑了过来,他的身子挡在了她和床柱中间,她一头撞在他怀里,那种不可思议的剧痛让他想都没想,抬手给了她一个耳光。她呆呆地静下来,像是一团影子突然凝结在月色里。
然后她突然弯下身子,像条蛇那样,柔若无骨地俯下去,他惊讶她能如此柔软又如此粗鲁地逼近他的下体,双手硬硬地撑在他的胯部,他的双腿只能听话地分开,她的手伸进他的中衣里面,紧紧地一握,有股寒战立刻从脊背直通他的天灵盖——她的手有点凉意,然后是她的舌头,却是暖和的。他静静地屏息,像是狩猎那样,诱饵却是他自己身体上最宝贝的那部分,她是他的猎物,他任凭她不慌不忙地吃掉自己。她好像能这样吸干他,长老们当初为何就没能成功地把她吊死在祠堂里。她终于坐了起来,手背抹着嘴角,他胆战心惊地回想着她喉咙里那种吞咽的声音。
他说:“你疯了。”
她惨淡地微笑,不过他看不见这个笑容:“我不能再怀孕。”
他安静了片刻,闷闷地说:“自打洞房花烛夜之后,她就不许我碰她。”
她愣了一下,终于明白他指的是谁。她说:“我给你买个人放在你屋里,等三年孝期满了,你就纳了她为妾。”
他冷笑:“你以为我过来,只是为了让你准我纳妾?”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你自己瞧着办吧。我死不足惜。只是你若真的逼死我,我也能毁了你这一辈子。你是要我下跪,还是要我给你叩头,都可以,只要你饶过我。”
他离开了没多久,连翘就押着那个贪玩的小丫头回来了。她只来得及把所有散落在床榻上的衣物慌乱地塞到被子底下,然后整个人也埋进被子里。连翘会以为她是不胜酒力,她闭上眼睛,整张床都像风车那样转着,她知道他们其实都是醉了,她,还有哥儿。
天色微明的时候,谢舜珲才悄悄地回来。他打赏了睡眼惺忪的小厮,打发他去睡,然后自己牵着马去往马厩。原本从十一公的席上散了,只是耐不住唐璞的盛情,于是就去他那里坐坐——哪知道他请来的两个歌伎就在那里等着,怀抱着琵琶笑意盈盈地起来欠身。别的客人说,唐璞的别院里向来如此,欢饮达旦,不知朝夕。不过是听了一曲《终身误》,又听了一个《满庭芳》,还有几个曲子没记住,可是天倒先亮了。
他看到令秧脸色惨白地等在马厩里,头发只是挽着最简单的髻,只穿了套月白色的袄裙,额上发际还有一块胎记一样若隐若现的乌青。他心里一惊,睡意便散去了大半。“怎么是夫人。”他耐着性子,“这里可不是夫人该来的地方。”
“我还没谢过先生。”令秧凄然地一笑,嘴唇干得发裂,“家里能跟吴知县攀亲,多亏了谢先生美言。”
“夫人过誉了。”他静静地拴了马,“其实知县大人看上的是唐氏一族有人在京城平步青云,谢某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
“我不懂这些。”她静静地看住他的眼睛,“只是谢先生能再指点指点我么?究竟有没有别的女人,可以不用等到五十岁,提早有了牌坊的?除了死,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谢舜珲一怔:“这个……也许有,夫人容我回去查查。”
“谢先生,我怕是等不了那么久了。若有一日实在不得已,只能自己了断。就怕那时候没工夫跟谢先生辞行,先生的恩德我只能来世再报。”令秧以为自己会哭,但是并没有。
“夫人遇到了什么难处吧?”他一转念,又道,“夫人不必告诉谢某。不过谢某只劝夫人,眼下夫人最该做的,就是熬到三小姐嫁入知县府,到那时候阖府的境遇都不同了,夫人且耐着性子熬过这几年,到那个时候,不怕县衙里没人知道夫人的贞节。夫人且放宽心,记得我的话,府里关上大门发生过什么没那么要紧——所有的节妇,烈妇,不过是让世人都知道了她们的贞烈而已。就像是看戏一样,他们要看你扮出贞烈。夫人冰雪聪明,世人想看什么,夫人就给他们看,切忌认真——夫人懂得谢某的意思么?”
“就算能一直扮下去,也不是真的。”
“夫人若是有了牌坊,那就是真的。”
“我自己知道不是。”令秧此刻执拗的眼神就像她身后的那匹小马。
“谢某只告诉夫人该怎么做。至于怎么自处,是夫人自己的事。人生在世本来就是受苦。不受这种,便受那种,若有人真能如夫人所说,全是真的,真到什么都不必去扮,那便也不是人了,夫人说是不是呢?”
第六章
令秧自己也没料到,七年,一晃,也就过去了。
这一年,唐家大宅里最大的事情,自然是操办三月间,三姑娘出阁的大事。人仰马翻了足有半年工夫,好不容易把如今已亭亭玉立的三姑娘送去了知县府。按说,如今已不是知县府了——吴知县升了青州府同知,只等婚事办完便只身去山东上任,家眷还都在休宁留着。如此说来,也还不算远嫁,倒是减轻了不少蕙娘的伤感。三姑娘长大了,自然不似小时候那般淘气蛮横,人沉静了很多,可这一沉静却又沉静得过了头,甚至显得阴沉。装嫁妆的箱子堆满了绣楼下面的一间空屋——平顶的官皮箱和盝顶的官皮箱像密密麻麻的蘑菇那样,堆在陪送的屏风和亮格柜的脚底下,箱子顶上再摞着两层小一些的珍宝箱和首饰盒——令秧也不大懂,那些箱子盒子究竟是紫檀木,还是黄花梨。总之,夫家派了十几个人来抬嫁妆,也耗了半日工夫。族中的人都咋舌,说倒是没看出来唐家如今还有这样的底子——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不过区区90石大米而已,娶进来一个这样排场的媳妇儿,自是不能轻慢。
令秧现在的贴身丫鬟——小如——也在给令秧梳头的时候撇过嘴:“外头人都说咱们府里舍得,只是不知道,操办嫁妆的这些花销,蕙姨娘讨过夫人的示下没有?夫人性子宽厚,只是有一层也得留心着,如今三姑娘的嫁妆开销了多少,他日给溦姐儿置办的时候,是要翻倍的。咱们溦姐儿才是嫡出的小姐,不然传出去,人家笑话的是咱们府里的规矩。夫人说……”
她看着令秧转过脸,一言不发地看着她,便住了口。令秧依然面不改色地注视着她,直看得小如拿梳子的那只手因为悬着空而不自在起来,令秧就这样看了一会儿,牢牢盯紧她的眼睛,缓慢道:“管好你自己的嘴。”小如垂下了眼睑,悄声道:“夫人今天想梳个什么发式?”“随便你。”令秧淡淡地说。
小如是前年夏天来令秧房里的,平心而论,小如觉得夫人倒不刻薄,有时候还对小如嘘寒问暖的,只是即使笑容可掬的时候,也不知为何有种冷冰冰的感觉。总之,别人房里主子奴才有说有笑的事情,小如是不敢想。她默默地把梳子放回梳妆台上,仔细地在令秧的发髻旁边插了几颗小小的白珍珠——那是令秧允许自己的唯一的装饰。
没有人知道,在诸如此刻的时候,令秧最想念连翘。
可是连翘已经走了。
本以为,三姑娘出了阁,府里能清静几天——可是三姑娘带着新姑爷回门之后不久,就又要开始准备老夫人的七十大寿了。不过越是忙碌,蕙娘倒越是看着容光焕发,整个人也似乎看着润泽起来。众人都道是回门的时候,看着新姑爷对三姑娘体贴得很,蕙娘自是宽心,长足了面子,自然益发神清气爽。老夫人的这个生日,操办起来还和往日做寿不同些。这一回,唐家跟族中打了招呼,老夫人的寿诞,要宴请族中,乃至休宁县这几个大族里所有的孀妇赴宴,无论年轻年老;附近普通乃至穷苦人家,被朝廷旌表过,或在邻里间有些名声的孀妇也一并请来,办成一个有声势有阵仗的“百孀宴”。
不用说,这自然是谢舜珲的主意。
这些年,因着十一公的喜欢,谢舜珲更是常到休宁来,一年里至少有三四个月倒是在唐家过的——若是赶上有什么大事发生,比如川少爷的小妾生下的小哥儿的满月酒,只怕还会待得时日更多些。府里早已将谢先生也当成家里一个人,不用谁吩咐,厨房里都已熟记谢先生不爱吃木耳,喝汤喜欢偏咸一点儿。
把老夫人的寿诞办成“百孀宴”本来也不过是灵机一动。由川少爷试探着跟十一公提起来,结果十一公听得喜出望外,击节赞叹,连声道“百孀宴”一来福泽邻里,二来为自己门里的后人积德,三来唐氏可以借着这个时机,把自家看重妇德的名声也远扬出去。于是当下拍板,承揽下大部分“百孀宴”的开销,又叫唐璞负责监督着往来银两。
“千万记着。”谢舜珲告诉令秧,“这‘百孀宴’,说是给老夫人祝寿,其实是给夫人办的。”
那一天,令秧命人打开多年来一直上锁的老爷的书房,独自在里面坐着。谢舜珲进来的时候,她原想回避,后来又作罢了——如今府上应该没什么人会在意她单独跟谢先生多说几句。她笑道:“谢先生可是听我们川少爷提起老爷藏着的什么珍本,想来看个究竟不成?”谢舜珲也笑了,来不及回答,令秧便行了个礼,“我不过是想进来坐坐,看看老爷的旧物——如今三姑娘嫁了,老爷知道了也该高兴。谢先生喜欢什么书就拿去看吧,那么些书总是白白放着也太寂寞。我先回去了。”七年下来,她言语间益发地有种柔软,不再像过去那样,脸上总挂着一副“知道自己一定会说错话”的神情——她就这样轻描淡写地确定了,这些没人看的书很寂寞。
谢舜珲也对着她的背影略略欠了欠身子,缓慢道:“千万记着,这‘百孀宴’,说是给老夫人祝寿,其实是给夫人办的。”
她在门槛前面停下了步子,手悄然落在了门把手上。她系着一条孔雀蓝的马面裙,随着她轻轻地挺起脊背,裙摆上的褶子也跟着隐隐悸动了一下。她也不回头:“谢先生这就言过其实了,不过是我们府里牵个头儿,把邻里间这些寡居的妇人都聚过来,也好热闹一下罢了……”
“若真的只是为了让你家老夫人热闹一下,请戏班子岂不方便,何必请来一撮愁眉苦脸的寡妇?”谢舜珲不客气地冷笑道,“夫人且记得,谢某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百孀宴’的主意让府里破费——我自然有我的道理。到了寿诞日,老夫人的身子撑不得多久,周旋那些孀妇的自然是夫人,夫人沉着些应对着便好——十一公已经允诺过,‘百孀宴’会由唐氏一门年年办下去——夫人就是要让所有这些人都别忘了……”
“都别忘了休宁唐家还有我这个孀妇守着,对不对?”令秧淡淡地挑起嘴角,语气讽刺。
“夫人一定耐住性子沉住气,有朝一日,人们提起休宁乃至徽州这地方的贞节妇人,都会想到夫人你——到了那种时候,夫人不拘想要什么,只怕都不是难事。这世间任何事情,无论大小,不过是大势所趋,谢某要为夫人做的,不过是把这‘大势’造出来。”
“谢先生嘱咐的,我都记得就是了。会照着先生说的做。”她恭顺地打开门,微微侧过身子跨出去,借着侧身的工夫,回头一笑。
小如还在房里等着她,迎上来笑道:“夫人可回来了,叫我一通好找。再过半个时辰裁缝就该来了,老夫人的寿诞,怎么也得给夫人添两件头面衣裳。夫人这回想要什么式样的?”
令秧脸上浮上了倦意:“凭他怎么好的裁缝,我穿来穿去也不过就是那几个颜色,做了也是糟蹋银子。”
“夫人这话可就差了。”小如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