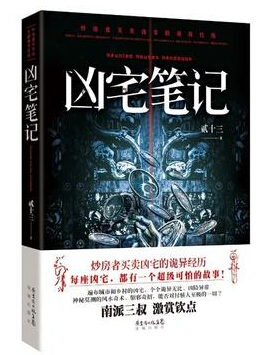园青坊老宅-第5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寓意平安的意思。“平门”没有门,只是在墙上开了一个瓶形的框。连廊穿过“平门”进入一进天井,再穿过天井,汇入一进厅堂,经过厅堂再分开,进入二进天井,一直通到三进的厅堂。连廊分分合合,分在天井里,合在厅堂中,天井这部分连廊由于是方形的,又叫回廊。连廊汇入三进的厅堂后,进入雨廊,穿过厨房和库房中间的过道,最后进入后花园。
如今老宅里的连廊早已面貌全非,看不出一个完整的样子,更别谈从前院通过连廊到达后花园了。老宅里人满为患,连廊都被占用了,有的被隔成住房住了人家,有的被隔成厨房烧饭。连廊在前院的起点处,就是程基泰烧饭的地方。连廊的终点,被隔成住房住了孙拽子一家。现在要弄清连廊的归属,会牵涉到很多人家的切身利益。
为了共同的利益,老宅里的人空前地团结起来。一团结就取得了成果,第一次谈判,开发公司就做了让步。
可是,散会以后,人们回到家里一想,喜悦的心情就降温了。这些连廊和共用厨房,如何计算面积?这些面积属于哪家?各家能分多少?越想,问题越具体,越想,矛盾越多,一个一个都和自家利益相关,都无法回避。
于是,各家的房门又关了起来,家家都在灯下商议着自家的事,核心内容当然是如何维护各自的利益了。老宅人的团结联盟,已经分崩离析了,表面上还维持着客客气气的样子,心里却在相互试探虚实。老宅人的心,又散了。
老宅三进的东连廊,一部分齐家做了厨房,一小部分被何惠芳隔成了厨房。厨房外还留着一点窄窄的回廊,回廊边有一排石凳。这些石凳已经年代久远,它不是给人坐的,而是早先小姐们摆放时令花草的,春天放迎春和杜鹃,夏天放牡丹和芍药,秋天放菊花,冬天放腊梅,平常就放有一些罗汉松、黄杨、文竹之类的微型观赏盆景。
现在老宅里哪还有地方给人赏花种草,但那些放花的石凳还在。石凳上现在没有放花,但两家人各自放了一个破盆。齐家放的是破花盆,里面种了几根葱。就是平时用过的葱根,随手点在破花盆里,有时烧菜来不及去买葱,就在花盆里掐几根。花盆虽破,但盆里总有几根绿色的葱。其实种葱不是目的,只不过以此向何家表示,这块地方属于齐家的。
何家不种葱,但何惠芳也是个精明人,她何尝不知道齐家的意思,她在窗前的石凳上放了一口破缸,缸里装着洗碗淘米的泔水,有时也倒点剩菜剩饭。几天下来,三分五分卖给从郊区来收泔水养猪的农民。后来物价上涨,精明的何惠芳不要那三分五分的钱,而要农民带点小葱来换。后来,养猪改用饲料了,郊区农民不再到城里来收泔水。可这口破缸仍然放在这里,这也是向齐家表明这边是属于我何家的。破缸放在石凳上,日晒雨淋,变成了蚊子繁殖后代的温床。但何家就是不拿走。
齐家是老房东,他们家把连廊隔出来做厨房早,差不多占用了连廊的三分之二,何惠芳是“文革”中搬进来的,只占了连廊的三分之一,这两个破盆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分别放在两边的。
多年如此,两家泾渭分明,从未有过异议。两只破盆也像落地生根一样,清楚地表明着彼此的“楚河汉界”。
这天早上,谢庆芳打开房门,发现石凳上有点异样。原来,何家那口长期空着的破缸里放进了土,土上也插了几根葱,不是葱根,而是葱。何家也开始种葱了?谢庆芳马上意识到何家的用意不是在种葱,那破缸还被悄悄地往自己家这边挪了一寸,虽然挪动的只有那么一寸,这也是何家在悄悄地多占地方。马上要测量连廊了,你何家多了,我齐家就少了,谢庆芳想上前把它挪回去。后来一想,也就那么一寸,何家占不了太多的便宜,就忍下了。但从那天开始,谢庆芳就特别注意那口破缸,每天都要看一看。
过了两天,谢庆芳发现那口缸又被挪了一寸。她想了想,还是忍住了,她还有更重要更紧急的事要做。那次大家与开发公司谈判时,她一句话没讲。因为她家的情况和老宅里所有人都不同。她家是真正的私房主,将来怎样还房,她还在等开发公司和她谈。她也为此找过汪经理,汪经理说:“你们家的事好说,因为你们才是真正的私房。你先等一等,我们把大部分人家的事谈完了,再和你商量。你放心,不会让你吃亏。”汪经理实际上是想把她家稳住,不让她们和其他人一起闹事。这段日子,她还在急着办另外一件事,这件事一定要在老宅拆迁之前做好,是大事,顶大顶大的事,她不想坏了自己的大事。于是,再一次忍住了,毕竟才两寸的地方,装作没看见就是了。
可是,当第三次看见那口破缸又被何惠芳挪了一点,谢庆芳再也忍不住了,她上前把破缸移了回去。
第二天,破缸又被挪回来了。她再一次把它移回去。此后,你来我往,谢庆芳和何惠芳在暗中较上了劲。
这天早上,何惠芳出去买菜了,谢庆芳又把破缸移了回去。而且移得比原来的位置还要多一点,也就是说,谢庆芳转守为攻了。
何惠芳买菜回来看见破缸不仅被移回来,而且还退回到自家一边。就把菜篮子往地下一放,又要将破缸移回去。这时,谢庆芳从门里冲出来,指着何惠芳说:“你这是做什么?”
看到谢庆芳,何惠芳有点尴尬地笑着说:“那石凳平时也是空着,我也想种点葱,烧菜时好应应急。”
“别把人家当傻子,谁看不出你的心思。”谢庆芳说。
何惠芳见自己的小点子被人识破,就想把此事支吾过去,说:“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怎么知道我的心思?”
谢庆芳说:“不要以为就你聪明。那破缸放了多年都空着,突然想到种葱?你种葱也不要种到人家的地方,谁不知道你的用意?”
好像被谢庆芳打了脸,何惠芳干脆就把脸拉下来了,说:“你不要以为这房子还是你们家的,空着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放东西,凭什么你家要多占一些。”
谢庆芳嗓音提高了八度:“你还以为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当权的时候啊?早落实政策啦,该是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怎么,你还想强占?早不是江司令的那个年月了。”
谢庆芳把死人江堂发拖出来,直戳何惠芳的心窝子。
这句话,一下把何惠芳拖回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一股热血直往何惠芳脸上冲。谢庆芳今天这样不屑地说到江堂发,当年可不是这样。
那时的江堂发是何等的人物?“武斗”打得激烈的时候,江堂发每次回来都横挎着枪,是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还带着一个警卫员,警卫员背着冲锋枪。当时正是暑季,何惠芳就把饭桌放在西连廊外的天井里,就是现在的这个石凳旁。江堂发吃饭时,手枪就放在饭桌上,板着脸不苟言笑,左邻右舍都不敢大声说话。有一次,一只苍蝇在饭桌上飞来飞去,江堂发赶也赶不走,就怪谢庆芳家的那个破花盆。他梗着脖子冲着谢庆芳家的窗户叫:“养这几根破葱干什么?净招苍蝇。”第二天,谢庆芳就乖乖地把种葱的破花盆挪走了。江堂发死后,那个破花盆又不知不觉地回来了,一直放到今天再也没有挪位置。
谢庆芳的话,让何惠芳恼羞成怒,她气急败坏地说:“你以为现在改革开放了,像你们家这样的就翻天了?江司令怎么样也不比你们家那个台湾的国民党军官差。”
两个人翻了脸,你一句我一句,声音越来越大,话也越来越难听。一个坚决要放,一个坚决不让放,两个人的四只手就按在破缸上,一个要挪,一个不让动。情急之下,何惠芳腾出一只手狠狠地推了谢庆芳一把,谢庆芳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下她可不依不饶了,从地上爬起来,叫着:“打人啦!”一把揪住了何惠芳的头发,何惠芳也伸手抓住了谢庆芳的头发,两个人头顶着头,你揪着我的头发,我揪着你的头发,僵持在那儿。
老宅邻里之间的磨擦几乎天天都有,吵架甚至打架也常有发生。平常这种时候,只要有人拉架,双方就会松手,然后再互骂几句,事情基本上就结束了。可这时恰恰大人们都上班去了,一时没有人来劝架,两个中年女人就这样揪着头发僵持着。
何惠芳知道自己打不过谢庆芳,这样下去必然要吃亏,首先声音沙哑地说:“你放不放手?”
谢庆芳虽然力气比何惠芳大,但连日来总熬夜,又要照顾齐社鼎,此时已气喘吁吁了,她也想结束“战斗”,乘势下台,说:“你放,我就放。”
何惠芳又不愿自己先放手,让谢庆芳占了便宜,“你先放,你先动手的。”
谢庆芳又来气了,“我先动手的?是你先动手,我才动手的。”
“我先动手的?是你先抓头发的,还说我先动手的!”何惠芳觉得自己已经吃了亏,还要输理,一时间气又上来了,于是手就不由自主地用上了劲。
何惠芳一用劲,谢庆芳也用了劲,两人又开始扭了起来。只是这时已经没有开始那样激烈了。
两人相互拽着头发,头顶着头,眼睛看着地上,嘴巴还在不停地互骂。
忽然,两人都停了下来,手也不拉了,嘴也不骂了。只见一只乌龟从墙角的阴沟里慢慢地爬了出来。它先从阴沟里伸出头,朝外看了看,然后慢慢地爬出来。这只足有汤碗大不知道已经活了多少年的乌龟,一步一步地朝两人的脚边爬过来。乌龟不怕人,反而逼得谢庆芳和何惠芳不得不为它让道。乌龟爬到两人的中间,停下来,抬起头,似乎很不理解这两个女人为什么打架,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然后一步一步地穿过天井,爬到了另一边的阴沟边,钻了进去。天井的青石板上,留下它从阴沟里带出来的一道长长的黑泥。
谢庆芳和何惠芳不约而同地松了手,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道理似的,各自理理乱糟糟的头发,默默地回家了。
何惠芳洗洗脸,梳了梳头,一屁股坐在那个旧时的“美人靠”上,看着空荡荡的家,心中涌上一股无助的悲哀。寡妇还是被人欺啊,何况她还是个“造反派”的寡妇。“四类分子”“右派”,甚至包括像孙拽子这样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历史反革命都摘帽平反了,她却无法摘帽平反永远出不了头。如今老宅里家家都在想方设法从拆迁返还中多得点好处,可她却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想来想去,就想了这么个小点子,还被谢庆芳发现打了一架。何惠芳想痛哭一场,又怕被谢庆芳听见笑话,只能强忍着。
她对着江堂发的旧照片,其实是在哭自己。自己是个寡妇,女儿又残疾,谢庆芳敢动手打人,明摆着是欺负自己。曹老三虽然忠实可靠,但大事上也无法帮忙,只能在搬家的时候出出力气。人活着,都有一个期盼,可自己的盼头在哪里?
想着,想着,泪水又夺眶而出,何惠芳低声地哽咽着。这时,却听见楼下的谢庆芳放声地大哭起来。
谢庆芳和何惠芳在天井里打得不可开交,齐社鼎却一脸安详地躺在床上。前几天他从床上掉下来以后,病情又重了,神志不太清醒,本来能说简单的几个字,现在又不能说了,反应也迟钝了。
谢庆芳披头散发地回到房间里,洗了洗脸,就从梳妆台抽屉里拿出一把牛角梳,梳那一头的乱发。梳子刚一插进头发里,就是一阵钻心的痛。刚才打架时,头皮都被拉肿了,谢庆芳只得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把头发梳顺。
梳妆台还是结婚时买的,跟着自己已经几十年了,它在窗前像落地生根一样一直没有挪动过。谢庆芳也像这梳妆台一样,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齐府,离开过这个房间。如今,梳妆台旧了,自己也老了,曾经的一头乌发里白头发越来越多了。梳妆台上有一面圆镜子,镜子的反面嵌着一张谢庆芳和齐社鼎的结婚照,照片上的谢庆芳穿一件旗袍,全身上下凹凸有致。那时的谢庆芳真的是年轻漂亮,跟齐社鼎在一起拍的照片,像一朵白玉兰开在一节老树桩上。看着照片,再看看镜子里现在的自己,一股悲哀直涌上心头。从想当齐府的当家人,到嫁给树桩一样的齐社鼎,到如今成了齐家一个老妈子,自己的一生就这么走过来了,要不是心里有那个企盼支撑着,她真的想不出活着还有什么盼头。
谢庆芳听到齐社鼎在床上动了一下,嘴巴呓语似的唠叨着。她走到床前,看到齐社鼎竟然面带笑容,这笑容让一股无名之火直冲谢庆芳的脑门。谢庆芳想,何惠芳虽然是个寡妇,但她的丈夫死了,再也不会拖累她了。自己虽然有丈夫,却如同一个活寡妇。齐社鼎这样不死不活地躺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