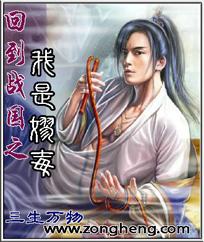明郑之我是郑克臧-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冲锋,结果一鼓盛二鼓衰三鼓竭,非但没有攻击得手,反而被耿精忠击败,等到其余溃散清军重整后反扑过来,刘国轩更是抵挡不住,由此郑军大败。刘国轩虽然最后时刻领一部返回九龙江东,但郑军精锐经此一战彻底沦丧,不得已,刘国轩率剩下的二三千残军弃守长泰,退回海澄
“复甫,怎么来了?”连遭败绩的朱锦如困兽一般,突然见到身为东宁总制使的陈永华风尘仆仆的出现在自己面前,心中的诧异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诧异过后,心中顿时涌起了一阵不安。“可是东宁出事了?”
“王上不必过虑,东宁一切安好。”尽管台湾内里国库中匮、外间社番捣乱,但陈永华却不得不若无其事的宽慰着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朱锦。“只是臣得闻本藩迭遭败绩,兵将损失颇多,所以特赶来恳请王上撤兵。”
“撤兵?”朱锦扫视着陈永华。“这就是陈卿的来意?”朱锦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陈永华这个人向来谨小慎微,从不越权行事,今天怎么会突然干涉起军机来了,他想了想,似乎明白了什么。“是钦舍让卿来的。”
“王上,虽是世孙力主本藩撤兵,但臣也是同意的。”陈永华变相承认着,说着还从袖口里掏出一副信来。“世孙还有一封信托臣转交王上。”朱锦拿过去观看着,等他大略的扫了一遍,陈永华继续进言道。“如今鞑虏及汉奸势大,本藩在闽省已经进取不得,不若转战粤桂琼,或可别开生面。”
“粤桂琼?”朱锦把信再三读了一遍,随即拍到桌上。“兹事体大,孤少不得还要咨询一二。”朱锦是个甩手掌柜,所谓咨询,原来是找陈绳武,现在是找冯锡范来掌总。“不过,本藩水师尚在,海澄亦在手中,所谓失败,不过是钦舍的臆断,复甫何以跟着惊恐。”
“东宁财力已至极限。”陈永华坦白着。“十年积蓄已然悉数用尽,实在无力再担负大军所支;除此之外,当年随先王入台各镇屯户如今几乎家家戴孝,已无精壮可调,而新近实台百姓不过是为田土而来并非真正顺服本藩,因此也无法轻易签军。”财力困顿、兵源枯竭,这两样平时只要遇上一件便是亡国的征兆,因此陈永华极力建议撤军是有理由的,并非单纯听从了郑克臧的建议。“因此臣以为,晚撤不如早撤”
陈永华很快就返回了东宁,但他带来的建议却在军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事关重大,冯锡范不敢轻易向朱锦建言,就把是撤军还是转战粤桂琼的问题推给了一线的指挥官——不少郑军将领人心浮动、思归心切,也有部分看到杨贤在雷琼红红火火便想转战粤南,但以刘国轩为首的一批郑军将领却不愿意落为杨贤的配角。
“绝不能撤兵,”刘国轩如此对朱锦大声疾呼着。“如今鞑子本欲夺海澄而不得,若是本藩认输自动撤军了,岂不是让鞑子喜出望外了。”当然这个说法并不能让朱锦满意,于是刘国轩补充着。“如今本藩军心沮丧,若是不经一战就从海澄和思明撤回东宁,恐怕日后看到清虏的旗号就要闻风而遁了。”
冯锡范看看意有所动的朱锦,决心出言帮刘国轩一把,如此既能对刘国轩等军中大佬示好,也能继续打击陈永华叔侄:“王上,臣以为武平伯此言不是没有道理,而且臣以为只有占住了思明和海澄才好跟北庭斡旋,以最小的代价换回最大的收获。”
朱锦的眉头弹了弹,他自然明白冯锡范的意思,无非还是以思明和海澄为筹码从清廷手中得到一些承诺,尽管这并非是他的初衷,但好歹能为几年来出兵大陆的损失讨一个说法,也好让自己有颜面回东宁见父老。
尽管觉得自己又一次被说服了,但朱锦依旧有些犹豫不定:“那南撤至琼州呢?”
“琼雷不过是偏师之地,有杨贤杨老大人一部便可。”刘国轩是这样认识的。“且海路甚遥,万一清军水师仅直跨海攻台,可是往救都来不及啊。”
“那粮饷和兵源?”
“有了海澄就等于在大陆上有了门户,本藩自可以收敛溃众亦可以重新征兵。”刘国轩信誓旦旦着。“至于粮饷,东宁困度,但琼州输入有余。”所谓有余是因为郑军兵败后兵力减少,并非是琼州输入多了。“可支撑一时,或可以转机。”
“这?”
见到朱锦还在犹豫,冯锡范忙坚定他的决心:“王上,当断则断呢。”
“那就如卿等所言,姑且继续坚守吧。”
刘国轩和冯锡范对视一眼,双双俯首应道:“诺!”
56。壮大
两艘小小的单桅纵帆船灵活的在海面上穿梭追逐着,其风驰电掣的速度、转弯时的倾斜程度,足以让初见的人为之心惊胆颤,不过,这一幕对于时常在台江上撒网的渔夫来说却是司空见惯,唯一不同的是,当初只有这样的帆船只有一条而今却是两条一起出现
看着兴冲冲归来的水兵队领队,一直用千里镜观察海面的郑克臧依旧问的很仔细:“佛光号操纵起来还顺手吧,比之英圭黎工匠所造飞马号又如何。”
亲自操过一遍船的麻英如实的报告着:“几乎跟英圭黎人船匠造的飞马号一样无二。”
“好,”听到这样的回答,郑克臧的脸上终于微微露出了一丝喜色,几天来因为朱锦不肯果决舍弃思明和海澄桥头堡的阴霾也似乎随着童子营少年船匠的出师而驱散了不少。“马原、唐通、吴虎、李平,做得好,尔等想要什么样的赏赐,尽管开口!”
虽说郑克臧问的只是站在自己面前的马原等四人,但其实这四年来童子营中前前后后一共遴选了十五位少年转入了船场学习,因此郑克臧的话实际是向整个造船团队许诺,只要马原等人的要求不出格的话,相信是可以满足的。
由于没有想到郑克臧的许诺会如此的慷慨,四人中最年长的马原犹豫了一下正准备张口,但排在其身边的李平却抢先应对道:“有总领的称赞就已经胜过其他的赏赐了。”
李平的奉承话让郑克臧不觉一愣,随即目光在四人脸上流转了一番,忽然发现了其中的关窍,正所谓党内无党帝王思想、派内无派千奇百怪,尽管马原等四人都是寒门子弟,但明显几人之间各有小派系,马原想当老大,可李平显然是多有不服,至于其他两人或持中或观望,显然比散沙好不了多少,不过这样的结果正是郑克臧乐于看到的,他绝对不想在任何方面出现所谓的“第二人”。
“这话说得好,余爱听,可是李平,下次可不准再溜须拍马了。”郑克臧故意如此说着,果然看到了几道若有所思的目光。“余这里有功就赏,有过就罚,用几句好话打发尔等的事,余还做不出来。”说到这,郑克臧沉吟了一下。“着晋升马原、唐通、吴虎、李平为正八品总旗,其余者授正九品小旗。”
还不等欣喜若狂的几人给自己谢恩,郑克臧又继续着:“余会安排工部给尔等颁发一枚佛光号下水嘉章,以做纪念,这枚嘉章还可以作为尔等的资历,不得了啊,了不得啊,童子营自行建造的第一艘夷船就出自尔等之手,何等的荣耀,日后记入史册,永传子孙呢。”
“总领,这,这真的能载入史册?”唐通有些不敢相信的问道。“只是一条小船呢。”
“什么小船,这就是历史。”郑克臧严肃的告诉他们。“或许上不了青史,但童子营要有自己的营史,尔等一点一滴,谁人做过什么贡献,营史里要一一载明,只要大明不亡,童子营不灭,尔等功绩就要代代传下去。”
四人目瞪口呆着,就连一边的麻英也瞠目结舌,显然郑克臧给他们画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大饼,正当他们目眩神摇之际,郑克臧却话锋一转:“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造出佛光号只是开始,接下来仿制双桅纵帆船、双桅横帆船、试制三桅横帆船甚至夷人船匠都造不了的风帆战列舰,余还希望尔等能再立新功!”
马原等人热血沸腾的保证着,郑克臧含笑听着,一边听,他一边考虑着是否现在就将几人分组以便使其相互竞争,但考虑到他们才刚刚拿一条最基本的小船练手,技艺并非已到臻境,因此便强按住了分化的念头。
“空话余不想听,余只希望尔等能言出即行。”郑克臧威严的说着,心里却在盘算着是否要现在就解雇了那些英圭黎工匠。“好了,尔等且先下去吧。”郑克臧挥挥手,四人领命而去,于是郑克臧冲着一旁拱手侍立的麻英问道。“麻百户,水兵队现在有多少人船了?”
“水兵队现下有二百二十人,其中水军调来的老兵和征召的渔民计一百人,童子军一百二十人。”麻英如数家珍的报着数,二百二十人的规模甚至已经比郑克臧设定的营级单位更大了。“船只有广船东胜海号,福船南安海号,沙船东沙甲、东沙乙,单桅纵帆船飞马号,双桅纵帆船骑士号,双桅横帆船飞鹰号、飞龙号,对了,刚刚又加了一艘佛光号。”
“二百二十人,九条船,规模不小啊。”郑克臧权衡了一下。“水兵队要扩充为营。”麻英脸上一喜,不过好没等他做起升官晋爵的美梦,郑克臧的话就戳破了他的希望。“余会从水师调营官和副营官进来。”郑克臧似乎看出了麻英的失望,笑着安慰他。“怎么有些失落?你才多大,已经是正七品试百户了,再升就拔苗助长了。”
郑克臧希望麻英能自己转过这个弯来,可若是麻英迟迟不能觉悟,郑克臧也不会舍不得放弃他——四期童子营、三期正军中有的是人才来替换他,更何况麻英在水兵队中的地位已经鹤立鸡群了,这也是郑克臧所不能忍受的。
“改营以后,以东胜海号、飞马号、佛光号为台江队,专司训练新近少年水兵,以台江内海行船为主;以南安海号、东沙甲、东沙乙三艘组成琼海队,以老兵带新丁;以骑士、飞鹰和英雄三船为猎鲸队,行走大洋。”郑克臧扫了扫垂头丧气的麻英。“巩天这几年做不差,可以晋为台江队领队,再简拔一名老兵为琼海队领队,你且继续担着猎鲸队的领队,对了卡尔船长是留在哪个队中,你可有什么建议?”
“属下以为,卡尔船长的经验是远洋,所以还请总领将其放在猎鲸队。”麻英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实话实说着。“属下的经验不足,若没有这些夷人水夫的襄助,断送猎鲸队是小,误了总领的大事,属下可担当不起。”
郑克臧冷冷的看着麻英,似乎在分析他的话到底是抱怨还是真心实意,好半天之后,郑克臧才缓缓的点头:“也罢,就依你的意思,不过卡尔他们是客卿,操训可以让他们管,其他的一定要握在你的手中。”
“诺!”
“还有,虽然是猎鲸队,其实你们也可以试着做几回海贼。”
“海贼?”麻英又吃了一惊。“这是不是有伤天和。”
“天和?”郑克臧一呲牙。“你可以去问问卡尔,海商跟海贼有什么区别”
对于朱锦不肯放弃海澄和思明抱有沮丧的不止是郑克臧一人,清廷福建总督姚启圣也算得上是一个,为了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他特意派遣漳州进士张雄来厦门议和,并附上一封措辞恳切的长信。
“昔令先wang震动天威,亦不忍父老嗟怨,静处台湾;今贵藩诚能体会先志,念井里疮痍,翻然解甲息兵,天和人顺,荣华世世!数月徒劳士卒,涂炭生灵,亦何益于贵藩哉?即从贵藩下游者,恐今昔人心不同,事变难测;能不顾念及此!近悉贵藩大有恻隐桑梓之念,故修章布悃,惟望息心毕论,并遣使偕临”
可是巧言令色的姚启圣是一个死心塌地投靠满人的汉奸走狗,他之所以绥靖明郑,目的还是跟杰书、喇哈达一样,只是为了讨回海澄以便向康熙交代,既然存在着这样的功利性,那么谈判自然就无法顺利的进行下去了。
于是朱锦遂以“顷承明教,以生民为念;不佞亦正以生灵涂炭不忍坐视,故修矛缮甲相与周旋,亿万生灵所共谅也。天心厌乱,杀运将回;苟可休息,敢不如命!礼应遣员奉教,但贵使之缆未解,而诸将之戈已挥。彼此差池,未及如愿”相回应。
吃了一鳖的姚启圣是乎还不罢休,在张雄被遣送回来之后又派出泉州乡绅黄志美赍书入厦门再此商谈议和事项,但由于其继续坚持“将以必得海澄,乃可通好”的方针,双方的谈判终于又一次宣告破裂了。
这一年的十二月,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都没有实现目的的姚启圣,以明郑方面索价太高无意和谈为由上奏清廷,重新执行封界令。原本在耿精忠叛清之后回归故地的沿海居民再一次背井离乡,“上自福州、福宁,下至诏安,沿海筑寨、置兵守之;仍筑界墙以截内外,滨海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