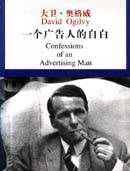��Ƥ��-��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ߣ������䡡��ռ��
�����������ɰ�������⡡���������������ռ�������������������ѧϰʹ�ã���Ȩ��ԭ���ߺͳ��������У����ϲ������֧�ֶ��Ĺ������档
����
��һ�¡��ܱ�֮��
1948�����죬��������һƬ���ң���Χ����ʮ������ӽ����ٵĿ�Ͷ��ʳ�������ϰ������ݸ���Ƥ���Թ��ˣ����С��ÿ�춼�ж������ˣ����ڵı�ֽ˵���������ˡ���ʬίԱ�ᡱ��һ�죬���촦������һ��������ľ�����������ź��Ӷ��������ˣ�������û�а취���͵��г���ȥڿƭ��Щ�����ĺ��ӣ���ʮһ����ĺ���ƭ���ң��ø��Ӱ�С�����ˣ������ϵ���������õ����϶�������������Ǯ��������ס��������£��Ҳ���û�м�����Ҳû����˵����ʲô���������������������ص����ȵȶ��������ݵ�ʱ��������ʮ�����˵���Ҿ���
���ڳ����IJ��Ӽ������߾�����ʮ�������ϼ��ֱ����ã�����ú;����ܶӵȡ���Щ���ӵ�ʿ�����ö������ᣬ�������ӣ���������Ȼ��ʣ��Ե��������ʣ����ŵƺ���̵�������ڰǶ������֡�
�����ؾ�û��������������������ս�۴�ã�����Ԯ����������Χ������ʯ��֣�����ĵ籨ָʾ�������ش�Ԯ���������������Ԯ�ǿ��Եģ������ǰ첻��������û�У�ʿ�����䡣ʿ���ѳ������ɡ���Ĺ�������������Լ��ѳ��ˡ�����֮���
��������£����ڳ�������˾����촦�ٹ�����û��ʲô��ͷ���������봦���Ź��仹��һЩ˽�������9�£��Ҿ��뿪�˶��쳤��ְ���漴�����ֳܾ���վ��վ����ޕ�Ᵽ��Ϊ�����������顱�鳤����Ȼ���Ͼ����ֲܾ���ġ���������������顱��Ϊ����Ԭ����һ֧�������˵ġ����ڵ����������¶ӡ�����װ����������ģ�һ���ٽ��鳤���ĸ���У��Ա������һ����̨����2�µ�9�£���֧������װ���̨�ˡ�������鳤��û�й���������ֻ�������켸��нˮ�������ѡ�
���˶��촦�����ǡ���һ���ᡱ��ÿ��������ң������Ժ����֡���Ȼ�������������ϰ��գ������ҵ���������������ҵ�ϰ�ߣ����Դ��ף����Զ��ͣ�ÿ����Ȼ����õ�������ۡ����ͣ�����֥���ͣ������ⲻ�ϣ�һЩС������ҵ�����Եġ��������Ҳ��һЩӦ�꣬����֮��Ҳ���Ǵ�ƴ��⡣���˳Ծ����Ρ���Ů�����裬û�д�����ᣬ����֯��ͥС��ᣬ�����ڸ��������ݡ����С����̫̫���Ǹ�С�㣬���߰��㣬�Լ������и���������Ϊ��ŪŮ�˵��ն�����ʱ�ҵ���������������룺�������군�ˣ���·��һ����һ�ж��������ң�Ϊʲô�����������أ�
��ƽ���нӶ����������籨�����ٻأ������Ź���ƽ�������籨˵������̫ү����Ͽ�������ٲ����������Dz�Т����Ȼ���Ҿ͵�����ȥ���㡭����һЩ���Ѵӱ�ƽ����������ʺ����������뿪�������Σ�յ������ӹ��ڼĵ����������ǿ�Ͷ�ģ�������������ǼIJ��ߵģ�ֻ���õ�̨���籨�������ÿվ��ĵ�̨����Щ˽�˵籨�������̨����������á��һص籨�������ǣ��������汻Χ���ɻ����ѱ���·���ڱ����ƣ���������ɻ���ֻҪ�зɻ��Ҿ��ߡ�������ޕ������˵���˵ġ�
9����Ѯ�Ժ���ս���dz����ã������Ǵ���̵���Ϣ����������ط������������Ǹ��ؽа�·��ռ�ˡ���Ϣ��Դ���������������������������ܡ���ͨ�����Ͼ����ܾ�Ҳ������վ���˵籨��ָʾ����DZ��������DZ��������DZ������������ɢ��ƽ���С����µף�������ޕ����������Ҫ��װ����ƽȥ��������ޕ��˵�������ߣ��������Ͼ��ֱ�����ʾ���Ҳ���ͬ���㾭����ƽ�������ˣ������ţ������������־־ֳ���������ƽ�����Ų���˵�ú����������뼰��ƽ�ȵصİ�·�����ڶ�ѯ������м����ɴ˿ɼ�����·��Ҫץ�㣬�㻹�Լ�������ȥ�ˡ���
��һ�룬��ô�ߵ�ȷΣ�գ���ʶ�ҵ��˺ܶ࣬����5��20���ڳ����ٿ��ľ����ᣬ��ף����ʯ����α��ͳ�������������μӣ�����������ľ������鳤����վ�ڴ����ǰ�ľ������ϣ���Ȼ���ű��£�ȴҲ��¶�����ݡ�����ָ��ֳ�����������˵�����㻹�°�·����ʶ�㣬վ���������Լ��������أ���
�������ʧ������ô�죿������ޕ���о�����һ�����������ͻΧ����ޕ�����˵������������Ҫ��ʱ�����ǿ��������������ӣ����߾�����ʮ��ʦ����ʮ������ʮ��ʦ�ͼ���ʦ���������������ӵIJ��ӳ������ˡ����ԡ���Ԣ��������˵���ˣ��������Ѿ����Ͼ����˵籨��ë���������ܾ־ֳ�ë�˷�ص�˵��ת��������ͳ�����������ӿ���������һ���ж�����
��˵�������ƻ�����ʵ�֣��ڶ������ǻ�װDZ�ӡ�����Ȼ���²ߣ���Ҳ���ܲ�������ޕ��ͬ�Ⲣ�����ܵĶ����������������˶������С��Ƭ���ҡ���ޕ�⡢�Ź��䣨���촦��������Ԭʿ�٣����ֳܾ���վ��վ�����������ܣ�������������ӳ�����Ԭ�������˶��ڶ��촦Ժ���յġ���Ƭ�պ�֮�����˵������и����������˹�������֤�����û������һ�����������������ˡ�������ξ��ı�����Ū������·�����Ҹ�����һ���ƽ�
���ֽ�ҽ������Ū��һЩ��ȡ�ƣ����������ʳѻƬ��Ψ��;�в�����ʳ��
��һ�죬�ҵ����촦ȥ���������ҹ����ij�������˵�������ڣ�û��ʲô���ӿɰ��ˣ����ΰ������������ˣ�������Ѻ�ļ�ʮ���˶������·����������˵����·���ͺ��촦�����촦���ǹض��쳤�������������Σ�һ�����ң�һ���dz���ᰡ��⻰Ҳ���٣����ǹ�ȥ��ôץ�˼ң����˼ң�ɱ�˼ң������˼��編���ơ����ԣ������η���Ҫץ��ɱһ��������ɱ����һ������
����ѽ����ɱ��ɱѽ��������ɱ��Ҳ������ɱ�������ֽ���˵����������������ɱ�Ķ�����û�У��汻��·ץȥ�������˻�������ܡ�Ӧ��Ԥ����ҩ������Ҫʱ������һ�ţ�������ʡ�����1945��⸴���ں���ץ��һ���ձ�ս�����ٽ����ľ��٣�Ѻ�����ǵĿ�����������֮ʱ��û�������飬������һ�鶾ҩ����ʲô�ڹ�Ҳû�о���ɱ�ˡ��ϰ壨��ͳ����Դ��ҵijƺ�����ʱ�ڱ�ƽ����һ��Ƣ����˵������س����ܡ���
������ձ�ս���Ѷ�ҩ���������������������ʡ�
�Ҹ������������ھ������߶���û������������������ڱ����������ίԱ�������Ƴ����ҶԿ���������˵����ץ���İ�·���ձ�ս��һ������Ҫ���·��ѹ⣬��������һ������������ٲ����ģ���������ϴ���衣������ʲô��Ҳû��������
û�м��죬�������������ܡ���������֣��һ���Һ��Ź�������һ���籨��˵Ҫ�ڳ�������DZ���飬ԭ���ķ�ѧ���Ǹ����ѱ�¶���ݣ���DZ�����������ڳ�������ɫ���鳤��ѡ����������˳ɣ�����α��������٣�������Ϊ���������鱨��������ʱ�ڳ������У����ļ��ڳ���ס������������ϵ�ࡣ��Ը��ɡ������Ź�����֣��һ����һ���籨������˳ɽ��ܸ�����10�³����������÷ɻ�����˳����DZ�����Ͷ�˸ɵ�أ��ܵ籾�ȣ������Ҵ������ڵ�ʮ��֧������˳����˰���ľ��ѣ��������ʳ��
ͬʱ�����ֳܾ���վҲ������DZ���飬�鳤����ǿ������������أ�������·����һ�����ӹ������������ˣ�����
����10�£����ƶ���ޕ������ȥ��̸�����ͻΧ�����飬��˵����Ϊ�˽����ж���������վ�ϵ��˱���飬�㡢�ҡ�Ԭʿ�١�Ԭ�����������ܡ�����奱���һ���飬������˱�5���飬ÿ��10����15���ˡ������ж������������ҡ���
������Щ���飬��û�������
Ϊ�˱��ڽ����ж������촦����������Ա������ᵽ����ס�������IJ������ţ���˵����ʯ���������Բ���һ�У�����Ϊ�������Ȼ���¡���ÿ��Ӵ������߾��ľ����Dz���������Ǵ��ơ����룺����������ô����ӣ�������������ʦ����У���ϵľ����м��٣�����ʲô�������д�������������ӣ����������һ�飻�ӣ����һ���ӣ����ò��Ź������ǡ�����������ˣ������µĶ��������һ������Ԥ�����ڳԻ��������̫ƽ�ꡣ
10��14�ս��ݷ��߱�ͻ�ƣ������Ϣ�����������������������о��³�ʶ���˶�֪�������ݱ�ռ���ж�����ɽ��ͨ��ʹ�����붫����ͨ�Ͼ���ʹ�������ؾ���Ϊ����֮��������ӣ������������ӣ�10��15�գ��ҿ������߾������д�С����������һ�����м��ͣ����ޣ��ƺ�Ҫ���������ӡ�
10��16����ũ������ʮ�ģ���33������ա��������ͬҵ�������³�κռԪ������ף�٣���˵�������ʱ��ɲ��ܹ����գ�������֪��˵�л������Ҫ�ۻ�ۻᣬ�͵���������Ҽ�������͵�ų�һ�٣�����͡���
����κռԪ�����˼������ѣ��ҽг�������һ��ϯ�����㺣ζ��Ӧ�о��С������̾Ʒ��������߰˰���Ԫ������һ���оŰ���Ԫ������������������ɢ����ҹ�Ҳ���Ϣ���Ҹ��ϴ�����ͷ��ú�͵���ը�ˣ��������IJ����ˣ�˭Ҳû���������������ô�ỵ���أ��粻�����ٲ�����ƫ�ڹ�������ҹ����̫���������һ��Ų�����������˯�ˡ�
�ڶ�����������һ�û���������ҵı�����ɳɣ����߾������ӶӸ��������⣬����ʧ��ظ����ң��������ˣ���ʮ���ѱ��ˣ������군�ˡ����ڳ����������֣����߾��ķ��ؿ���ͨ������ʮ���ķ��ز�ͨ����������쵽����˾�ȥ������Ϣ�ɣ���
�Ҵ�æ������绰��������߾���ı������绰��һ�ö�����û���������绰���ˣ�ϴ�����Ҿ͵����߾���ı������ı��û���ˣ������¼�����ʲôҲ��֪��������¥�����̰����������IJ�����û�У�˵�����������գ�����˵�������ִ����߾�����ת������˾��ζ�����Ƴ����ݣ�һ���ſ�������˾���ı��������ı����Ф�������ٴ�����ʿ���Լ�����һЩ�Ƴ��������������ң�����ʲô��Ϣû�У�����û�У������߾�û�ҵ�һ���ˡ�����ʷ������������ı����������ȥ�ˡ���
�������ǿ���������ʷ�߲Σ�ʷ���ף���������������վ�ٽ�վ����û�У���Ҷ�˵û�������绰������ס������һ��ְԱ�ӵģ���˵����ʷ�߲���ҹ���վ��Ÿ��ٳ���ȥ���裬����������ʮ�����أ���ʮ���ڱ������������û��ͣ���ڱ���ǹ�������������Ҽ磬����С����·ʩҽԺ���ơ���
�������벻�������顣
���ָ����촦�Ź����绰��������Ѻ���˷���ô���ˣ���˵�����������ˡ���
�Ҹ���������������ȥ�Ͽ��߰ɣ�����ʲô����
��˵�����ã��������ߡ���
�һ�ס��һ������ֱ���������У�ʲôƤ�������¡��ޱ���ë̺����������������������һ���ӡ���Щ�����е����������µģ��е������ø������ġ�һ����Ů����1000������ף�һ���ں�Ů����600������ף����ӱ�ʮ��������Щ���������Ķ���ҽ���������ҵ��ռǡ��ż����籨���������ֵĶ�����������Ƭһ�ɷ��ա��Ұ�һ��ˮ���ģ�һ������ɽʯ��˽���������顣������Ѳ��һ����û�������ֵĶ��������ֳ�ȥ�ˣ�������·��С���Ƕ������Ƕ������������𣨳����Ź����ٽ�˾���������˵������ޕ�����Ƕ������Ƕ�����һ��������أ����ȥ�ɡ���
�Ҵ�æ�ϵ��Ź�������¥�ҵ���ޕ�⣬����һ�Ʋ�ξ�����������Ҿ�����Ϣ����ʲôҲ��֪������һ�����Ԣ��������ʦ�����ٽ�˾��������ܣ�������������ӳ������������ֽ�����������Ԭ���������ֳܾ���վ�����鳤����Ԭʿ�٣����ֳܾ���վ��վ���������ˡ�
��ޕ�����˵�������Ǿ���ͻΧ����Ͳ�Ҫ��ȥ�ˡ���
������ʾ��Ԭʿ�ٰ��Ҽ���ס�����ҳ�ȥй©������ܡ�Ԭʿ�ٶ���˵���������ݰɡ���һ�����ݼ�ʮ���ˣ�������ġ��һ���ؼҿ�������ȥ���߾�����������Ϣ���ҳ�Ԭʿ�ٲ�ע�������������˳�����
����Ķ���û��������ǿ��š���ת��һȦ����ɳ��������һ�����վ�����Ի˵���������ˣ����ڵĶ����������ˡ���
�ҴӼҳ��������㵽���߾�ȥ��һ�뵽�Ƕ�Ҳ��û�а취�����ֻص��Ź�������������ޕ������ͻΧ��
��һ�������ˣ�����һ��С�����Ѿ��ϵ��ˡ�������Ժ��վ���߳����Ź����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