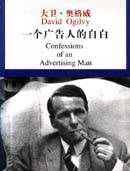黑皮自白-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感到邹瑞亭太势利眼,人家的东西为什么自己变卖了,还不给人家钱?项迺光已经不是长春站长了,管不着他了?小人作风。
邹瑞亭是地痞流氓,日本特务腿子,给日本人抱孩子,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后来又给白俄当仆役,又学会了俄语。伪满于长春警察六分局当特务股长。六分局住了许多白俄,归他监视,作了许多罪恶勾当。光复后,花钱运动参加了军统外围。在北京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当外勤督察员。有一次,派他去抓土匪,他不懂特务技术,叫门的时候,站在门的中间,手一敲门,里面“啪”地一枪,把他的右腿击伤,土匪没有抓着,自己先挨了枪子儿。谈起来真丢人。特务机关认为这种人没用,便放在一边不派他工作。他在医院把伤养好,一看没有人理睬他,又托人写了一封信调到东北。到沈阳后,他给军统局东北区秘书主任陈绎如行了贿,便派他到长春站工作。在长春站又行贿副站长袁士举,派他为少校组长。1947年春,因为长春战事紧张,他私自逃到沈阳,擅离职守,长春站当时的站长王力,即刻把他开除。可是他仍与军统的大小特务勾搭,以后认识了项迺光,认识了我。投机倒把,坐飞机运黄金。娶了小老婆,对他母亲与大老婆置之不理。特别在伪满的时候,倚仗日特,强奸白俄女人,逮捕无辜人民。
邹瑞亭到了我这组之后,心中很高兴,他单纯地认为:“关梦龄都没有枪毙,我有什么关系。”
这时从北京又解来一个栗宗元,他是伪满长春“三张二栗”的一栗。倚仗日本势力胡作非为,他看中了哪家姑娘,便给这家打电话,叫这个姑娘于晚上什么时候到某某饭店,如果不去,明天就抓人,说是反满抗日,是思想犯。看中了一个京剧女演员,唱完戏,就用车拉到饭店过夜,不去?行吗?邹瑞亭说他看见栗宗元了。
栗宗元自己不能写材料,叫杨文昌帮着写。
杨文昌帮着栗宗元写材料,写了一天还未写完,我把杨文昌找来,对他说:“你先把他在北京认识的社会关系写出来,检举要紧,过去的罪恶先不忙写。”
于是杨文昌启发栗宗元写社会关系,检举隐藏的反革命。他检举了不少人。郭科长一看这些材料很高兴,我又对杨文昌说:“邹瑞亭与栗宗元二人都是伪满的特务,要他们互相交待罪恶,比他们单个儿交待还有成效。你对栗宗元说,邹瑞亭不够朋友,把你的事都说出来了。这个人为了自己,就不管别人。这样一说,栗宗元受不了,就会揭发邹瑞亭。”
杨文昌果然对栗宗元这么说了,轻描淡写地一提栗宗元便受不了了。
“邹瑞亭说我什么?怎么说的?”
“算了,提这个没用,我也是听犯人说的。他不仁,咱们不能不义。不与他一般见识。他的事你又不知道。”杨文昌再三“拦阻”。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多得很,我说,你给我写!甭客气。”
栗宗元把邹瑞亭的罪恶检举了不少,内中有的邹瑞亭已经坦白,有的没有交待。
接着我又对邹瑞亭说:“栗宗元与你有仇吗?”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只是吵过架又好了,怎么了?”
“他说你许多坏话,咳!这小子……”
“他说我坏话?我倒要检举他!在伪满时,栗宗元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谁不知道?他那个买卖怎么来的?还不是敲诈来的!十六岁的小女孩他都强奸,缺德到家了……”
“算了,你要检举,就写材料。”
他说我代笔,写了许多栗宗元的罪恶。我给杨文昌一看,杨文昌说:“这两个小子,哪一个也活不了,有民愤。科长说有人控诉他们。”
“那就完了。”我下了结论。
小红楼的各监房门、窗,大加修理,大部分都换了新门,安上新锁,比过去坚固多了。郭科长这些日子忙得很,见面说不上几句话就走,有些事,我报告给他,也不注意。我知道一定另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3月下旬的《人民日报》刊载:美特高佩洁和他妻子马瑞卿在天津被捕。高佩洁是美国特务机关任用的特务。他在天津利用一个皮货庄,与丹麦、美国间谍一起活动。在他住处搜出大小电台三部,密电本七本,还有美特发的照相机等。这是解放后破获的第一个大特务机构,国际特务组织。使人震惊。
高佩洁与我相识,他的老婆马瑞卿在长春也与我认识。他家住长春东三马路。1948年7月,他多次请我吃饭,我也多次到他家。那时,军统有人对我说:“高佩洁自称少将,说是给美国新闻处工作,美国新闻处在长春的时候,他与美国人有来往,现在美国人走了,他何去何从?别被他唬了,如果给八路做工作,那可上当了。”
我说派人从旁调查一下。这话被高佩洁知道了,他认识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佩和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史祚炎,他托这两个人婉说,要见见我,请我关照,并以史祚炎的名义在高佩洁家中设宴。我去了,他对我说,他给美国情报机关做工作。1948年9月,我到他家,高佩洁对我说,要到沈阳。我对他老婆说:“你们过解放区要小心,共产党抓去了可要共妻的,那可不是玩的。”
“共产党把我抓去,我就自杀!”马瑞卿说。现在她被捕了,能自杀吗?这些人早晚都要落网,谁也跑不掉。
尚传道住一个单号,每天看书,吃小灶,犯人只有他一个吃小灶。早晨牛奶、面包、鸡蛋,中午一菜一汤,晚上一菜一汤,都是面食或大米饭。他什么也不写,似乎到这来研究马列主义而不是反省罪恶。一天我在看守所与宋所长谈话,郭科长也在。正赶这时,一个看守端一个方盘,盘里一碟炒鸡蛋、一碗黄瓜汤、三个馒头。这是尚传道的伙食。我说:“他什么也不干,吃这么好,现在东北吃黄瓜是稀罕东西。”
郭科长说:“你又馋了?回头给你也弄点吃。”
“我不吃,我吃炖豆腐就很好。”
“回头给你买包子,再买点酱肉。”宋所长说着骑车走了,不一会儿真买来了。郭科长叫我吃,他们谁也不吃。以后又把杨文昌找来,我俩把一斤酱肉,二十个包子吃光了。
郭科长说:“政府对你们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对尚传道与对你们的要求也不同。他觉悟慢,叫他多反省一个时间,叫他自觉认识自己才行,不能勉强。”
督察处侦审室的侦审员于文学也押在圆楼上。昨天小组长汇报,他是第一小组组长。会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来的?他说:“长春解放后,我逃到沈阳开了一个粮米铺,呆了一年,去冬被捕到这里,判刑七年,送到监狱。最后又从监狱解回公安局。”
我问他在沈阳还看见督察处的人没有?他说:“李贺民在沈阳蹬三轮,邢士林在沈阳开了一个电料行,贾英明在沈阳赋闲,去年冬天都被捕了,可能解到长春监狱。”
4月23日,圆楼上的犯人一律搬走,搬到小红楼。这一下,小红楼住满了。我搬到小红楼楼下七号。我们这屋有杨文昌、徐克成、李中候和我。
4月26日晚上,院内汽车不住的响。宋所长叫我们四个人,搬到圆楼。我们四个人,一屋一个,另外,马尚、沈重、王达生、栗宗元等人也一人进一个监号。我进屋之后,楼下便大批地往里进人。宋所长、王所长和几个所员,把进来的人送到各号。我在屋里往外看,人来得很多,也不问姓名,就往各监号塞。我这个屋一个一个地往里进,不到半夜,已28个人!不用说睡,就是坐也挤得难受。我心想,这是大逮捕。
楼下也押满了人。
这些人,我不认识。都是些什么人呢?楼上楼下押了五六百人。这个举动可不小!大概是现行反革命,也不能有这么多呀?
天亮时,我勉强地躺下睡了一觉。5点钟起来,坐着一屋子人,谁也不认识谁,互相看看都是陌生的。吃饭时,更乱了,我装作什么也不懂。他们拿筷子,也递给我一双,半碗白菜汤,一碗高粱米饭。吃罢饭,都开始大便,厕所在屋内,一大便,屋里这个臭哇。
饭后,我开始活动,先问我身旁犯人的姓名,这时看守战士严厉训斥:不准说话!我心中有数,照样与附近犯人说话。我告诉坐在门旁的一个小孩说:“老弟,你在那看着点,看守的过来先咳嗽一下。我们谈话有什么关系?大家在一起都是有缘的。”
“对,这位说的对,贵姓?”
“姓郭,叫郭依平,买卖人。认识几个反动派,当年沾点光,现在受点罪。”
大家笑了,你一言,我一语。我明白了,都是昨天夜里一块捕的。捕的方式都一样,用公安局的捕票抓来的。
有的人说:“我已经登记了,这回为什么还捕我?”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刚睡下就抓来了。连行李都不叫拿,咳,祸从天上来!”
“我就知道这几天不好,居民组长老到我们那儿,无话找话,问这个,问那个的。”
“昨天可抓老了!我来的时候,一院子大小汽车,满了,转不开身。”
“我还戴着这个家伙,下车拿不下来,就叫我进来了。”我一看这个高个胖子,右手戴一支铐子,左手没有戴,铐子紧紧扣在右手的肉里,手腕上的肉都红肿起来。看守所太忙了,宋所长也顾不得了,怎么还不给他拿下来?我告诉他,可以报告给那个看守战士,他赶忙报告看守,又等了一会儿王所长给他开了钥匙,把手铐子拿了下来,不过费了很大的工夫,因为这个铐子的锁不容易打开。
在这群人中,我先注意了七八个,对他们进行了重点侦察,他们一致的口气是不满政府,埋怨政府,不认为自己有罪。
我对这个大逮捕也有看法,政府说反动党团特登记坦白从宽。这回抓来的有许多人是登记过的。如此说了不算有失信用。不过人民政府对我的不杀,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说出埋怨政府的话。
夜里,不能睡大面,不能仰面,只能侧身睡,所谓睡小面。28个人挤得喘不过气来,这些人都没有被褥,也不冷,挤得直出汗。刚睡下便开始提审,我们这号提出去五六个。有一个叫胡荄,是1949年底我们写材料,李芳春检举的。我感到,我们写的那些材料有了用途。先把胡荄提出去,又提宋毅,接着提老董头,后来提我。提我到郭科长办公室,于审讯员也在那儿。还有很多人在外边屋子审讯,都在连夜忙。我知道这个逮捕规模很大,不仅长春市,恐怕别的地方也会有。郭科长问我号内的反应,我说:“都认为既已号召登记坦白,我们已经照办,还抓我们,这是说了不算;第二,自己不认为有罪,解放前自己没有血债。在解放以后,又无现行活动,为什么还要捕来?第三,反正政府说了算,刀把在政府手里愿意抓谁就抓谁。”
又问我个别犯人情况,我举例说了几个,于审讯员在旁边说:“关梦龄,你这回的工作可被徐克成拉下了,徐克成了解的情况比你多,比你全面。”
郭科长也这么说了两句。我心中的话,徐克成干这套给我提鞋,我都不要。用不着“激将”。桌上摆着纸烟,还有花生,我吸了一支烟,吃了几粒花生,郭科长叫我回去好好再了解一下,明晚,再向他汇报。
我附近有一个小孩,有20岁,他叔父开理发馆的,因为认识一个建军的特务,被捕,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建军的孙华南叫我给他送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后来人家对我说,那是情报。现在被捕,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问他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他说在解放前。我心中想,那问题还不大。他又说:“我这个反革命,连烧鸡都没有吃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穿过,他也没有给我钱,今天我被捕来,你说冤不冤?”
我心想,这个小孩老实得很,怎么也反了革命?内中必有枝节,再不就是公安局做情报出了偏差。这么多的人捕来,绝不可能一点偏差没有。这个小孩就有问题。
有一个山东老头,在南关种地,姓什么我忘了。我看这个老头不像地主恶霸,我问了他许多事情,没有一点嫌疑。一定是抓错了。晚饭后,我到看守所对宋所长报告此事。看守所没有底案,查不着这个人的名字,宋所长说:“回头再查一下,没有问题,就得放。”第二天早饭后,这个老头调走了,可能释放了。
夜里,照例审讯,各屋的铁门不住地响,不叫名,叫号,所以夜里睡觉多数睡不好。
我每天都出去汇报。看到各屋都有干部在审讯,有许多来审讯的干部我没有见过,可能是市局别的科的干部。看来是大动员。
有一个叫宋毅的,他是长春警察局的秘书,不是军统分子,一个书呆子。是被人介绍到长春警察局充秘书的,并且办了个边疆通讯社,他私人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