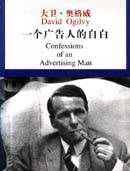黑皮自白-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宗元是个中学生,他只有19岁,去年冬,他与两个同学成立反共青年团,他是负责人,在长春市内各电影院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郭科长叫我了解他们的组织,人员及上级关系,两天之后,郭科长把我提到他的办公室,赵处长也在座,赵处长对我说:“你很辛苦哇,健康还好吧?”
“报告处长,我的身体很好,处长好。”
他叫我坐下,递给我一支烟,郭科长从旁说:“于宗元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处长要了解一下。”
“于宗元是反共青年团的团长,另外一个同学是副团长,姓×,他家开一个木匠铺。他们写传单,开会都到这个同学家。还有一个瓦匠支持他们,但不是上级。一个同学加入了他这个反共青年团。我问他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他说:‘我也不是有钱人,我家也没有在国民党干事的。我看了一些侦探小说,见国民党接收人员很气派。认为不革命,不吃苦,不自己打江山,将来没有出息。同时,我认为共产党长不了,于是我与同学就成立反共青年团。’”
“有一些问题真是不可思议呀!”赵处长摇摇头很慢地说出这句话来。
“我看应当把这个姓×的学生逮捕!”我没加思考,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不能随便抓人,还要仔细考虑一下……”赵处长还要说什么,又不说了。
当时我脸很红,后悔失言。一个犯人,怎么能在政府人员面前说出这样的话,第一,忘了身份;第二,还是军统特务作风,随便抓人,不管证据够不够,抓来再说;第三,这样暴露自己的缺点,赵处长还能相信我吗?
我与门光第谈天,他从哈尔滨到长春,做投机倒把的买卖。在沈阳与长春之间联络了一些奸商,公安局认为可疑而被捕。他被捕在五月底,进监较晚。对这次大镇压,他说:“这是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长春抓了一千多人,除了押在公安总局,各公安分局也押满了人。4月26日晚上来一个大逮捕,别的都市也是同一天抓的。公安局有一个科长与我同学,这个科长姓×,他告诉我那天夜里,把公安局的干部都留在总局,不准外出,口令是‘交通’。到了晚上7点,全市公安人员出动捕人,到5月15日这天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一次枪毙了150多人。叫这些人跪下,把帽子一抹,后面战士用机关枪扫射,第二次又枪毙了50多人,两次有200人。这两次,我都在场,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建军的,还有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听说北京、沈阳枪毙的更多。还有已经判了徒刑的,这回也枪毙了。”
他这一说,我感到后悔,5月15日我还不怎么害怕,认为不会枪毙多少人,可听他这么一说,判了刑的还有处死的,那我就是很危险的了。所幸没有被枪毙,又活到今天。是不是还有第三次镇压?那就听天由命了。共产党怎么说怎么有理,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杀也有理,杀了也有理,我又想,就是把我枪毙了,我比陈牧还多活了一年多,这也是宽大,不过我认为不会再枪毙我,我是北满军统特务宽大的典型,如果把我枪毙了,那人们就只能说,没有宽大,全是惩罚。况且我努力争取,也有成绩,到今天不会枪毙我了。我虽然这样想,恐惧的心情还是有的,这是内心的矛盾。为什么有这样矛盾呢?因为我对镇压与宽大的标准和依据还不知道,虽然毛主席说“可杀与不杀之间,不杀”,但是其间的分野我不清楚,犯人也不知道。因此,有恐惧的心情也毫不奇怪。不过这时的恐惧与1949年春天的恐惧不一样,现在的恐惧不严重,刹那间就过去了。
楼上十个组展开交待问题竞赛,每个小组长都很焦急,要走在前头,作出成绩,互不相让。因此,出了偏差。
首先,第六组组长李中候逼迫他那屋的一个犯人交血债,没交血债,不叫吃饭,不给水喝,接着又开始打人,罚跪。打人的情形各组都听到,看到了,因为同在一个圆楼,没有前窗,只是铁栏杆。各屋的事别屋能听见,看见。我把打人的事对宋所长反映了。在宋所长还未制止的时候,第三号、十号、七号,也都接着打起人了。于是宋所长把十个组长集合到后院进行了批评,强调不许打人!打人犯错误。宋所长虽然这么说了,可是李中候、沈重等人认为是为了促进同犯交待问题,打几下没关系,因此依旧打下去。这样一来事情严重了。
我们第一组一直没有发生打人事件,我认为凭我这张嘴就能把对方说服,还用打?我在屋内对同犯说:“咱们这屋,交待问题还用打吗?我看用不着,打人的犯错误,被打的人也丢人,男子大汉,有什么事敢承当,别说坦白了不会枪毙,就是枪毙了,又有什么关系?你不坦白不一样枪毙吗?”我利用别屋打人威胁本号的同犯,敦促同犯交待问题。
十号监房有一个叫姚汝纯的,是中学的数学教员,到过台湾。小组长沈重说姚汝纯利用中学教员作掩护,进行潜伏活动。但是姚汝纯不承认,于是沈重就动手打他,姚汝纯在小组挨打受气,成了“碉堡”,于是他承认:“我是台湾军统特务机关派来的,我携带有一部电台,两个密本,电台放在香港,我计划去取,我在长春收集文化机关的情报……”
这个材料内中有许多漏洞,赵处长提姚汝纯亲自问话,姚汝纯照样说。经赵处长再三追问,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赵处长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你不要有顾虑,可以对我说。”
姚汝纯把小组打人逼供的事一一道出。于是赵处长知道了监号的一切情况。赵处长问郭科长,郭科长说:“有打人的事,但批评纠正了。”
当天晚上,郭科长到了圆楼,大喊大叫,把各组的学习组长严厉地批评了一番:“为什么打人?谁给你们的权?你们都是犯人,为什么把过去的那一套作风搬到这里来?损害政府的威信!打人的组长要进行自我检讨,现在宣布停止学习!”
第二天停止学习了,每个犯人都不准讲话。我心想,打人的事宋所长知道,他制止了,不过没有认真制止。郭科长对此也马马虎虎,看守战士每天看守犯人,各屋打人的事,也看得到。都是有一半默许,才发生打人,逼供的事。这件事的出现,干部与犯人都有责任。
停止学习的第三天,我们几个学习组长,除了沈重因负责挑饭仍住圆楼,其余八个学习组长都集中在小红楼楼下,六号监房。这是个小黑房子,八个人挤在一块,真够受,这是处分我们,小禁闭。
由这开始,来了许多男女干部,都穿藏青哔叽制服,每张面孔都异常严肃。找每个学习组长审问打人的事。
“谁叫你们打人的?”
“谁也没有叫,我自己打的。”
“你为什么打人?不知道打人犯法吗?”
“……”
一般都是这样问答,只有我那组没打人,我的答话与以上不同,问我话的人是一个高个干部。我既没有打人,他就询问别组情况,我尽知道的谈了一些。
讯问李中候的是一个女干部,有30多岁,板着面孔,问道:“你们谁先带头打的人?”
“我先带头打的人。”
“你把打人的方式及打了多少人,详细地谈一谈,要老实。”
李中候从头到尾谈了一遍。
最后女干部问:“你打人的目的是什么?”
“打人的目的是叫他交待问题。”
“打人之后,没有人制止你们吗?”
“宋所长制止了,我们没有听,我们还是打,一切由我自己负责。”
“你是不是钻政府的空子,给政府造成损失,企图破坏政府的政策?”
“不是。”
每一个学习组长都问了多次,这样审问了三四天,才告一段落。我们背后议论,这些人是长春市委会的干部,有的犯人认识其中的人。
另一个下午,把我们学习组长及原来的学习副组长都集合到办公大楼的一个大审讯室里,有20人。不一会儿,龚副局长和一个穿衬衣的人来了。龚副局长问:“各学习组长,副组长都到齐了没有?”宋所长说到齐了。龚副局长讲话:“你们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犯人,在这次学习中,打人、逼供,这是特务行为,这与我们政策是相抵触的。我们对你们这种作法是不同意的,肯定说这也是错误的,有人钻政府人员的空子,企图不轨,这种行为是犯罪的。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纠正,这一点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到了外边,不准许把这些事乱讲,如果有人乱讲,就是犯错误!”谈到这,停了一下,看了我一下:“关梦龄!”
“有。”
“你谈谈这件事,怎么办?”
我说:“我们都是反革命罪犯,在监中利用学习机会,钻政府人员的空子,打骂同屋犯人,逼供,给政府造成重大的损失,破坏了政府的威信,因此有人从中煽动造谣,说政府支使打人。这是无中生有的诬蔑,我坚决反对!犯人学习组长打人骂人,应看做是监内的现行反革命活动,应当受到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我说完了,龚副局长说:“关梦龄这样认识比较正确,你们都应当有这样认识,你们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龚副局长讲完话,叫别的学习组长回去了,唯独把我留了下来,龚副局长说:“到那个屋子去,有人与你谈话。”
他下楼走了,我到了那个小屋子。方才穿衬衣的那个干部站在地中央,问我最近学习什么?我知道这是前言,不是本文,这些话他随便问,我也随便答,最后他问:“郭科长给你买过苹果没有?买过其他吃的东西没有?买几次?”
我如实说:“买过许多次,买过包子、苹果、香肠、花生等。”
“打人的事,郭科长看见过没有?”
“没看见过。”
又说了一些别的事,叫我回来了。这次谈话内容,我想是调查郭科长给犯人买东西的开支,核对一下,是不是犯人真吃了这些东西?这真是,身子一虚,什么病都来了。犯人打犯人,郭科长犯了错误,这又有了贪污的嫌疑。我心中为郭科长犯错误而不快。我想,我没有给郭科长脸上抹灰,我对得起他。我是非常狡猾的特务,什么花招我都有,但我对郭科长没耍过手段,原因,他很年轻,口快心直,办事着急。我要留给他这样一个印象:关梦龄虽然是个老特务,但还老实,叫他办什么事,他努力去做,不会欺骗。所以,我写材料或反映情况,从没有半点不实之处。我看到的、听说的、我指挥别人做的、我自己在场看别人做的,都老老实实反映出来,并且一切都有分寸,从不糊里糊涂,故而郭科长相信我,因为有这些事实。
郭科长犯了错误,换了一个王科长。宋所长没有换。我们这屋八个人,王达生出去了解一个新来的犯人,走了,把李中候调到圆楼,蹲号去了,让他与一般犯人在号里坐着不准动。李中候这个人不老实,乱七八糟,自己没有办法帮助同犯交待问题就带头打人,这回就坏在他身上。
10月上旬,看守所提我到前楼审讯室,审我的是我的盟兄弟高心鲁,头两个月我便从郭科长嘴里知道他升了科长。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干部坐在旁边。
高心鲁站起来与我握手,他说:“没有瘦,还胖了。”
“身体还好,老太爷老太太都好吗?”
“都好。才侠有信没有?”
“没有,我给她去过信,小孩子来过信。她们在徐州,还可以生活。”
“今天向你了解一个材料,国防部第二厅的问题……”最后,那个女干部出去了,我对高心鲁说:“这回郭科长犯错误,多可惜,我都不好受,你可千万别犯错误,负责任的人,稍一不慎,就可能犯错误。”
“我特别小心,不会犯错误。”
“我听人说,你在家还请客,这种作风要不得,不行呀,要节约哇。”
“我找人吃顿饭你都知道?”
“有一个犯人住你对面,他说的。”
“是不是一个老头?”
“对了。”
我回来之后,我感到高心鲁还是大手大脚地花钱,他吸的是有锡纸的香烟,这有多贵呀。我想起1948年高心鲁给第一兵团副官处长罗寿安行了贿,得到10万斤大豆加工成豆油的生意,按当时计算高心鲁可得70两黄金。他本没有加工厂,便将大豆卖了,折成豆油价格付给兵团。两天以后,郑洞国来了一个电报,不许把大豆加工成豆油,让把十万斤大豆作为军队的主食。罗寿安找高心鲁强迫他还大豆,高心鲁便携带全家老小出了长春,逃到解放区。临走之时找我给写了条子。没有我的条子出不了卡哨。为此罗寿安还放出空气,说“关梦龄私通八路!”想起这一段,看他现今的作风我替他担心。
自从镇反过去,敌我划清界限,干部也不与我握手了,说话也你我分清了。尚传道的小灶也不叫吃了。他在号内也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