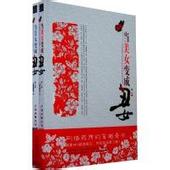当美女变成丑女-第6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西门芩提醒,我又能逃避多久呢?
我异常温柔地看着他,凌哥哥,就到此为止吧,求你别再逼我。我怕你跟我都无力承担坦白的后果。
“凌哥哥,你还是走吧。我不会跟你走。我有我的选择。”
“丁丁,你是不是怕老夫人反对?她已经过世了。现在我才是丁家的主人。”他有些焦急,面对我完全不在他意料中的反应,渐渐无法冷静。“你是不是气我来的太晚了?我一安排好,就立即马不停蹄地赶来祁风,一刻钟也没耽误。你也知道地西门家不是普通人家,没做好准备,我根本带不走你。”
我叹息:“你怎么还不明白,即使老夫人不在了,有些命中注定的东西依然永远不能变更。”
他一怔后哈哈大笑,意气风发地扬起下巴:“原来你说这个啊,我以为什么呢!谁说不能变更,我就要变给你看看。”
我莫名其妙,差点以为他是不是不能接受现实而有些糊涂了。
他抓着我的肩,用力把我扳到他面前:“丁丁,你听仔细了,你不是我的堂妹,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你说什么?”我耳中嗡嗡作声,眼前一片金花。
老夫人临终前告诉我的,当年你亲生祖母的丈夫病逝,祖父见他漂亮,强娶她做小,她是带着肚子进门的。我还带来了你父亲的亲笔书信,上面说得很清楚。“
“你在开什么玩笑?“
颤抖着接过我爹的家书,还没等看完,我眼前就一阵阵发黑,脚下一个趔趄,幸好丁维凌把我捉得很紧。
“老夫人就是因为你地祖母不是清白身子进门却得尽祖父的宠爱,才会在祖父逝世后变本加厉折磨她,折磨五叔一家人。”
我茫然,真可笑不是吗?我一直害怕自己行差踏错,苦苦压抑,结果不过是一场女人之间地战斗。
“天意,天意啊!”我狂笑。是老天也看不惯我的没心没肺,所以才要我穿越时空来到这个陌生地时空做一回任情任性的丁丁,要我也知道疼懂得痛吧。
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问我一声:丁丁,你可愿意?不不,我不愿意的!
“丁丁,丁丁。你怎么了?”丁维凌大惊,拼命摇晃我。
梳得美美的发髻散乱着摇摇欲坠,我笑得前俯后仰,不能自己。
短短几句话,让我这十几年变成了一个笑话。
丁维凌募然指着我的头,难以置信得喊:“丁丁,丁丁,你地头发——”
我突然不笑了,抬起脸,清清晰晰地对他道:“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对我来说。这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笑话。无他,只因为历历都发生在我身上。由我一件件亲受。
丁维凌愣了下,回过神来:“你明明知道的,在我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存在,无论你是否是我的堂妹。”他蹙起了好看的眉毛,对我用笑话一词定义彼此的关系显得非常不满。
“所以你就一手把我送来西门家,一手把如言送进鬼门关,是吗?”我望住他,眼中的悲哀浓得化不开。
“你我血脉相连,你知道留着我迟早是嫁给温如言。所以呀把我远嫁他乡;你知道有如言在我就嫁不成,所以就联手玄天宫、西门世家一起害死了他;你知道有老夫人在,你就永远出不了头,所以老夫人就只能天年已尽;你当然也知道,如果我被休返家,势必不肯再嫁。只能移旁于你。如此这样兜来转去,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和你生活在一起,一切尽在你算中。”
终于摊牌了,当血缘成为笑话,曾经的爱情也成了荒唐。我凄然一笑,凌哥哥除了算不到我们其实并没有血缘外,也没算到我最后竟然不肯和他走吧!
“你怎么会这么说?”丁维凌大惊,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捉住我肩膀的手,一连后退了好几步。
“凌哥哥。事已到此,你又何必再装?”我凄然道。“我孤身远嫁他乡,便已打定了主意再也不想、不问、不提此事。可是你又何苦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呢?”
丁维凌怒道:“你宁可信西门家地人胡说八道。也不信我吗?”
我淡淡道:“我只信自己的心。”眼睛会骗人,可看透了世情地新不会。
“丁丁,你是爱上西门纳雪了吗?”丁维凌惊怒交加,开始口不择言:“他可是不喜欢……”
“他不喜欢女人嘛,我知道的。”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早知他是知情的,以丁维凌的性情和能力,怎么可能不把西门家掘地三尺地了解清楚就把我送进来呢?
“那你还留在这里守活寡?”一向斯文有礼的丁维凌也忍不住粗俗起来。
“我在这里有我的责任,我要为如言报仇。”这件事我并不打算瞒他,何况也根本瞒不住。
“温如言,又是温如言!做了鬼居然还阴魂不散。”他暴跳如雷,气得破口大骂。“早在第一天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祸胎。”
我冷冷地道:“凤郎自己也是个祸胎,只要是我重视的男人都是祸胎吧?”
凤郎太过纯真,我视他为弟,所以他还能忍着,可温如言地心是剔透的,他洞灼人心的双眼一定使丁维凌也感到了恐惧和威胁,才会想出了这种一石数鸟的连环毒计。如言只是太过关心我,才明知山有虎而偏向虎山行。
丁维凌的瞳孔募然放大:“你我二人自小亲密无间,我疼你胜过一切,你居然是这样看我的?”
我涩声道:“我只知道,是你我二人联手送他去死地。”他是算无遗策的主谋,而我糊里糊涂中成了他的帮凶。
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爱我的男人最后却为我而死,而我根本不能真正替他报仇,因为那个真正的幕后黑手是我永远也下不了手的。执着要找我的麻烦,我还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活着虽然太难,可我不能再让如言希望了。
丁维凌重重一拳捶在梅树上,洁白地花瓣在洁白的鹅毛中纷纷扬扬飘落。他痛苦地低喊:“那是个意外,你懂不懂?没人要他死!”
“凌哥哥,我是你身边最亲最亲的人,连我都要算计。你不累吗?”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根尖针狠狠扎进了心里。
“丁丁,你居然不信我?在你地眼里温如言终究还是重要过我。”他踉跄了一下,眼中闪烁这晶莹,有这心痛难当地难以置信。
我沉默。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我们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在没有学会遗忘前,命运就以经烙下了遗忘的宿命。
空中有一群鸟排着整齐的人字形队伍鸣叫着飞过。是要南飞的雁吧?丁维凌突然一甩袖,便有一只雁一个跟头坠落下地。雁群惊散,在空中徘徊,发出悲切的叫声。飞了几圈后,头雁终于振作起精神,排好队形,继续南飞。只是雁群最后那只雁的身形显得那么的孤单和悲切。
“你看到了吗?没有了你,我就是那只雁。”他幽幽望住我,眉梢眼角地高傲全被忧郁笼罩。让人伤感地想要落泪。
“他们本来是好好的,你却生生拆散了他们。”我望向夜空中大雁坠落地方向,却终究还是不曾流下泪来。
“说来说去,你是在怪我拆散了你和温如言是吧?”夜色中的他脸容憔悴,完全没有了记忆中的意气风发。
我不知道该说是还是不是,答案都不重要了。我最在意的人一个个都已经离开了我。
“你要我说是。还是要我说不是?”
丁维凌一窒,他想摆出一惯的强势来,可惜惜日的情感一去不回,这强势便失去了支撑的凭恃,成了纸老虎。
我怅然转身,缘尽于此吧。
“丁丁,就当我求你了。你跟我走,我们忘记以前的一切,重新开始。”他的表情便象是扑火地飞蛾。痛苦而决然,明知道是条绝路。依然不死心地挣扎着。
“凌哥哥,你走吧!好好对待扶悠表姐。”有些事情。放手了便再也不能回头,有些记忆写上了就再也不能抹去。那一场青葱岁月,我们终是檫肩而过,他尤是他,我仍是我。
“如果你心里还能记挂着我们的情谊,就帮我好好照顾爹娘和凤郎,让他们好好地生活下去。”一地海棠,踩在雪白的花瓣上,仿佛踩在了过去的时光上,步步是刀,踩出一地的凄伤,就像我、像如言、像丁维凌、像西门芩……
不知走了多远,身后一直响着沙沙的脚步声,但我一直没有回头。
我早已没有了回头路。
幽幽一叹,说不清地孤寂便笼罩了这一方小小天地。
西门芩缓缓渡步上前,摇头叹道:“都是痴心人啊!”
“你怎么也在这?”
西门岚坦然答道:“来监视你们。”
我淡淡道:“西门芩倒还真不放心我。”
西门岚耸耸肩:“倒不是他不放心你,是我不放心丁维凌。丁维凌要是想不择手段,我就只好出手了。”
我微摇头:“他不会逆我的意思的。”
“他既然能背叛你一次,又怎么不能背叛第二次?”
西门岚的话语比刀还尖利,因为真所以痛,让我哑口无言。
说不难过,那真的连我自己都不信。这么多年,一天天的感情积聚起来,不仅有男女之爱,还夹杂着深厚的亲情和友情,我对他曾经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到了如今却说不上一句实话,勾心斗角地彼此算计着。
我明白他的心思,心里跟明镜似地,他会这么想这么做我不怪他。只是我原以为可以放心把手伸给他们握着,但他们一个背弃了自己的诺言,离我而去;另一个背弃了我地信任,推开了我。
从此以后,我还能相信谁呢,或者该问的是,我还有机会去相信吗?
我找不到答案。
以暴制暴
丁维凌的出现是个迹,他的消失也象阵风,西门家族的人没有过问半句,似乎无人知道他曾在某个月夜出现在我的沉雪阁。
他们不提,我自然更加不公多提半句,这件事便如风起涟漪,波心微微一荡便又平静如镜。
一切好似都没发生过,或者说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自然该有些事要发生,想挡也是挡不住。
比如说我的头发。
起初只是偶尔的一两根,一日两日的发中的银色日益多了起来,到了现在已经渐渐遮不住了,所以每天清晨流光为我梳妆的时候总是很头疼。
我起先看这星星点点的斑白也很不顺眼,总觉得白得太刺目,可这时代也没有染发剂,于是看久了也就习惯了。就象这世上的很多无可奈何的事一样,习惯了也就是那样了。
反倒是旁我总是看得不太习惯,身边亲近之人如流光张之栋自然时不时在我耳边嘀咕,要我多些休息少些操心。说了也是白说,他们自然也是知道。但身为近侍的职责还是不得不说,说完就是忙着搜罗各种白发变黑的土方偏方,忙着将西门岑这送来的何首乌、芝麻之类传说有乌发功效的滋补之物流水价让我吞下去,我也只有苦笑着顺从。
不过传说中能让白发魔女白发变黑的优昙仙花在这个世界是从没有人采到过,自然人们由年轻而衰老的趋势也就无可逆转,所以我的发也是日渐的不知所措,这世上的奇迹并没有那么多,至少不会总是让我遇上。
只是因为有当世第一名医在这,那就总有人不愿死心。所以西门泠受缠不住,精制了几瓶药丸亲自送来。
我问他:“有效吗”心里并不抱着什么希望。
他木木的道:“也许有也许没有,我并不是神仙,但总没坏处。”
我淡淡哦了声,还是接过,随手放在桌上。
他伸手入怀,下意识地又警醒的四周张望,虽然他自己很清楚并没有闲杂人等经过。他从怀里掏出一只精致的白玉葫芦,只拇指般胸有成竹,莹莹发出辉芒,外形极其精致可爱。
我忍不住就见猎心喜,伸手去拿那玩物。
他“嗖”的收回,清了清嗓子才很严肃的对我道:“这里面就是你要的名无。”
“无名?”我扬高了眉梢。
“一种见血封喉无药可解的毒药,我刚刚研制成功的。”
“连你也不能解?”我再一次要求确认。
“不能。”
我接过葫芦,感觉轻飘飘的,摇一摇:“怎么才这一点?”
他骇一跳:“你还不满足?我炼了一年也只得这么一滴。”
这次轮到我骇一跳,原来竟是只有一滴,用了就没了,难怪是无名了。
他犹豫了下,终于还是有些不放心的问我:“你真的不是把它用在我们姓西门的人身上?”
“不是。”我正色,答得飞快,想都没想一下。
于是他放心的走了。
他如此天真的相信了我,当然他也就注定要为这天真买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不是吗?
半个月后,当西门风的死讯传来的时候,我正悠闲的在梅林里收集做梅雪茶的花瓣,只是微微浮动了一下眼皮,并不抬头。
深吸了一口气,暗香在林间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