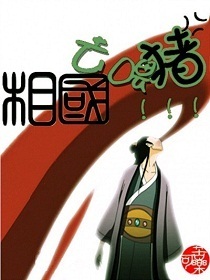相国-第2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许是太过伤心了,突然间,八妹竟是吐出了一口鲜血来,杨延昭惊慌的伸出手,想要扶起她,可却丝毫触碰不到。
“小鱼儿!”
一声惊叫,杨延昭睁开湿润的双眼,看着四周陌生床榻桌椅以及那燃得正旺的火炉,这才明白,刚才的一切不过是个梦。
真的只是个梦么?
恍惚间,杨延昭又一次见到了八妹伤心欲绝的模样,鼻子顿觉满是酸楚,本是擦干的泪水又一次的落了下来。
“吱呀!”
木门被推开,一丝寒意灌进了很是暖和的房间,杨延昭忙胡乱的摸着脸颊,也在这时,他才发现身上那沾满血迹的棉袍已经被人换成了干净的裘皮辽服。
人未至,已有淡淡的清香随着那缕寒风飘了过来,抬过头,那左婆娑正跨进了屋里来。
“你醒了?”
声音冷冽,恰似屋外呼啸的寒风,让人无意亲近,更是生不出好感。
见杨延昭不出声,左婆娑柳眉蹙起,贝齿咬了咬小嘴,转身往外走去,只是心中多了怨恨,关门时不觉得力道大了许多,啪的一声惊得门边上火炉里的火苗儿惊怕地乱窜着。
对于厌恶之人,杨延昭自然是没有兴趣与她说道着话,哪怕是看一眼,都会觉得不屑。
待左婆娑离去之后,这才努力的坐了起来,身子骨似乎还隐隐约约作痛,但想起那日大殿上的突破,杨延昭心里还是有着莫名的欢喜。
可是片刻之后,脸色猛然一变,杨延昭瞪着眼满是愤怒之色,“我去你大爷的,又是封印!”
胸口不断起伏着,骂完这句,竟是忍不住的咳嗽了起来,“总有一天,老子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手紧紧的抓着那兽皮做成的毯子,杨延昭钢齿咬的嘎嘎作响,眼中充满了恨意。
就在这时,门再次被打开了,那道杨延昭很是熟悉与憎恨的身影飘然而至,打量了他几眼,幽幽的道了一句,“你醒了?”
丝毫不在意杨延昭眼中的仇意,耶律明伸手抓来一张木椅,坐在了床榻前,“你别这样看着我,有些事情便是命中注定的,过去和未来,都无法改变。”
如同发了狂的猛兽,杨延昭双眸染成了血红色,满是愤怒的吼出了一句,“那你有没有算出何时死在我的手里!”
耶律明依旧没有恼怒之色,只是独自一人在那般笑着,好一会见杨延昭平静了下来,这才继续开口道,“那日大殿上救你的是我师祖,封印你的也是他,你是我巫教算出来的秉承天运之人,因而是不能放你离去的。师祖他老人家说你的尘缘未了,所以才封印了你,让你回大辽断去红尘羁绊,待过两日你伤养好了,我便送你回去,等你了却了世俗之事,师祖便会亲自为你解开封印,接你回雪山。”
双手握成拳,杨延昭咬牙切齿的道,“就算我是你说的秉承了什么天运,也不会跟在你身后,终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你!”
“呵呵,先前我便已经说了,有些事情是上天安排好的,由不得你我,若是你有那本事,便尽管来找我好了。”
说着,耶律明起了身,正欲离去,却又是止住步子对着杨延昭道,“如今你已经是我巫教的‘逍遥使’,大辽境内定是无人敢加害与你,不过你也不可妄开杀戒,否者我照样是可以再让你煎熬一番的。”
话语说得很是随和,只是其中的杀机却如针芒毕现,凌厉的让人喘不过气来。
“砰!”
盯着耶律明离去的身影,杨延昭拳头愤恨的砸在了床榻上,满腔的怨恨与杀意,除了有血海深仇的耶律休哥之外,这是第一个让他恨不得生吞活剥的人。
好一会,才使得情绪平复了下来,虽然杨延昭做梦都想杀了耶律明,可事实也正如他先前所说,即便恢复了炼气的修为,也不是地仙修为的对手。
更何况眼下丹田内多了一道刻满古老文字的封印,从这上面散发的藏上久远气息来看,必定比左婆娑的封印强上百倍,又岂是他轻易能解开?
更为可笑的是竟然莫名其妙的成了巫教的‘逍遥使’,且不说这‘逍遥使’有何种的地位,单凭这种强加于他的做法,杨延昭想到就很厌恶。
这巫教的人都是疯子么!
先前要强收他做徒弟,现在又让他做什么‘逍遥使’,使得杨延昭对这巫教厌恶至极,恼怒的骂了一句,又往着地上唾了一口。
蓦然间,回过头,杨延昭看到了床头上放着的东西,玉虚,一道赵光义赐的金牌等他随身带着的物件儿,当看到最后一样时,目光再也移不开了,双目渐渐泛起红色,变得迷离哀伤。
那是个绣着牡丹吐蕊的香囊,是当初离开汴梁时柴清云给他的。
顿时,杨延昭只觉得心中所有的怨恨都化作了无限的思念,先前的梦境再次浮现在眼前,颤抖着双手拿起香囊,取出里面已经发了黄的符纸护身符,落着泪,将护身符放在脸上,似乎这样才能感受到那点滴的柔情。
半晌,杨延昭才从痛苦的思念中清醒了过来,小心翼翼的将护身符放进锦囊,与玉虚,金牌一道,塞进了怀来,毕竟眼下他最为珍贵的东西便是这些了。
深吸了口气,杨延昭明白自己心中最为想要的便是回到大宋,回到柴清云、罗氏女她们的身边。
所以他要用上一切能用的机会,哪怕是有违初衷,那又如何,世人皆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他现在依然没有失败,只有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在的胜者。
眼中闪过一丝的坚定,杨延昭手放在胸前,感受着锦囊的温暖,再次变得与前日子一般,将心里的韧劲和愤怒深深的藏了起来。
耶律明没有失言,三日后待杨延昭行动自如后,便送他下了这高耸入云的雪山,不过没有让他一个人离开,而是派了巫教圣女左婆娑一道前行。
山脚下,是一眼望不尽的皑皑白雪,苍茫大地,银蛇乱舞,即便是心情郁结的杨延昭也因此添了几分宁静。
左婆娑一身墨绿的宫装,不知是因为寒凉还是为了装扮,披着件貂裘大氅,看起来很是别扭,知道她修为的杨延昭明白,大抵还是后者了,所以心里默默的念叨着赶紧来道惊天雷劈了这很是碍眼的女人。
古朴黑漆马车静静的停着,杨延昭率先登上了马车,毕竟他现在修为被封印着,北风怒吼,寒气扑面,可是让他冷得厉害。
车内摆放着一直小火炉,顿时觉得暖和不少,车外的左婆娑几番犹豫,终究是跟着上了马车,只是脸上带的寒霜丝毫不亚于车外。
“啪!”
一声清脆的鞭声响起,马车快速的前行着,车厢中,火炉吱吱的燃着,杨延昭闭目养神,左婆娑则是阴沉着个脸,本是漂亮的大眼却因恨意而怒瞪着。
最终,左婆娑沉不住气了,厉声说道,“别以为师尊让我跟着你,就能随意的使唤我,哼,你最好别惹了我,否则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砰!”
一块刻着九蛇缠绕的褐色令牌甩到了左婆娑的眼前,随即悠悠的声音响起,“说完了?那么可以换我说了?第一,我没让耶律明派人跟着我,当然,如果有的选择,我也不会选你;第二,这令牌你可认识,虽然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但照耶律明的意思来看,似乎我现在的地位在你之上,所以只要我愿意,你就得脱光了衣服站在我的面前。”
对于这左婆娑,杨延昭心中没有一丝的好感,自然恶语相向了,后者在看到令牌时,起初是语塞面露窘态,但听到最后一句时,不由得恼羞成怒,伸出手运出一道真气,便要朝着杨延昭袭去。
“我是‘逍遥使’,你这是要犯上?”
闻言,左婆娑只得收了掌势,用着杀人的目光瞪着他,酥胸也因愤怒而不断起伏着。
俯身捡起地上的令牌,杨延昭故意在手中晃了晃,“没想到这么块破牌子还挺好使的,不过话说过来,即便你脱光了,我也不会瞧上一眼的。”
话一出口,那左婆娑又是恼怒的做出扑杀他的攻势,可那令牌又在她眼前来回晃着,顿时泄了气,只得愤恨的踢着车厢。
而杨延昭则是心中莫名的一阵暗爽,收了令牌,闭上眼不去理会暗自生气的左婆娑,身体随着摇晃的马车摇摆着,似乎睡着了一般。
第三百一十三章 逍遥使出山
马车在荒芜的原野上疾驰,溅起无数的雪花,留下两道蜿蜒曲折犹如游蛇般的车印。
车厢中,有了之前的拌嘴,两人一路无言,左婆娑也许是盯杨延昭盯得乏了,闭目养神起来,只是鸦黑的睫毛时不时地跳动着,睁开一丝缝来,瞄了一眼,又是合上了。
对于她这小动作,杨延昭根本不放在心上,一路行来,不断的挑起车窗帘布一脚,望向车外,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终于,在多次的探头张望之后,杨延昭的眼中闪过一丝的欢喜,对着驾车的巫教弟子大声喊道,“停车!”
虽不知缘由,但驾车的弟子还是顺从的将车停下,快速转动的车轮因骤然停下在雪地上碾过深深的槽痕,那雪泥杂草更是被甩飞了出去。
稳住向前倾的身子,左婆娑正要发怒,便听得耳边那讨厌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圣女殿下,前面便是贝伦山了,能否劳烦殿下给我抓只白兔子来?”
“你竟然让我去山上抓兔子!”
这下,左婆娑彻底爆发了,玉手指着杨延昭,涨红着脸,酥胸起伏,很显然,已经是怒火中烧。
若不是顾忌他‘逍遥使’的身份,杨延昭相信,眼前这疯婆娘绝对会毫不留情的一掌打过来。
将怀中的令牌拿出来吹了口气擦了擦,杨延昭自言自语的念叨着,“这年头队伍不好带了,即便是做了仅次于掌门的‘逍遥使’又有何用,这样别人就会听你吩咐了?唉,我还是自己去吧,希望这山中少些豺狼虎豹,不然小命可就丢在这里了。”
说着,杨延昭便要起身往车下走去,那左婆娑却是一跺玉足,狠狠的瞪了他一眼,“算你狠,你给我等着!”
纵身下车,很快,身影便钻进了贝伦山的雪林之中。
“看来这‘逍遥使’做的还是有些甜头的,至少这疯婆娘听话多了,或许真的可以试试让她脱光了衣服?”
坐在马车内,杨延昭双手抱着头,靠在车厢上,自言自语的说着,脸上没有淫·荡之色,反而是深深的恨意。
北地的夜色总是来得比较快,血红的残阳渐渐隐去,北风越发的猛烈,卷着渗人的寒凉,即便是躲在屋子里听着那狂风呼啸都会觉得心里慌得很。
城门当值的兵卒裹着厚厚的棉袄,心中正巴巴的望着太阳快些落下,这样也能在垛口处躲躲风寒,偷偷的喝上几口酒暖暖身子。
夜幕垂下,城门口已经往来过客寥寥无几,正当守卒打算关了城门时,一辆马车从远处飞驰而来。
提着那冰凉的长矛,几人便打算上前盘查,怎奈那驾车的黑袄之人并不停车,而是瞪了他们一眼,“大胆,国师大人的马车你们也敢拦!”
说着,又是抽了一鞭子,便听得一声马鸣,马车便冲过城门,往着上京城内飞奔而去,转眼便看不到了影子。
城门口,那些兵卒没有半点的恼怒之色,纷纷丢下手中的长枪,望着马车行去的方向叩拜行礼,口中默默念叨着不知名的经文。
小河依旧冰封,上面的积雪没有半点融化的迹象,反而比先前又厚实了不少,或许是这两日又是下了一场雪。
宅子的大门紧闭着,往日里本该亮着的灯笼却没有点上,使得门前一片漆黑,杨延昭下了马车,看着这宅院,突然间生出一种劫后余生,大难不死的感叹来。
也不知宅子里还有没有人了,或许陈管家他们都已经离去了,想到这,杨延昭不禁看了看怀中有些不安的白兔子,继而上前敲起门上的兽环来。
或许是风声太大,清脆的兽环撞击声传不到宅院中去,敲了好一会也不见有人应声,他便索性用手在门上拍了起来。
这下,终于听到院子里传来动响,杨延昭也暗自松了口气,这里他在辽朝暂栖之处,也是唯一能让他有所心安的地方,有人在,那真是太好了。
不多时,朱门开启,一个家仆探出了半个身子来,待看到是杨延昭,忙从门内走了出来,便要弯身行礼。
这人他也认识,遂寒暄了两句,便带着左婆娑进院子了,至于驾车的弟子,便交给那家仆去安排了。
此时酉时未过,但院子里灯火已经灭去了大半,只有零星几盏亮着,与平日里的相比,少了些许的生气。
杨延昭正要往着客厅走,便看到迎面走来整理衣衫的陈管家,想来天寒地冻,闲来无事的他早已经在床榻上躺着了,听到杨延昭回来的消息,自是慌张的穿戴着衣衫急忙的走了出来。
“